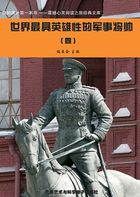经历了艰难的旅程,甘地终于到达了他的目的地比勒托里亚。他以为达达·阿布杜拉的律师会派人来接他,因为在来此地之前,阿布杜拉赛已经告诉他不要轻易住到印度人家里去,因为他们的对手在这儿很有势力,以免他们的书信和秘密被对手得知。而甘地也答应了他的要求。可并没有人来接他,原来这一天是星期天,或许那位律师派人来也很不方便。这下可使甘地很为难,因为他已领教过旅馆的厉害,他担心没有旅馆肯收留他,他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1893年的比勒托里亚车站灯光黯淡,旅客稀落。甘地等旅客都走了以后,把车票递给检票员,并询问什么地方可以投宿,要不然他就得在车站过夜了。可检票员并没有给他多少帮助,而这时站在旁边的一个美国黑人看到甘地的困境便和他攀谈起来。他说:“这么说来,你是一个没有任何朋友的真正的生客了,如果你愿意跟我来,我可以带你到一家小旅馆去,老板是一个美国人,我跟他很熟,我想他会收留你的。”尽管甘地对这个人的建议有些怀疑,可在目前状况下,他也别无选择,只好接受了他的建议,向他致谢后跟他去了。
那人把甘地带到约翰斯顿家庭旅馆,约翰斯顿答应他住一夜的条件是:甘地只能在自己的房间用饭。因为这里只有欧洲客人,如果甘地去饭厅吃饭,老板害怕客人会不高兴。
这里到处都可以窥见种族歧视的痕迹。甘地只好保证不到饭厅里吃饭,而且只住一夜,明天就会和律师取得联系的。可正当甘地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等招待员送饭来时,老板约翰斯顿却亲自来了,他告诉甘地,他征求了其他客人的意见,那些客人对甘地去饭厅吃饭和在这儿投宿毫不介意,甘地可以到饭厅里去用餐了。并不是所有的欧洲人都戴有色眼镜的。甘地很高兴地到饭厅饱餐了一顿。
第二天早上,甘地拜访那位律师阿·伍·贝克先生,把有关自己的一切情况都向他说明了。
贝克说:“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律师的工作可以委托你做,因为我们已经请了最好的顾问。这件案子拖了很久,也很复杂,所以我想请你帮忙的,只不过是了解一些必要的情况。而且你自然可以使我和当事人的来往更便利些,因为今后我所需的一切情况都可以通过你获得,这当然有好处的。我还未给你找到住处,我想最好等见到你以后再说。这里有一种可怕的种族偏见,所以为你这样的人找住处是不容易的,不过我认识一个贫苦女人,她是一个面包师的妻子。为了增加一点收入,我想她会收留你。”于是贝克把甘地带到她家里,她果然同意收留甘地,食宿在内每周35先令,这样,在比勒托里亚甘地总算安顿下来了。
贝克先生虽然是个律师,可同时又是一个坚定的普通的传教者。在甘地和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便探听甘地对宗教的见解。
甘地告诉他:“我生来是一个印度教徒,可对印度教所知有限,对其他宗教知道的就更少了。在宗教问题上,我也不知自己在相信什么和应当相信什么。我想好好研究一下自己的宗教,如果可能的话,也想研究研究其他宗教。”
贝克先生听了甘地的话后很高兴地说:“我是南非宣教总会的董事之一。我自己出钱盖了一座教堂,按时到那里讲道。我没有种族成见。我有几个同事,我们每天下午一点钟都在一起聚会几分钟,祈求和平和光明。如果你愿意去参加我们祷告,我会很高兴的。我可以介绍你认识我的同事,他们一定喜欢见到你,而且我敢说你也会喜欢和我们在一起的。此外,我还可以给你几本宗教书籍看看,自然啰,圣经算是万圣之书,这是我要特别向你推荐的。”甘地答应了贝克准备明天去参加下午1点钟的祷告会,当时并未仔细考虑这个问题。
和贝克先生告别后,甘地付了约翰斯顿的房钱,便搬到新的住处,吃过午饭后又去见了阿布杜拉赛介绍的一个朋友。那个人告诉他旅居南非人所受的苦难,又一次让甘地觉得种族歧视的可恶。天黑以后,甘地吃过晚饭,躺在床上才想起白天贝克先生提到的问题。
甘地心想,贝克先生对自己有这样的兴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自己从他的教友们那里能得到什么呢?对基督教能研究到什么程度?怎样才能弄到印度教的书籍呢?对自己的宗教还没有透彻的了解,怎么能够正确地了解基督教呢?
当时通过思考这许多问题,甘地得到一个结论:应当排除情感,研究所碰到的一切事物,至于贝克先生的团体应如何应付,只好顺其自然了,在自己还没有完全弄清楚自己的宗教以前,不应当信奉另一种宗教。
尽管甘地并未打算信奉基督教,可在参加贝克先生的祈祷会后却和基督教徒有了往来。在那里甘地认识了赫丽斯小姐、嘉碧小姐、柯慈先生及另外几个人。赫丽斯和嘉碧小姐都是上了年纪的未婚女士,柯慈先生是教友会的会友。这两位女士住在一起,她们给甘地一个常年的邀请:每星期日下午4点钟到她们那儿去喝茶。每逢星期日他们见面时,甘地总是把一周来所作的宗教日记请柯慈先生过目,并和他们讨论自己所读过的书以及这些书给自己留下的印象。
柯慈先生是一个坦白而坚毅的青年,甘地除了星期日和他聚会讨论有关一些宗教问题和交流一些书籍的感想外,还常和他一同散步,或去看别的基督教教友,这样不久他们便较熟悉了。柯慈把自己所选择的书给甘地读,他用这些书充实了甘地。这一类书甘地在1893年读了不少,已不能完全记得所有的书名,不过还记得其中看这样的一些书:贝克博士的《城庙评注》,皮尔逊的《很确凿的证明》和巴特勒的《对比论》。
这些书有一些甘地很喜欢,有一些并不十分喜欢。不过《对比论》给他留下的印象很深。甘地认为这是一部精湛艰深而又打动人心的著作,要想能理解这部著作,必须反复研读几遍才行。
柯慈先生一心想让甘地信奉基督教,可甘地并没有这一打算。柯慈先生也并不是一个轻易认输的人,仍对甘地很关心,想对他加以影响。
有一天他看见甘地脖上戴着罗勒念珠的毗湿奴教项链,他以为这是一种迷信,心里很不舒服。便说:“这种迷信对你是很不合适的。来,让我把这项链弄断。”
“不,千万使不得,这是我母亲送我的圣礼。”甘地急忙说。
“可你相信它吗?”柯慈反问甘地。
“我不了解它的神秘的意义,如果我不戴它,我想我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但是没有充分的理由,我决不能把这条项链取下来,因为我的母亲把它戴在我的脖子上是出于她的爱和一种信念,以为它有助于我的幸福。当它随着岁月的消逝而自行耗损,终至破断的时候,我不会再想去弄一个新的。可是这条项链不能折断。”
柯慈先生当然无法理解甘地的理论,他对印度教的某些教规也不是很清楚,但他认为只有基督教才代表真理,他盼望有一天会把甘地拯救出来。因而他力图使甘地相信只有耶稣过问才可以洗涤他的罪过,否则他不可能得救,不管他做多少好事,也都于事无补。
在柯慈先生的介绍下,甘地认识了一个属于普鲁茅斯教派的基督教友。当他与这个家庭来往时,普鲁茅斯教友会的一个教友提出的一种理论却使甘地很吃惊。
那位教友说:“你不能理解我们的宗教有多么美。照你所说的,你的生命的每一个时刻似乎都用于忏悔你的过失和改过自新的工作上。这种周而复始循环不已的行为,怎么能使你得救呢?你是永远不能得到平安的。你承认我们都是罪人。现在看看我们的信仰是多么完美。我们自己改过自新是没有用处的,但是我们必须得救。我们怎么背得起罪恶的包袱呢?我们只能把它放在耶稣的身上。他是唯一无罪的上帝的儿子。凡信他的,必得永生。上帝的慈悲就在于此。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替我们赎罪,我们的罪就不会束缚我们。我们是免不了要犯罪的。人生在世而无罪过是不可能的。耶稣就因此受苦,并为人类救赎所有的罪过。只有接受他救赎的人,才能够得到永恒的平安。试想你的生活是多么惶惶而不安,我们却得到了平安的许诺。”
甘地对他的这一番宏论实在不敢苟同,他反驳他道:“如果这就是所有的基督教徒所承认的基督教,我便不能加以接受。我并不寻求从自己的罪恶的后果中得到救赎。我所寻求的是从罪恶的本身,或者说是从罪恶的思想本身得到救赎。在我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以前,我宁可过着不安的生活。”
从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出甘地那诚实的品格,他不肯借助宗教来逃避自己所犯下的罪过,而是走通过对自己所犯罪过的反思来使自己得到经验教训,使自己以后能避开这种罪恶。同时他相信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相信这样的救赎论。柯慈先生就相信自我纯洁是可能的,因而柯慈担心甘地会因他听了那位教友的救赎论而对基督教产生偏见。可甘地向他重申了自己绝不会因这件小事而对基督教产生偏见。但这时的甘地仍然无法接受基督教。不过他与基督教徒的交往更多更深了,这也与贝克先生的关怀是分不开的。
贝克先生对甘地的前途也很关心。他把甘地带到威灵顿大会去。新教派的基督教徒每隔几年便召开这样的大会,使信徒们得到一种启发或自洁。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宗教维新或宗教复兴。大会主席是当地有名的安德禄·穆莱牧师。
贝克希望大会上使人感奋的宗教气氛和赴会者的热忱和诚笃会使甘地皈依基督教。他还把希望寄托在祷告的功效上,并举出很多例子,讲述祈祷的功效。甘地向他保证:当他感觉到内心的呼唤时,没有什么东西会阻止他皈依基督教。甘地之所以给贝克这样保证,因为甘地做事向来顺应自己内心的声音,如果背着这种声音做事,对自己来说不但很困难,也会使他感到痛苦。基于这保证,也是贝克先生想使甘地信奉基督教的意愿,他们便准备动身到威灵顿去了。
在去威灵顿途中,贝克先生带着像甘地这样被认为是“有色人种”的人赴会也遇到了麻烦。有好多次贝克因此而遇到不便。
有一天碰巧是星期日,由于贝克先生和他的同伴不愿意在安息日旅行,他们便在途中逗留下来。费了好多周折,车站旅馆的经理才同意让甘地留宿,但绝不让他到餐厅去吃饭。
贝克先生不是一个轻易让步的人,他要为旅馆的客人争取权利。可在当时民族歧视比较严重的情况下,他又很为难,尽管他竭力掩饰他所遇到的困难和不便,可甘地却看得清清楚楚。况且自来南非以后,他所感到的种族歧视也不是第一次了。特别是印度人在南非的遭遇,也使甘地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民族偏见。这也是后来甘地之所以要改变这种局面的一个原因吧。
这个大会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的集会,甘地对于他们的诚心感到高兴。他会见了穆莱牧师,也知道很多人为他祈祷,也喜欢他们唱的一些圣诗。大会开了3天,尽管甘地理解并欣赏那些赴会的教徒,然而他并不觉得有什么理由使他可以改变宗教信仰,并且他不相信只有成为基督徒才能进入天堂或得到解脱。当他把自己的这种想法直率地告诉几个相好的基督教朋友时,他们都很吃惊,然而他们也无能为力,没有办法使甘地改变他的观念。
参加了这个大会,贝克并没有使自己原来的打算得以实现。来之前和来之后,甘地仍旧对基督教存有疑虑。而甘地的困难尚不止于此,他实在无法相信耶稣是上帝化身的独生儿子,只有信仰他的人才能得到永生。倘若上帝能有儿子,人们都可以算是他的儿子。若说耶稣像上帝,或者就是上帝本身,那么所有的人都像上帝,或者就是上帝。甘地认为说耶稣的确是以他的死和他的血来赎救世界的罪恶当作寓言还有几分道理,他是不肯相信的。另外,根据基督教的信仰,只有人类才有灵魂,其他生物却没有,所以对它们来说,死亡就等于完全的毁灭,甘地却不以为然,他的信仰恰恰相反,他可以承认耶稣是个殉道者,是牺牲的体现者,是个神圣的大师,但不能认为他是空前最完善的人。他死在十字架上对人世来说,是个伟大的示范,但如果这件事本身有什么玄妙或奇异的好处,甘地是无法接受的。他认为就哲学上说,基督教的原理并没有什么高超的地方。倘若以牺牲精神而论,他觉得印度教徒远远胜过基督教徒。因而甘地并不认为基督教是一种完美无瑕的宗教,更不认为它是一种最伟大的宗教。
在对基督教产生疑问的同时,甘地也并不认为印度教就是完美无瑕而伟大的宗教。他深切感觉到印度教徒的缺点。他认为“不可接触者制度”(是印度教的一种社会制度,当时印度社会除四大种姓外还有一个不可接触者阶级,被称为‘贱民’,被认为是不洁的、有罪的,不能用公共的水井,不能进寺庙……)是印度教腐朽的部分,他无法理解宗派和种姓的存在。既然说《吠陀》是上帝所启示的,那为什么《圣经》和《可兰经》就不是呢?因此在宗教问题上甘地陷入了迷惑,特别是除了基督教的朋友设法改变他的信仰外,伊斯兰教的朋友也那样做。他只好把他的困难写信告诉赖昌德,同时还和印度其他的宗教权威通信,并且得到他们的答复。赖昌德来信让他要忍耐,更深一步地研究印度教。并且有一句话甘地印象深刻:“若以冷静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我相信别的宗教没有印度教那么深远的思想,没有它对于心灵的洞察,或它的博爱精神。”于是甘地开始对宗教作了进一步研究。
甘地买了一部谢礼译的《可兰经》,开始读了起来。同时还弄到了关于伊斯兰教的其他书籍。并和住在英国的基督教朋友通信,其中有一个朋友把甘地介绍给爱德华·麦特兰,甘地便开始同他通信。他寄给甘地一本《完美的道路》,这是他和安娜·金世福合著的书,这本书对流行的基督教信仰提出了反面的看法。他还给甘地寄了另一本书《圣经新诠》。这两本书甘地都很喜欢,它们似乎是支持印度教的。而托尔斯泰的《天国就在你心中》更使甘地倾倒,给他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在它的独立思考、深奥的道德和求真精神面前,柯慈先生所给他的书籍似乎全都黯然失色了。
甘地对宗教进行了初步的研究,而这种研究把他带到了他的那些基督教朋友所未料到的方向。尽管他走了基督教朋友所不想叫他走的道路,但对他们在他内心唤起的宗教的向往,甘地却是永远感念不忘的。正是这种宗教的呼唤,才使他研究了各种宗教。
在甘地到比勒托里亚以后,在他并未有什么实际工作的时间里,他不仅和基督教朋友交往,进行宗教研究,与此同时,他还设法和印度人来往,了解当地印度侨民的状况。
铁布·哈齐汗·穆罕默德赛在比勒托里亚的地位和声誉是很高的,凡有公众活动,少了他就无法进行。好在甘地刚到比勒托里亚的第一周就认识了他。甘地告诉他自己很想和那里的每一个印度人有所接触,有一种想研究那里印度人情况的愿望,请他帮助,铁布赛很高兴。
甘地的第一步是召集了一个集会,请比勒托里亚所有的印度人都来参加,打算把德兰士瓦的印度人的情况告诉他们。
这次会议在哈齐·穆罕默德·哈齐·朱萨布赛的家里举行。到会的大半是弥曼商人,虽然也有几个印度教徒参加了,但当时住在比勒托里亚的印度教居民就很少。在这次会上甘地作了他生平第一次公开演说。他在演说中强调了商业上的诚实,当时有些做生意的人说商业和诚实是不能并立的,他们说商业是很讲实际的,而诚实则是一件宗教的事情;他们认为实际是一回事,而宗教却是另一回事。他们以为做生意谈不上纯粹的诚实,除非是切实可行,人们是轻易不说的。
甘地在演说中竭力非难这种说法,使商人觉悟到他们的双重责任:在外国诚实格外重要,因为少数几个印度人的行为乃是他们的亿万同胞的品行的准绳。在演讲中甘地还针对当时他们人民的习惯和生活还不是很讲卫生的情况,让他们加以注意,同时还强调了让他们忘却诸如印度教徒、穆斯林、波希人、基督教徒、古遮拉特人、马德拉斯人、旁遮普人、信德人、卡赤人、苏尔特人等差别的必要性。由此可以看出甘地是没有任何民族偏见的,他认为普天之下的人民都应该是平等的,在前边他研究基督教时便曾经有过这样的观念,他说如果耶稣是上帝的本身,那么所有的人都是上帝。
在会议结束时,甘地建议成立一个协会,以便把印度侨民的苦处陈述于有关当局,以便争取印度人所应有的权利,他并表示可以抽出时间为这个协会服务。
在这次会上还决定以后每周或可能时每月开一次这样的会。这次会开得比较圆满,而且甘地给参加会议的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由于定期地召开这种会议,甘地很快地熟悉了当时住在比勒托里亚的印度人,而且也了解了他们的情况,借此他去见了比勒托里亚的英国监督官贾科布斯·戴·韦特先生。这位监督官很同情印度人的处境,可他没有什么势力,无法改变那种局面,可他答应甘地尽其所能帮助他们。
在这同时,甘地还写信给铁路当局,告诉他们,根据他们自己的规章,印度人也不该受到旅行限制。可他得到的答复却很令人失望,回信称:印度人只要是服装合适的,当然可以买头二等车票。可这如何能解决问题呢?什么叫服装合适,那衡量的尺度又是什么呢?决定权还不同样是操纵在站长手上吗?印度人仍旧得不到公正的待遇。
从英国监督官和铁布赛给他的一些关于印度人事务的文件里甘地得知,印度人是如何被残酷地驱逐于奥伦治自由邦之外的,这需要追溯一下历史的原因。
奥伦治自由邦的印度人,由于1888年或者更早的时候所订立特殊的法律,而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利。如果他们想在那里住下去,就只有到旅馆去当招待员或干些类似的卑贱工作。做生意的被赶走了,只给了一点点名义上的赔偿,尽管他们请愿,递交了申诉书但没有结果。而在德兰士瓦于1885年通过了一个更严酷的法律,1886年略有修改,根据这个法律,所有的印度人到德兰士瓦都得交纳3英镑的人头税,除了在特别划给他们居住的地区内,他们不得拥有私有土地,可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土地的私有权。他们还没有选举权,所有这一切都是根据那个为亚洲人而立的特殊的法律,其他适用于有色人种的法律对他们也有效。根据这些法律,有色人种、印度人都不得在公共的人行道上行走,如果没有许可证,不得在夜间9时以后出门。而这一条对印度人来说更不公平,凡被认为是“阿拉伯人”的人,作为一种优待,都可以免受这项规定的约束。这样一来,谁能享受优待只有警察说了算了。
关于不得在公共人行道上行走和不许在夜间9时以后出门的规定,甘地本人有切身体会。当时甘地常常和柯慈先生在夜间出去散步,很少10点以前回家。可一旦警察把他抓起来那可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同样困扰着柯慈先生,他可以给他的黑人仆人发通行证,可他又不是甘地的主人,无法给他发通行证,况且那是违法的。无奈,柯慈先生只好带甘地到当地的检察长克劳斯博士那里,原来这人和甘地竟是校友。可他尽管对甘地深表同情,也并未给他发一张通行证,而只是给了他一封信,授权他出门时警察不得干涉。甘地出门的时候便带上这封信,庆幸的是他一次也没有用到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意外,或许警察也怕麻烦去弄清他是印度人中的哪一个派别吧。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他自此结识了克劳斯博士,这种关系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很有用,以便利于他的工作。
关于使用人行道的规定对甘地的遭遇的影响可比不让夜间出门坏多了。
当时他常常走过总统大街到一块空旷的地方去散步。克鲁泽总统的房子就在这条街上,是一栋非常普通的、不惹人注意的建筑物,只有在看到门前放哨的警察时才表明它是某一位官员的房子。甘地总是沿着人行道不声不响地走过那名岗哨,这些岗哨是常常轮班调换的。有一次有一个警察没做任何提示性的警告便把甘地推开,并把他打到街上去了,当时弄得甘地不知所措,几乎惊呆了,而正巧这时柯慈先生骑马走过这里,便招呼甘地说:“甘地,我什么都看见了。如果你到法院里去控告这个人,我将乐意作证人。你遭受到这样粗暴的殴打,我觉得非常遗憾。”
可甘地并不想控告这个人,因为他也只是执行条文而已。柯慈申斥了那个警察,那位警察只好道歉。从此甘地再也不走这条马路了,他不想再发生这种不愉快的事,他选择了另外一条路散步。这件事加深了他对于印度侨民的感情。
在比勒托里亚的居留以及和那里印度人的来往,使甘地有可能就德兰士瓦和奥伦治自由邦的印度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情况进行了一次研究。通过对印度侨民的艰苦情况进行的研究以及读到的材料、听到的谈话以及自己的亲身体验。甘地明白南非不是一个有自尊心的印度人住得了的国家,如何才能使这种情况获得改善,便成为他心中不得不考虑的越来越操心的问题了。
和基督教徒的交往以及和印度侨民的交往或是对宗教的研究都没有使甘地忘记自己到南非来的目的,那就是达达·阿布杜拉的案子。
达达·阿布杜拉的案子不算小,牵涉到4万英镑的得失。因为它是由商业交易引起的,所以里面涉及许多琐碎的账目。有一部分要求是根据已经交付的期票,另一部分是根据对方交付期票的特别承诺。被告的辩护是说这些期票不是以合法的手续取得的,而且缺乏充分的理由。这个微妙的案子充满了无数的事实和法律问题。原告和被告双方都聘请了最有才能的律师和法律顾问。
甘地负责给律师准备原告的案由和挑选一些有助于他的案子的事实,因而便可以看到自己准备的材料有多少被律师所采纳,有多少被舍弃,同时也可以看到律师所准备的材料究竟哪些是由法律顾问所采用的。这对甘地的确是一种教育,锻炼了他的理解力和运用证词的能力。甘地对这个案子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他把所有关于这些交易的文件都看过了。当事人很信任他,使他的工作没有任何障碍,由于对簿记学的研究,他的翻译能力也有提高,因为来往信件大部分是古遮拉特文,需要翻译。
由于甘地把精力放在案子的准备工作上,因而他对案情的了解不亚于当事人。在研究案子过程中,甘地发现他的当事人的理由虽然很充足,可法律却似乎对他不利,为此他请教了南非著名律师李昂纳先生。李昂纳先生让他在案子的事实方面,作进一步研究,然后再去找他。甘地便把事实重新作一番推敲,并且在无意中还找到了一件和这个案子颇为相似的南非旧案例。当他再次去见李昂纳先生,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他时,李昂纳先生说这场官司打赢的可能性很大,当然还要弄清是谁经办这个案子。
通过这番调查,甘地发现事实在办理案子中的重要作用,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事实就是真理,我们一旦依附了真理,法律自然就会来帮助我们了。
甘地知道达达·阿布杜拉的案子,事实的确是极有力的,因而法律方面当然是有利的。可是他觉得,如果官司继续打下去,原告和被告双方就会两败俱伤,而他们彼此都是亲戚又是同乡,谁也不知道这件案子要到什么时候才能了结。如果让它继续在法庭里弄个水落石出,它可能无限期地打下去,这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其实双方都希望立即了结这个案子。甘地便想从中调解,让他们双方尽快把这个案子了结。
他见了铁布赛劝他去找人仲裁,向铁布赛建议让他找他的法律顾问,提议如果能找到双方都可以信任的仲裁人请他出来公断,这个案子就可以迅速获得解决。
当时,律师费急速增长,尽管当事人都是商人,也经受不了这么庞大的支出,这件案子占有了他们过多的注意力,使得他们连做别的事情的时间都没有了,同时相互间的恶感也不断上升。况且不管哪一方胜诉,双方的费用都不会小。因而甘地觉得有责任使他们双方重归于好。
由于他的努力,铁布赛总算同意了。仲裁人也选定了。结果阿布杜拉获胜。
然而这并未使甘地感到满足。如果阿布杜拉要求铁布赛全数付清37000英镑是不可能的。因当时旅居南非的波尔邦达弥曼人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就是宁肯死亡而不愿破产。可铁布赛不愿意少付一个铜板,也不愿宣布破产。这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达达·阿布杜拉同意他分期偿付为数不大的款项,阿布杜拉慷慨地答应了,时间也拖得很长。取得分期付款让步,对甘地来说,比促使他们同意仲裁还要困难。可是双方对于这个结局都很满意,也得到了舆论的推崇,甘地的快乐是不可言喻的。
通过办这个案子,甘地学会了法律的真实的实践,学会了通过掌握人性之善良的方面而深入人们心灵。他懂得了律师的真正职责并不是寻找法律来支持他们的当事人在法庭上获胜,而是使当事人之间的嫌隙消除言归于好。
这个教训是那样深刻地印在他的心里,以至于在他执行律师业务的20年间,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促成案件的私下妥协。这样对他的收入和精神都没有什么损失了。这体现了甘地那善良和博爱的品格,他不希望他的当事人弄得两败俱伤,他希望看到人们和平相处,不分地位尊卑,都在同一个蓝天下快乐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