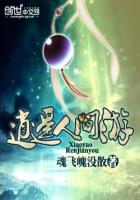肖邦度假回到华沙以后,他的爸爸妈妈看见肖邦晒黑了,身体也变得结实了,嘴唇上面露出了微微发黑的胡须。他们说:“没有想到,一个多月的乡村生活,能给你的身体带来这么大的变化。”
随后,肖邦把他在庄园里创作的乐曲交给埃尔斯纳老师审阅。在他的这些乐曲里,蕴含着新的素材和新的表达方式。
埃尔斯纳认真地看着肖邦的作品,他仿佛也亲临了那个欢乐的丰收节晚会。在这个晚会上,肖邦用低五度的粗犷和尖锐的高音相互对比,用音乐诉说着这个古老的习俗。
埃尔斯纳还从肖邦的作品里,品味到了新的异国情调。乐曲里面浸透着辛酸与忧愁,与乐章里面欢快的旋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尽管这些作品显得很稚嫩,但埃尔斯纳老师还是给了肖邦许多鼓励。很快,高中生活到了最后一年,肖邦开始专注于其他科目的学习了,因为父亲希望他可以在古典文学以及数理方面有好的成绩。
开学后,肖邦开始跟着埃尔斯纳学创作与波兰舞曲、圆舞曲不同的《玛祖卡》舞曲。《玛祖卡》的旋律明显地显现特有的舞蹈节奏,这种舞蹈的步法非常丰富,特别是男子跳得激动时,常常用脚变换出各种花样,非常精彩!
千篇一律的练习弹奏,已经满足不了肖邦对音乐的强烈渴求,他脑海里即兴演奏的灵感,时时激起他强烈的创作欲望,他终于创作出了充满自由魅力的《玛祖卡》舞曲。
肖邦又用自己在乡间亲耳听到的犹太人的音乐音调与和声,创作了富有特色的乐曲《小犹太》,作品纯朴生动,前奏和尾奏用了平行的空音,模仿出民间器乐的演奏,使旋律活跃,具有欢乐的舞蹈性质。
后来,在肖邦的全部作品中,《玛祖卡》舞曲占了很大的比重。《玛祖卡》是肖邦创作民族民间风格音乐的试验田。在肖邦的作品中,《玛祖卡》不但数量最多,而且内容也是最丰富、最富有独创性的。
几年后,在华沙国家剧院举行的音乐会上,肖邦弹奏得最多的,便是他创作的《玛祖卡》。当时,听众为他的那些好听的民族和声、为他民族化的节奏、为他娴熟的演奏技巧所倾倒。
正如《波兰快报》发表的音乐评论所说的那样:
肖邦熟悉波兰的山川和河流,熟悉波兰乡村民歌。他把乡间的曲调用他精湛的技巧,完美结合在他的作品里。他创作了波兰人自己的《玛祖卡》。
1825年10月29日,华沙首次上演了著名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的代表作《塞维勒的理发师》。
肖邦看过这出歌剧后,觉得很有节奏慼,便抑扬顿挫地朗诵起里面的台词。从此他喜爱看歌剧了,歌剧院只要上演新戏,肖邦就场场不落,他把自己的零用钱都省下来买了戏票。
在那个年代,欧洲音乐界把歌剧看作是音乐的最高形式,作曲家尼釆第、梅雨、韦伯等音乐名人作品上演的日子,都会成为华沙的音乐迷们盛大的节日!
这一学期,肖邦又交了一个新朋友雷姆别林斯基。他经常和肖邦一同去看歌剧。当时,雷姆别林斯基已是个小有名气的音乐家了。他虽然比肖邦年长几岁,但和肖邦有着共同的音乐志向,他们之间有着说不完的话。
一天,他们一同从剧院里出来,走在华沙的大街上,肖邦对雷姆别林斯基说:“我发现你弹琴时,左手和右手一样有力,你能告诉我你是怎样练习左手的吗?”
雷姆别林斯基说:“这太简单啦!用你的左手,做你右手能做的事情!”
听完雷姆别林斯基的话,肖邦如梦初醒。从此以后,他吃饭、穿衣、写字,一切都用左手来做,终于有一天,他把自己的左手锻炼得和右手一样的灵巧了。“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早在1825年以前,时局就已经动荡了起来。
街上走过一列列押送囚犯的队伍,但是这些囚徒不是一般的犯人。在欧洲城堡的监狱里已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然而他们不是常见的罪犯。
不仅在华沙,而且在巴黎、在莫斯科、在维也纳和柏林都悄悄地流传着有关密谋集团、有关暗杀暴君、反对国王和皇帝暴力的消息。
中学里一些高年级学生已经知道了不少这类事情。正是这一年的秋天,他们当中一个名叫阿达姆·维耶日依斯基的,直接从课堂上被带走了,人们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他。闹哄哄的课堂和走廊里一连几天死一样地寂静。那位被抓走的同学的几个朋友穿着丧服来了,而他的一位最亲近的朋友突然出走了。
那天,当维耶日依斯基被抓走时,蒂图斯马上跑去找肖邦。肖邦正在弹奏克莱门蒂的练习曲,他不久前才刚得到这些练习曲的乐谱。现在他正为解决演奏上的难题努力克服不听从使唤的小拇指所造成的阻力。
蒂图斯一进门就开了腔,但又立即收住了话头。肖邦一边点着头,一边不停地在说:“是的,是的。”但是看得出来,他没有听,也没听见。
当朋友使劲把他的手从琴键上拽下来,又向他重复一遍之后,肖邦才理解到这个坏消息的含义。
蒂图斯匆匆地对肖邦说:“有人说,维耶日依斯基参加了一个名叫乌卡辛斯基组织的密谋集团。他们将受到严厉的审讯和判决,因为他们反对君主政权。”
“他们想反对亚历山大吗?”肖邦轻声地问。
“大概是的。”蒂图斯显得有些惊慌。
两个小伙子面面相觑,一声不吭,好像在他们头上笼罩了一大片乌云的阴影,似乎是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蒂图斯必须马上回去上课,因此留下肖邦独自一人。他又开始弹奏克莱门蒂的练习曲,但他觉得,此时此刻,音乐还不是什么不值得关心的东西。
一个音乐主题、一个充满威严和力量的谐音,犹如战斗的呐喊,在他的脑际一掠而过。肖邦试图在琴键中找到它。他想弹奏、谱写出这样的作品,它能称得上对英雄们的悼念,它要像诗、像叙事诗、像凯歌,同时又像哀乐。
他甚至没有听到尼古拉提着灯走进已是昏暗的房间,还叫了他一声“弗里德里克”。
直至叫第二遍时,肖邦才从凳子上站起身来:“爸爸,我听着哪!”
尼古拉脸色阴沉,心事重重。他没有注意到窗户开着。
“你快去准备明天的功课吧!今天音乐已经够了。”
肖邦顺从地站起身来,但在门槛上站住了。他回过头,怯生生地问:“宪兵没有再抓走其他人吗?”
尼古拉严肃地告诉肖邦:“可不要说,也不要去想这个问题。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外面,我永远不准你再谈这些不幸的事,懂吗?”
肖邦的目光垂了下来,他轻声地掩上房门。但父亲的声音把他又叫了回来。尼古拉手里一直还提着灯,灯光从下面照到脸上,他的脸色显得憔悴、衰老。
他温和地告诉肖邦:“别去想这些。这一切是徒劳的,不值得,真的不值得。要知道,我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但今天我断定,所有这些战斗和斗争都是徒劳的。别去想这些吧!”
柯希丘什科起义的日子,如同昨天刚过去一样,让尼古拉对此仍然记忆犹新。那是法国人民把自己君主的皇冠连同脑袋一起搬了家的时代。因为几百年来千百万人的贫困、饥饿和痛苦,曾使路易十六皇帝的路德维克·卡佩公民站到了人民法庭的被告席上。
那时人们以为,似乎可惜的政权所造成的罪恶将一去不复返,欧洲人民的历史将由欧洲人民自己来谱写。华沙从巴黎的街垒中得到了启示。法国籍的、赤诚的波兰人尼古拉在华沙的街垒中曾经作为柯希丘什科的战士战斗过。
然而,法国革命失败了。华沙的街垒也沦陷了。革命失败后20年,即弗里德里克·肖邦出世5年后,欧洲的君主们云集在奥地利首都漂亮的维也纳城,开会讨论如何整顿隐藏着对革命的回忆的危机,并遭到了它的执政官和背叛者拿破仑的战争浩劫的欧洲。
会议建议划分新的国界,与会者跳了欧洲上流社会最时髦的华尔兹舞。开会期间缔结了闻名的“神圣同盟”。
一方面,政府报刊的无耻文人、君王统治机关的忠实臣僚们,对君主的有关政令和法律大肆赞美和颂扬。另一方面,“神圣同盟”时期是以君主的秘密警察的活动而著称的。
“君权受于天命。”“神圣同盟”创立者们的政令和法律这样宣称。因此对君权必须给以最高的崇敬和绝对的服从。
但是,君王真正的基础是建立在社会不平等和最低层人民的饥饿、贫困、受压迫和受剥削之上的。皇帝和国王们深深懂得,不平等的权利靠盖上大印的一张纸、靠政令和法律都是保不住的,因此,宪兵成了这些权利的主要捍卫者。
在欧洲各国的首都建立了秘密警察厅。一有风吹草动,或出现任何反抗暴君的意图,它的密探和特务们就要跟踪侦探。绞刑架、枪弹和镣铐成了君王和他们的宪兵奴才们的武器。在监狱和城堡的牢房里,在他们的庭院里,在服苦役和流放生活中,为革命口号而战的人们倒下牺牲了。侦探们不分白天黑夜地奔忙着。囚犯们从容就义时高呼“自由万岁!”
在他们遭到绞刑、枪杀或因刑讯、苦役而折磨致死的地方,不断有新的战士奋起斗争。整个欧洲处于恐怖的无形密网的包围之中。但首要的事实却是,欧洲被另一个强大的网笼罩着,这就是革命密谋集团的网。
尼古拉知道这一切,也看到了这一切,但他对斗争的意义却不再抱有信心。随着岁月流逝,尼古拉的头发花白了,他年富力强的时代已经过去。工作、阅历、欢愉和忧愁在他脸上犁出了几道深深的皱纹。而这时“神圣同盟”的力量,它那大概不可抵御的威权正在日益增长。密谋和斗争只是带来了无谓的牺牲、痛苦和流血。
如果不是为了自己的独生儿子,尼古拉现在可能会竭力不去想这些。肖邦是自己一生的希望和骄傲。他经历了极度的不安,简直是心惊胆战的一刻。那一场反对暴君的徒劳战争的地下洪流会不会把肖邦卷进去呢?不祥的旋涡会不会把他吞没呢?
尼古拉知道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用不着宪兵,就可以理解中学高年级学生中不安的含义。整个华沙都在纷纷议论爱国同志会和自由波兰人同盟的密谋被揭破一事。军官中、市民中、大学生中,甚至在中学里到处都有人被捕。
而维也纳会议把俄国和波兰联合在既是俄国沙皇又是波兰国王的亚历山大一世的政权之下。“神圣同盟”创始人之一亚历山大一世在自己执政的初期选择了狡诈的策略。他对自己统治下的臣民说了许多好话。他给波兰制定了宪法,并许诺给俄国制定宪法。他的讲话像童话一样娓娓动听,因为实际上也只是童话而已,事实却是压迫、剥削和饥饿。饥饿使波兰和俄国的农民濒于死亡。俄国和波兰的监狱关满了俄国和波兰的自由战士。
1824年,华沙的爱国同志会密谋集团暴露了,紧接着自由波兰人同盟也暴露了。华沙的诉讼案件尚未结束,革命的华沙和革命的圣彼得堡、基辅之间开始了会谈,旨在掀掉亚历山大头上俄国和波兰国王的皇冠。
1825年12月1日,一个意外的消息在整个波兰迅速传播开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突然死掉了。
一群俄罗斯军官便趁着混乱的局势,在圣彼得堡发动了暴乱,希望能够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制度。华沙的人民都希望这次运动会取得成功。
于是,波兰人民纷纷行动起来,分发武器,上街游行,并与君士坦丁大公的卫队展开了枪战。可是,由于寡不敌众,武器也不够先进,暴动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随后,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波兰,统治者都对人民进行了血腥的镇压。
一个俄罗斯军团因为拒绝向新沙皇尼古拉一世宣誓效忠,被押往贵族院广场,然后用大炮炸死了。煽动闹事的人被处以死刑,知识分子遭到了驱逐。
那一段时间,波兰城内血肉橫飞,人心惶惶,处处充满了恐怖气氛。反动分子的血腥镇压让波兰人民普遍感到绝望,他们一齐穿上了黑衣,为死去的亲人和战友们戴孝。
密谋者们决定阻止他的继承人尼古拉登上王位。不会再有国王和沙皇了。俄国将获得宪法,遭受圣彼得堡君主铁蹄蹂躏的国家将获得自由,这些就是密谋者们的纲领。
然而,那些密谋者们犯了一系列错误。推举了拙劣的领导,犹豫不决,耽误了斗争开始的时间,而最主要的是没有把人民发动起来,尽管他们是想为人民并以他们的名义进行斗争的。根据尼古拉的命令,响起了第一阵枪声,枪弹的烟雾笼罩了枢密院广场,鲜血染红了白雪皑皑的大地。
那些枪声决定了一切。沙皇尼古拉踏着十二月党人的尸体登基了。俄国和波兰的监狱又一次塞满了囚犯。沙皇发现圣彼得堡和华沙暗中有联系后,气得发狂了。
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结成了同盟,这对于君王来说是最可怕的威胁。沙皇暴跳如雷,因为他懂得,这个同盟是预示他必将遭到失败的第一个信号,人民的同盟像飓风一样危险,它将像吹走纸折的玩具那样毫不费力地掀翻他的宝座。
沙皇签署的判决书宣告着死刑、无期徒刑和终身劳役。沙皇想以犯人的鲜血和痛苦来吓倒那些准备进行新的斗争的人们。
然而,流下的鲜血不单单只是产生恐惧,犯人的鲜血和苦痛首先产生的是新的仇恨。那些决意要反对非正义的人,也许会害怕死亡,但却不打算在死亡面前退却。
圣彼得堡和华沙的诉讼使丧事遍布两国,但那些穿着丧服的人们又重新开始联结起密谋集团的网。
表面看来,一切似乎都平息下去了。沙皇一登基就获得了“王位上的宪兵”的称号。慑于十二月党人的暗杀,沙皇向全国各地派出了一群群鹰犬,特别是圣彼得堡和华沙笼罩着一片恐怖。每一座墙、每一扇门都有特务、暗探的眼睛和耳朵在窥视与偷听。
因此,从外表看来出现了称心如意的、表面的安定是不奇怪的。人们似乎觉得,现在青年人感兴趣的只是歌唱、姑娘、斟满的酒杯和愉快的生活。甚至有这样的宪兵将军们,他们以为在对十二月党人进行血腥判决之后,任何人头脑里再也不会出现暗杀沙皇的念头。那些对于生活除了安宁别无奢求的人,更是对这种安宁确信不疑了。
肖邦正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看到和听到关于诉讼案件以及处决1824年和1825年密谋者的消息,尼古拉也有过自己的忧虑。对儿子的担忧和对暴君的仇恨、正义感和渴求有一个安宁的晚年的愿望,在他的内心斗争着。但对儿子的担心占了上风。因此,当那些事件平息以后,尼古拉暗暗地松了一口气,一切总算要平静、安定下来了。
1825年,俄国沙皇庆贺自己荣获波兰皇位,肖邦被召去为他演奏。
这件事情对肖邦的打击很大,他的身体状况也很让他的父母担心。他常常生病,稍稍做点事就会感到筋疲力尽。可是他依然没有放弃他的音乐和他的作曲。
在3年的高中阶段,肖邦一直担任学校的管风琴手,管风琴也成了影响肖邦音乐的重要乐器。很快,7月份的考试要来临了,肖邦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接触音乐或是弹琴了,他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准备一般的科目上,因此他十分疲惫。
不久,因为超负荷的学习,肖邦终于病倒了。他瘦削的面孔上呈现出空洞的神情。蒂图斯见到他的时候,简直被他的模样吓了一大跳。
1826年6月,肖邦从华沙中学毕业了。月底,肖邦得知自己考进了华沙音乐学院,才算是松了一口气。于是,他和蒂图斯两个人就到处闲逛,还经常去听歌剧或是音乐会。
同年7月3日,为纪念同年6月5日在伦敦去世的歌剧作曲家韦伯,华沙举行了隆重的追悼活动,并且首次上演上了韦伯的作品《自由射手》。
这部剧作讲述的是,善良的阿加特如何拯救苦闷悲伤的马克斯。这部剧的音乐写得很好,它的德国式情调,特别适合德国人的口味。肖邦一边看一边和雷姆别林斯基小声地讨论。
通过观看这出剧,更加拓宽了肖邦的音乐思维,谈话间,他萌生了一个更强烈的愿望:我也要在钢琴上表现精彩纷呈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