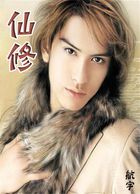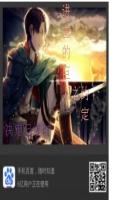武则天于圣历元年接回庐陵王并立为太子,是唐朝后来得以恢复的基础,没有这个转变和基础,李氏子弟就不能取得皇位继承的合法地位。随着李显被立为皇太子,从这时开始武则天对待李氏家族的态度也随之发生很大的变化,从原来的打击、抑制政策一变为笼络、安抚政策,逐渐恢复李氏子孙应有的政治地位,改善李、武两个家族的关系,希望能够形成李武联合执政的政治局面。有很多迹象都可以说明这一点。圣历二年十月,解除了李旦诸子的囚禁状态,赐宅于洛阳积善坊,兄弟5人分院同居,号“五王宅”。大足元年(701),又跟随武则天到了长安,又在兴庆坊赐宅,也号“五王宅”。李显共有4个儿子,长子李重润本来已立为皇太孙,李显被废黜后,他也随之迁居房州。李显立为皇太子,他被封为邵王。次子李重福这时封为唐昌王,三子李重俊封为义兴郡王,四子李重茂,由于年幼,直到圣历三年(700)才封为北海。李显的诸子中除李重润原来就有名位外,其余诸子都是这一时期册封的爵位。
此外,武则天还采取种种措施希望能调和李氏与武氏子弟间的矛盾。圣历三年,吉顼因依附于太子,武氏子弟怨恨,百般攻击,将其贬黜。吉顼临行时,得到武则天的召见,吉顼涕泣而言:“臣今日远离陛下,永无再见之日,愿向陛下进一言。”武则天命他坐下谈,吉顼说:“将水与土合为泥,有争乎?”回答说:“无。”吉顼又说:“将泥的一半制成佛,另一半为天尊,有争乎?”武则天说:“有争。”吉顼顿首说:“宗室、外戚各安其分,则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仍封为王,这是陛下驱使他们日后相争,两方都不得安全。”武则天说:“朕也知道,但是事情已经如此,也不好如何改变了。”不管武则天努力的效果如何,她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就是一种变化。在其他政治方面也都从这时起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在后面的篇目中还要详论。可以这样说,圣历元年是武周政治变化的一大转折点,转折的契机是李显被接回并立为太子,而促成此事的人无疑也是这种转折的促成者,因此他对李唐王朝的重建所做的贡献自然是关键性的。
那么,这个发挥关键作用的人应该是谁呢?司马光认为力主召回庐陵王的是狄仁杰,主张立庐陵王为太子的则是张易之、张昌宗与吉顼等人。司马光之所以这样看问题,根本的出发点还是想为狄仁杰讳,因为如果狄仁杰主张立庐陵王为太子了,则等于劝武则天废黜李旦的皇嗣地位,所以他宁可不相信这样的记载,转而采用二张劝武则天立庐陵王的记载。司马光这样取舍史料后,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即匡复唐室的功绩岂不是为二张、吉顼等人据有了吗?这也是他所不能接受的,于是他又进一步解释说,狄仁杰志在为唐社稷谋,而二张、吉顼辈则是为自己的长远利益着想,两方的出发点不同。《新唐书·狄仁杰传》说,张易之曾向狄仁杰请教自安之计,狄仁杰对他说惟有劝陛下迎回庐陵王才可以免祸。司马光认为狄仁杰不会和张易之这样的小人商议大事,认为这个记载也是不可靠。司马光的本意还在为狄仁杰讳,不愿让张易之玷污狄仁杰的人格。从狄仁杰对二张的一贯态度看,司马光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何况有许多史料都已明确记载是吉顼向二张献的策。尽管司马光绕了这么大的圈子,其本意仍在肯定狄仁杰在匡复唐室问题上的关键作用,同时又不想让自己心目中的社稷之臣有丝毫的“污点”。
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认为中宗复辟实由张易之之力,并不同意司马光的观点。陈先生只相信有关二张进言的记载,却对狄仁杰等一批朝士在这个问题上的作用的记载重视不够,其原因和他所要论述的论题有关。他认为从唐高宗初到玄宗末年,历百余年时间,实际上是李武联合执政的政治格局。二张是属于武氏集团中人,张易之的外甥杨国忠为天宝时期的权臣,自然也是武氏集团中人,说明武氏集团在玄宗未年仍在政局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了证明武氏集团在这一时期重大决策上的影响力,自然宁肯相信张易之促成中宗复辟的记载。
但是唐人凡论及此事者,几乎无不认为狄仁杰发挥了关键作用。其次是唐人吕温,此人为贞元至元和时人,充任过左拾遗、侍御史、户部员外郎等职。他撰写过一篇名为《狄梁公立庐陵王传赞并序》的文章,认为“唐复为唐,系公是赖”,“乃建国本,代天张机”。充分肯定了狄仁杰的历史功绩。稍后有唐人冯宿,他是贞元至开成中人,历任太常少卿、集贤殿学士、兵、刑、工部侍郎、东川节度使等职。他赞扬狄仁杰“再造唐室,时维梁公”。评价之高,前所未有。宪宗时的宰相令狐楚说:“洪惟昊穹,降鉴储祉。诞生仁杰,保佑中宗,使绝更张,明辟乃复,宜福胄嗣,与国无穷。”
唐代著名大诗人杜甫对狄仁杰也有很高的评价,作为诗人他用自己的作品赞扬了狄仁杰匡复唐室的不凡之举。他说:
汝门请从曾公说,太后当朝多巧计。
狄公执政在末年,浊河终不污清济。
国嗣初将付诸武,公独廷诤守丹陛。
禁中册决诏房陵,前朝长老皆流涕。
太宗社稷一朝正,汉官威仪重昭洗。
时危始识不世才,谁谓荼苦甘如荠。唐人众口一辞地赞扬狄仁杰,说明狄仁杰迎归中宗,匡复唐室的事迹在当时曾广泛传播,已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
为什么当时主张迎归中宗的人颇多,人们却只认可是狄仁杰的功劳呢?《旧唐书·狄仁杰传》说:“初,中宗在房陵,而吉顼、李昭德皆有匡复谠言,则天无复辟意。惟仁杰每从容奏对,无不以子母恩情为言,则天亦渐省悟,竟召还中宗,复为储贰。”可见进谏的人虽多,但真正能够使武则天改变主意的还是狄仁杰。狄仁杰能够成功的原因,一是方法正确,以母子之情感化她,使武则天易于接受。二是武则天信任和倚重狄仁杰,这样就建立了互相信赖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就不会猜忌和怀疑狄仁杰另有企图,因而也容易接受对方的意见。三是狄仁杰持身以正,不以权术诡道对待武则天。关于这个问题,王夫之的议论颇为精彩。由于狄仁杰把握时机,既达到匡复唐室的目的,又未引起社会动荡,所以有人误认为狄仁杰如果不采取诡秘手段、玩弄机权之术,恐怕达不到这样理想的效果。针对这种看法,王夫之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观点,他认为“以机权制物者,物亦以机权应之”,而君子不如奸人险诈,结果必然是君子先被击垮。只有以正自处,才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而天时人事自与之相应”,这样就可以不变应万变,使奸人无懈可击。他认为作为社稷之臣没有其他诀窍,“惟正而己矣”。出于这个看法,所以他批评了历史上那些“愤而或激,智而或诡”的人物,认为他们都不可取,他甚至认为“而智之流于诡者,其败尤甚”。由于狄仁杰不存在这些缺点,以正道自处,终于说服了武则天,使中宗得以复辟。故王夫之用十分赞叹的口气说:“斯狄梁公之所以不可及也!”《读通鉴论》卷21《中宗》五。王夫之的这种看法十分精辟,这正是狄仁杰既得以匡复唐室,又得以独善其身的最重要原因。我国古代士大夫提倡“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他们对那些能兼顾这两者的人十分推崇,认为只有这样的人才算达到儒家理想的最高境界。在这两者中前者是目的,后者则是基础,不能善其身自然就谈不上济天下。同时他们在观察问题时,不仅看效果而且还非常重视动机,如果一个人办事时虽然效果不错而动机不纯,也不能获得很好的评价。实际上在迎立中宗这件事上,不少人都出了力气,史籍中也有这样记载,但旧史臣却仍然认为“致庐陵复位,唐祚中兴,诤由狄公,一人以蔽。”原因就在这里。
宋人范仲淹也是一个十分推崇狄仁杰的人,他既是一个政治家又是一个文学家,所以他对狄仁杰的赞语写得十分得体,又不乏文彩,就把它作为本篇的结束语吧。范仲淹曰:
天地闭,孰将辟焉?日月蚀,孰将廓焉?大厦仆,孰将起焉?神器坠,孰将举焉?岩岩乎克当其任者,惟梁公之伟欤《宋文鉴》卷76《唐狄梁公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