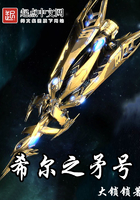敬爱的同志:
你译的《毁灭》出版,当然是中国文艺生活里面的极可纪念的事迹。翻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名著,并且有系统的介绍给中国读者(尤其是苏联的名著,因为它们能够把伟大的十月,国内战争,五年计划的“英雄”,经过具体的形象,经过艺术的照耀,而供献给读者),——这是中国普洛文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虽然,现在做这件事的,差不多完全只是你个人和Z同志的努力;可是,谁能够说:这是私人的事情?!谁?!《毁灭》《铁流》等等的出版,应当认为一切中国革命文学家的责任。每一个革命的文学战线上的战士,每一个革命的读者,应当庆祝这一个胜利;虽然这还只是小小的胜利。
你的译文,的确是非常忠实的,“决不欺骗读者”这一句话,决不是广告!这也可见得一个诚挚,热心,为着光明而斗争的人,不能够不是刻苦而负责的。20世纪的才子和欧化名士可以用“最少的劳力求得最大的”声望;但是,这种人物如果不彻底的脱胎换骨,始终只是“纱笼”(salon)里的哈叭狗。现在粗制滥造的翻译,不是这班人干的,就是一些书贾的投机。你的努力——我以及大家都希望这种努力变成团体的,——应当继续,应当扩大,应当加深。所以我也许和你自己一样,看着这本《毁灭》,简直非常的激动:我爱它,像爱自己的儿女一样。咱们的这种爱,一定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精力增加起来,使我们的小小的事业扩大起来。
翻译——除出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中国的言语(文字)是那么穷乏,甚至于日常用品都是无名氏的。中国的言语简直没有完全脱离所谓“姿势语”的程度——普通的日常谈话几乎还离不开“手势戏”。自然,一切表现细腻的分别和复杂的关系的形容词,动词,前置词,几乎没有。宗法封建的中世纪的余孽,还紧紧的束缚着中国人的活的言语(不但是工农群众),这种情形之下,创造新的言语是非常重大的任务。欧洲先进的国家,在二三百年四五百年以前,已经一般的完成了这个任务。就是历史上比较落后的俄国,也在一百五六十年以前就相当的结束了“教堂斯拉夫文”。他们那里,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做了这件事。例如俄国的洛莫洛莎夫……普希金。中国的资产阶级可没有这个能力。固然,中国的欧化的绅商,例如胡适之之流,开始了这个运动。但是,这个运动的结果等于它的政治上的主人。因此,无产阶级必须继续去彻底完成这个任务,领导这个运动。翻译,的确可以帮助我们造出许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丰富的字汇和细腻的精密的正确的表现。因此,我们既然进行着创造中国现代的新的言语的斗争,我们对于翻译,就不能够不要求: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中国白话文。这是要把新的文化的言语介绍给大众。
严几道的翻译,不用说了。他是:
译须信雅达,
文必夏殷周。
其实,他是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最近商务还翻印“严译名著”。我不知道这是“是何居心”!这简直是拿中国的民众和青年来开玩笑。古文的文言怎么能够译得“信”,对于现在的将来的大众读者,怎么能够“达”!
现在赵景深之流,又来要求:
宁错而务顺,
毋拗而仅信!
赵老爷的主张,其实是和城隍庙里演说西洋故事的,一鼻孔出气。这是自己懂得了(?)外国文,看了些书报,就随便拿起笔来乱写几句所谓通顺的中国文。这明明白白的欺侮中国读者,信口开河的来乱讲海外奇谈。第一,他的所谓“顺”,既然是宁可“错”一点儿的“顺”,那么,这当然是迁就中国的低级言语而抹杀原意的办法。这不是创造新的言语,而是努力保存中国的野蛮人的言语程度,努力阻挡它的发展。第二,既然要宁可“错”一点儿,那就是要蒙蔽读者,使读者不能够知道作者的原意。所以我说:赵景深的主张是愚民政策,是垄断智识的学阀主义,——一点儿也没有过分的。还有,第三,他显然是暗示的反对普洛文学(好个可怜的“特殊走狗”)!他这是反对普洛文学,暗指着普洛文学的一些理论著作的翻译和创作的翻译。这是普洛文学敌人的话。
但是,普洛文学的中文书籍之中,的确有许多翻译是不“顺”的。这是我们自己的弱点,敌人乘着这个弱点来进攻。我们的胜利的道路当然不仅要迎头痛打,打击敌人的军队,而且要更加整顿自己的队伍。我们的自己批评的勇敢,常常可以解除敌人的武装。现在,所谓翻译论战的结论,我们的同志却提出了这样的结语:
翻译绝对不容许错误,可是,有时候,依照译品内容的性质,为着保存原作精神,多少的不顺,倒可以容忍。
这只是个“防御的战术”。而蒲力汗诺夫说:辩证法的唯物论者应当要会“反守为攻”
。第一,当然我们首先要说明:我们所认识的所谓“顺”,和赵景深等所说的不同。第二,我们所要求的是: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白话。所谓绝对的白话,就是朗诵起来可以懂得的。
第三,我们承认:一直到现在,普洛文学的翻译还没有做到这个程度,我们要继续努力。第四,我们揭穿赵景深等自己的翻译,指出他们认为是“顺”的翻译,其实只是梁启超和胡适之交媾出来的杂种——半文不白,半死不活的言语,对于大众仍旧是不“顺”的。
这里,讲到你最近出版的《毁灭》,可以说:这是做到了“正确”,还没有做到“绝对的白话”。
翻译要用绝对的白话,并不就不能够“保存原作的精神”。固然,这是很困难,很费功夫的。但是,我们是要绝对不怕困难,努力去克服一切的困难。
一般的说起来,不但翻译,就是自己的作品也是一样,现在的文学家,哲学家,政论家,以及一切普通人,要想表现现在中国社会已经有的新的关系,新的现象,新的事物,新的观念,就差不多人人都要做“仓颉”。这就是说,要天天创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实际生活的要求是这样。难道1925年初,我们没有在上海小沙渡替群众造出“罢工”这一个字眼吗?还有“游击队”,“游击战争”,“右倾”,“左倾”,“尾巴主义”,甚至于普通的“团结”,“坚决”,“动摇”等等等类……这些说不尽的新的字眼,渐渐的容纳到群众的口头上的言语里去了,即使还没有完全容纳,那也已经有了可以容纳的可能了。讲到新的句法,比较起来要困难一些,但是,口头上的言语里面,句法也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很大的进步。只要拿我们自己演讲的言语和旧小说里的对白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得出来。可是,这些新的字眼和句法的创造,无意之中自然而然的要遵照着中国白话的文法公律。凡是“白话文”里面,违反这些公律的新字眼,新句法,——就是说不上口的——自然淘汰出去,不能够存在。
所以说到什么是“顺”的问题,应当说;真正的白话就是真正通顺的现代中国文,这里所说的白话,当然不限于“家务琐事”的白话,这是说:从一般人的普通谈话,直到大学教授的演讲的口头上说的白话。中国人现在讲哲学,讲科学,讲艺术……显然已经有了一个口头上的白话。难道不是如此?如果这样,那么,写在纸上的说话(文字),就应当是这一种白话,不过组织得比较紧凑,比较整齐罢了。这种文字,虽然现在还有许多对于一般识字很少的群众,仍旧是看不懂的,因为这种言语,对于一般不识字的群众,也还是听不懂的。——可是,第一、这种情形只限于文章的内容,而不在文字的本身,所以,第二、这种文字已经有了生命,它已经有了可以被群众容纳的可能性。它是活的言语。
所以,书面上的白话文,如果不注意中国白话的文法公律,如果不就着中国白话原来有的公律去创造新的,那就很容易走到所谓“不顺”的方面去。这是在创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的时候,完全不顾普通群众口头上说话的习惯,而用文言做本位的结果。这样写出来的文字,本身就是死的言语。
因此,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有勇敢的自己批评的精神,我们应当开始一个新的斗争。你以为怎么样?
我的意见是:翻译应当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确的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中国读者所得到的概念等于英俄日德法……读者从原文得来的概念,这样的直译,应当用中国人口头上可以讲得出来的白话来写。为着保存原作的精神,并用不着容忍“多少的不顺”。相反的,容忍着“多少的不顺”(就是不用口头上的白话),反而要多少的丧失原作的精神。
当然,在艺术的作品里,言语上的要求是更加苛刻,比普通的论文要更加来得精细。这里有各种人不同的口气,不同的字眼,不同的声调,不同的情绪,……并且这并不限于对白。这里,要用穷乏的中国口头上的白话来应付,比翻译哲学,科学……的理论著作,还要来得困难。但是,这些困难只不过愈加加重我们的任务,可并不会取消我们的这个任务的。
现在,请你允许我提出《毁灭》的译文之中的几个问题,我还没有能够读完,对着原文读的只有很少几段。这里,我只把弗理契序文里引的原文来校对一下(我顺着序文里的次序,编着号码写下去,不再引你的译文,请你自己照着号码到书上去找罢。序文的翻译有些错误,这里不谈了)。
(一)结算起来,还是因为他心上有一种——
“对于新的极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的渴望,这种渴望是极大的,无论什么别的愿望都比不上的。”更正确些:
结算起来,还是因为他心上——
“渴望着一种新的极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这个渴望是极大的,无论什么别的愿望都比不上的。”
(二)“在这种时候,极大多数的几万万人,还不得不过着这种原始的可怜的生活,过着这种无聊得一点儿意思都没有的生活,——怎么能够谈得上什么新的极好的人呢。”
(三)“他在世界上,最爱的始终还是他自己,——他爱他自己的雪白的肮脏的没有力量的手,他爱他自己的唉声叹气的声音,他爱他自己的痛苦,自己的行为——甚至于那些最可厌恶的行为。”
(四)“这算收场了,一切都回到老样子,仿佛什么也不曾有过,”——华理亚想着,——“又是旧的道路,仍旧是那一些纠葛——一切都要到那一个地方……可是,我的上帝,这是多么没有快乐呵!”
(五)“他自己都从没有知道过这种苦恼,这是忧愁的疲倦的,老年人似的苦恼,——他这样苦恼着的想:他已经27岁了,过去的每一分钟,都不能够再回过来,重新换个样子再过它一过,而以后,看来也没有什么好的……(这一段,你的译文有错误,也就特别来得“不顺”)。现在木罗式加觉得,他一生一世,用了一切力量,都只是竭力要走上那样的一条道路,他看起来是一直的明白的正当的道路,像莱奋生,巴克拉诺夫,图皤夫那样的人,他们所走的正是这样的道路;然而似乎有一个什么人在妨碍他走上这样的道路呢。而因为他无论什么时候也想不到这个仇敌就在他自己的心里面,所以,他想着他的痛苦是因为一般人的卑鄙,他就觉得特别的痛快和伤心。”
(六)“他只知道一件事——工作。所以,这样正当的人,是不能够不信任他,不能够不服从他的。”
(七)“开始的时候,他对于他生活的这一方面的一些思想,很不愿意去思索,然而,渐渐的他起劲起来了,他竟写了两张纸……在这两张纸上,居然有许多这样的字眼——谁也想不到莱奋生会知道这些字眼的。”(这一段,你的译文里比俄文原文多了几句副句,也许是你引了相近的另外一句了罢?或者是你把理契空出的虚点填满了?)(八)“这些受尽磨难的忠实的人,对于他是亲近的,比一切其他的东西都更加亲近,甚至于比他自己还要亲近。”
(九)“……沉默的,还是潮湿的眼睛,看了一看那些打麦场上的疏远的人,——这些人,他应当很快就把他们变成自己的亲近的人,像那十八个人一样,像那不做声的,在他后面走着的人一样。”(这里,最后一句,你的译文有错误。)这些译文请你用日本文和德文校对一下,是否是正确的直译,可以比较得出来的。我的译文,除出按照中国白话的句法和修辞法,有些比起原文来是倒装的,或者主词,动词,宾词是重复的,此外,完完全全是直译的。
这里,举一个例:第(八)条“……甚至于比他自己还要亲近。”这句话的每一个字都和俄文相同的。同时,这在口头上说起来的时候,原文的口气和精神完全传达得出。而你的译文:“较之自己较之别人,还要亲近的人们”,是有错误的(也许是日德文的错误)。错误是在于:(一)丢掉了“甚至于”这一个字眼;(二)用了中国文言的文法,就不能够表现那句话的神气。
所有这些话,我都这样不客气的说着,仿佛自称自赞的。对于一班庸俗的人,这自然是“没有礼貌”。但是,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和自己商量一样。
再则,还有一个例子,比较重要的,不仅仅关于翻译方法的。这就是第(一)条的“新的……人”的问题。
《毁灭》的主题是新的人的产生。这里,葬理契以及法捷耶夫自己用的俄文字眼,是一个普通的“人”字的单数。不但不是人类,而且不是“人”字的复数。这意思是指着革命,国内战争……的过程之中产生着一种新式的人,一种新的“路数”(Type)——文雅的译法叫做典型。这是在全部《毁灭》里面看得出来的。现在,你的译文,写着“人类”。莱奋生渴望着一种新的……人类。这可以误会到另外一个主题。仿佛是一般的渴望着整个的社会主义的社会。而事实上,《毁灭》的“新人”’
是当前的战斗的迫切的任务:在斗争过程中去创造,去锻炼,去改造成一种新式的人物,和木罗式加,美谛克……等等不同的人物。这可是现在的人,是一些人,是做群众之中的骨干的人,而不是一般的人类,不是笼统的人类,正是群伞之中的一些人,领导的人,新的整个人类的先辈。
这一点是值得特别提出来说的。当然,译文的错误,仅仅是一个字眼上的错误:“人”
是一个字眼,“人类”是另外一个字眼。整本的书仍旧在我们面前,你的后记也很正确的了解到《毁灭》的主题。可是翻译要精确,就应当估量每一个字眼。
《毁灭》的出版,始终是值得纪念的。我庆祝你。希望你考虑我的意见,而对于翻译问题,对于一般的言语革命问题,开始一个新的斗争。
JK1931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