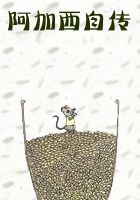5
黎文和涂龙在江边的小餐馆里吃了晚饭,闲着没事,便到录像厅里看录像消磨时光。不过,黎文惦记着黎明,揣摸着黎明有可能来找他,因此,看完一场香港的武打短片后就出来了。他对涂龙说:“到候船室或者囤船上逛一逛吧,这里面空气不好,闷得慌!”
涂龙明白黎文的真实意图,不便拒绝,于是,和黎文一道跑进了候船室。
长仁港是长江航道上较大的客运港,过往的乘客多,外面又下着雨,乘客都挤到不大的候船室里,他俩去的时候已经没有落脚的地方了。转了几个圈,他俩只好无奈地躲到大门边的廊檐下暂憩。
涂龙打量着黎文心神不定的模样,摸出烟,递一支给黎文,点燃,试探着问道:“哥,你见着黎明大哥了吗?”
黎文回答说:“见着了呀,他还拿了几百块钱给我!”
“才几百块?”涂龙不以为然地说。
“哥挣钱也不容易的,他本来找他们同事借了一千块钱要拿我做路费,我没要,还给他了。”
“干嘛还?真笨!”
沉默着,一支烟很快抽完了。
轮船驶来,拉响汽笛,停靠在囤船边。乘客开始陆陆续续地跨过浮桥上船。
涂龙起身,说:“走吧,哥,录像里说得好,自己有才是真的有,什么兄弟呀、姐妹呀、父母呀、朋友呀,只要你穷了,就不会有人把你当成人看待的。我知道你在等你哥,你以为他会冒着雨赶来送你一程?……别太傻了,他不会来的。你去见他的时候我就猜着了,他不但不会来送你,甚至连晚饭也不会请你吃。你是谁?他又是谁?差距大了,弟兄之间就没有平等!……好了,走吧,出门挣钱,挣了钱再回来娶媳妇,那才是硬道理!”他伸出手去拉黎文。
黎文自个儿站了起来,他寻思着涂龙的话,说道:“哥很忙,不是不想请我吃晚饭,他叫我等他的……”
“嘿,当官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你去相信他们。我问你,你哥工作到底有多忙?假如他真想请你吃晚饭,真想来送你,难道这点时间还抽不出来吗?他是怕你丢他的脸面呀!”
黎文琢磨,涂龙的话或许有道理,要不黎明咋两三年了都没有回一趟老家来看自己?人是会随着地位和身份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虽然他并不清楚黎明是否真的当了官,但凭直觉他还是推断出黎明的确变了,变得已经不再是几年前那个在任何场合和任何地方都可以随随便便地叫一声“哥”的哥了。这种推断恰好戳着了他的痛处,因此,他咬咬嘴唇,说:“走吧,上船!”
闷闷不乐地上到轮船上,又闷闷不乐地找到房间和床铺,黎文的心里仍不踏实。他抱着一线希望,出船舱来,斜倚着船舷,呆呆地望着江边码头高高的石阶。他指望着在风雨飘曳的灯火中,能在那长而陡峭的石阶的尽头,隐约地出现黎明的身影,哪怕只那么一瞬间,只那么一个模糊的轮廓……
汽笛迎着喧嚣的河风再次拉响了。
轮船缓缓地驶离岸边,然后在江心掉转头,震荡起发动机粗犷的轰鸣,划破澎湃的波涛,向着峡谷纵深处驶去……
风猛烈了,雨点斜打在身上,使人感到了阵阵寒冷。
涂龙来叫黎文进船舱里去。他说:“哥,外面冷,进去吧!再过几天我们就到沿海了。我们有了一份工作,也可以凭自己的劳动挣钱,那该多好啊!听打工的回来讲,沿海的工作好找,只要吃得苦,就能找到活儿干。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挣到了钱,那么我们就扬眉吐气地回来吧!身上穿着笔挺的西服,脚上蹬着雪亮的皮鞋,再在腰里别一个手机……嗨,浑身爽透,岂不快哉!什么女人,什么洋房,什么沙发、彩电……应有尽有,日子保证过得不比城里人差。我说我到沿海去挣钱,老妈子怎么也不答应,她呀,老了,看不清形势。沿海是开放城市,经济发达,哪里像我们这儿,穷山恶水,挣一分钱比登天还难……不走出去永远是贫穷,与其呆在家里穷一辈子,倒不如出门去闯一闯。好了,进去吧,别再去想不愉快的事,我俩是患难兄弟,一块儿出门,就一块儿高高兴兴地挣钱过日子,你说是吗,哥?”
黎文回头,说:“是呀,这一出门,就没有多的亲人了,是死是活,全靠我们自己。即便是大哥大姐和你母亲想到了要帮我们,也是远水不解近渴的……”他将双手放到涂龙的肩膀上,凝视着漆黑的夜空,喘了一口粗气,“人的命是一个不定的数,也许我们此行走正确了,也许我们此行走错了,但无论如何,是没法回头的。小时候爸爸常对我说,人的一生成功也罢,失败也罢,关键的往往就那么几步。比如我哥吧,他没考上大学,能有今天吗?可惜自己不争气,不能也像他那样考上大学,要不怎么会此时此刻独自为背井离乡感伤呢!”
“嗨,哥,别说丧气话好吗?走,睡觉!”涂龙害怕继续说下去黎文的心里会更加难受,因此,反手抱住黎文的腰,一边嬉笑着,一边连推带攘的将黎明拖进了船舱。
6
船到滨江,天已大亮。吃过早饭,黎文和涂龙便赶到滨江火车站去买火车票。他俩原是打算到深圳去的,不曾想到前往广州方向的乘客特别多,车票早已售完了。在露天广场逗留了半天,涂龙突然有了新的想法。他对黎文说:“哥,出门打工,干嘛死心眼的非要到哪儿去不可呢,依我看呀,哪个方向的车票好买,我们就到哪儿去!”
黎文觉得涂龙的话有道理,于是又到了售票处。经打听,只有福州方向的列车还有空余的车票,因此,商量一下,便买了车票拿定主意去福州。
晚上10点,火车驶离了滨江,驶离了滨江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流光溢彩的万家灯火……
两天后,他们到了福州。
踏上陌生的土地,站在火车站门前高大的榕树下,他俩既感到兴奋和激动,同时也对未来充满了惶惑和淡淡的忧虑。他俩把行李寄放在一家小旅店里,办理了住宿手续,然后,便匆匆忙忙的出去寻找劳务市场。初来乍到,劳务市场是他们惟一的希望和依靠。
福州的外来打工人员不是很多,找一份活干也不存在太大的问题。正好福州兴旺氮肥厂改制并准备扩建系列分厂,需要招聘大量的外来合同工,因此,他俩很快就和厂方签订了用工合同。
他俩被安排到装包车间,具体工作是负责将成型的氮肥封装成袋。那是氮肥生产的最后一道工序,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上呛人的氨气,实在地说,要不是为了挣钱吃饭,是没有多少人愿去干那差事的。因此,整个车间里几乎全是外来的打工仔和打工妹。
他俩刚到,就有不少的工友来向他们问这问那的打听情况,诸如从哪里来,家中还有什么人,吃住在哪里,月工资多少,和厂里当官的有啥关系等。能回答的他俩尽可能的都作了回答;不能回答的便一笑了之。其中有个打工妹叫韩静,长得清纯美丽,又十分善解人意,深受大家敬重。韩静听说黎文和涂龙是从滨江长仁来的,又得知他俩还没有找到住宿的地方,便主动将她隔壁空着的一间房屋介绍给他们,要他俩租下来,和她住在一块儿。
韩静说:“我也是滨江的呢,家在岭南,我们住在一块儿彼此好有个照应呀!”
岭南和长仁一山之隔,是真正的近邻,因此,黎文高兴地说:“是吧,那咱们是
老乡了。”
听说是老乡,涂龙立刻手舞足蹈起来,他说:“既是老乡,就总得找个合适的称呼呀,比如哥呀、姐呀、兄弟呀什么的,反正不能老是叫‘喂’,或者‘你’吧,那样听起来多生分呀。出门呗,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一个老乡呢,就多一张嘴,帮不了啥大忙,总之,关键时候能站出来说说话也行。你说是吗,韩静姐?”
他甜甜地微笑着,望着韩静。
韩静爽快地回答道:“好啊,只是不知道你们到底是我的大哥呢还是我的小兄弟!”
“当然我是你的小兄弟了,我才18岁呀!不过嘛,哥的岁数可能比你大,你应当像我一样叫他哥!”涂龙抢先说。
“你多大了?”韩静问黎文。
黎文憨厚地笑了笑,说:“再过3个月就22岁了。”
“呵,那是大哥,我年底满20岁。好,以后我就叫你哥,叫涂龙兄弟。”韩静说着,将目光转向涂龙:“记住,你以后只准叫我姐,不准再‘喂’和‘你’了,更不准直呼‘韩静’,否则我不会答理你的!”
“放心吧,姐,我巴不得找一个漂亮的姐姐关心我呢!”涂龙油腔滑调地说着,朝韩静扮了个鬼脸。
黎文和涂龙去旅舍取回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行李,住到了韩静的隔壁。自那以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格外的亲密了。轮到一个班,黎文和涂龙就总是抢着扛包的重活干,尽量让韩静只做封袋的轻活。如果不同时当班,在家休息的则把饭菜弄好,然后一块儿吃,一块儿出门玩。
韩静到福州大半年了,是头一年的秋天来的,对福州的情况以及风土人情较为了解,她一再告诫黎文和涂龙,千万不要去和当地人过多交往,也不要去和外来的不熟悉的打工人员过多交往。她说:“当地人大多有钱,一般是不会下苦力气挣血汗钱的,他们瞧不起外来的打工人员,你和他们搅在一块,最终吃亏的总是你自己。再说,沿海的治安秩序复杂,闹不准就搅进了什么团伙,命丢了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而外来的打工人员呢,又分别来自不同的地方,背景深奥,关系复杂,除了老乡,极少有去和别人套近乎的。因为彼此不了解,所以相互间就没有了信任。外出打工,并不一定都是为了挣钱,有的是在老家犯了案,跑出来躲藏的;有的又是想多生孩子,跑出来偷生二胎或三胎的。像车间的张**,就是带着一家老小打算来再生一个小孩的。总之,不熟悉就最好不要往来,干自个儿的活,挣自个儿的钱,吃自个儿的饭!”
听了韩静的话,涂龙把舌头伸得长长的,故作惊讶道:“妈呀,早知如此我就不来了!”
黎文说:“别妈呀娘呀的,你韩静姐讲的话务必要记住,你和我一样,没出过远门,外面的水到底有多深,是一个未知数。你在老家的时候不安分,到了这儿,不能再犯**病了,该管住的手要管住,该管住的脚也要管住。”
涂龙听出了黎文话中的真实含意,于是叫嚷道:“哥,咋老是提过去?我长大了,有主见了。放心吧,我不会给你和韩静姐惹事添麻烦的!”
黎文说:“但愿吧!”
不过,话虽如此说,黎文对涂龙却仍是压根儿不放心的。涂龙不仅喜欢占点小便宜和顺手牵羊的搞点小偷小摸,而且也时常喜欢玩牌搞赌博。独生子,从小娇生惯养,父母都管不了,何况是黎文呢!当初相邀着出门,黎文就没有答应,是涂龙再三保证了要改好,他才同意来的。既然一块儿来了,他就得对涂龙负责。要是涂龙有个三长两短,他怎么好回老家去向涂龙的母亲做交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