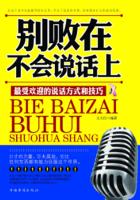向爸爸道别
1975年9月19日,由画院出面,在龙华火葬场为这位前任院长举行了一次追悼会。这时,周恩来同志病重,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时,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因此,追悼会总算在大厅中举行。画院里的老画师们,凡是走得动的,几乎都来参加了。他们在“牛棚”里共过患难,都怀念着这位于世无争的老画家。
送花圈的人很多。那时的花圈只有纸的,有一个却是鲜花的,用我们家乡称为“千年红”的小紫花球组成。我一看,原来是刘海粟先生请人送来的。后来得知刘先生当时正患重病,作诗曰:
暮年兄弟少,悲君亦自悲;泪雨满床头,真梦两依稀。
事后,刘先生在《怀念丰子恺先生》一文中说:
那时候养花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到处买不到鲜花。我刚巧领到一个月的伙食费,便请人跑到虹口公园费了不少唇舌,买花扎成一个花圈,托一位有正义感的学生吴侃送到龙华火葬场殡仪馆。……子恺……和他的艺术是有生命有气节的真花!……真花能留下种子,馨香远播,秀色长存,沾溉后学,美化世界,歌颂青春!
国内报刊上对这位海内外闻名的艺术家的逝世毫无反应,倒是由于我们通知了爸爸的方外莫逆之交新加坡广洽法师,在新加坡《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上登出了两条消息。到1976年的2月13日,香港《大拇指周报》上出现了两版“丰子恺先生纪念专辑”,发表了明川的《不悲不恸悼先生》和香山亚黄等人所写的《悼以外》、《迟来的噩讯》等悼文。
爸爸的老友叶圣陶先生得知噩耗后,寄来一首诗:
故交又复一人逝,潇洒风神永忆渠。
漫画初探招共酌,新篇细校得先娱。
深杯剪烛沙坪坝,野店投书遵义庐。
十载所希归怅恨,再谋一面愿终虚。
……
追悼会后,我整理了爸爸留下的可怜的书画遗物,全部拿出来,对姐姐们和兄弟们说:
“你们挑!吧,剩下的给我。”
我们对这些东西谁也不争。各人!了自己喜欢的书画作品和书,我拿了剩下的一幅小书法和一些日文书(日文书后来都捐给缘缘堂了)。大哥!了一些图章,余下的图章由弟弟拿去保存了。
爸爸给我们每个子女都画的那套四季屏,我的一套被美术学校的学生抄家时抄走了,所以当时爸爸的画在我手头一张也没有。数年前,我二哥送了一幅小画给我,我受宠若惊,如今一直挂在我书桌左壁上。
爸爸去世后我拿到的一幅小书法——陶渊明的四句诗“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则挂在右壁上。当时我!取这幅小书法,只是因为爸爸在那套“精品”画中有一幅是画我,画题正是用的这四句诗。如今这四句诗悬诸左右,正好成了我的座右铭。十余年前,我把这幅画清除颜色,印在我的名片反面。我的晚年就是在爸爸这四句诗的勉励下度过的。我为研究爸爸的生平和创作,从未浪费过一分钟。因为“岁月不待人”啊!尤其不待我这80岁的老妪!
重见天日
我想说的不是中国人民重见天日,那种欢庆就不必谈了,那不是从内地回到江南故乡的欢乐,而是从地狱回到天堂的欢乐。我在这里只谈爸爸的画重见天日。已经有12年了,报刊上看不到爸爸一幅画、一篇文。
1978年4月23日的《文汇报》“风雷激”副刊上忽然登出了爸爸的一幅《山到成名毕竟高》。亲友们奔走相告,家属们欢喜雀跃。其实那并非为专门介绍丰子恺的画而登出的。那幅画只是作为插图陪衬一篇文章。文章题目叫《数学家的诗篇》,作者是复旦大学陆士清,内容是歌颂苏步青先生的。只因《文汇报》有一位先生持有此画,他想让12年没和读者见面的丰子恺露露面,便作为此文的插图悄悄地“塞”了进去。这一炮打得好!爸爸的作品重见天日了。
由于这幅画下面载了“丰子恺遗作”五个字,看到报纸的读者方才知道他们所敬仰的老画家已经不在人世。爸爸去世后新加坡、香港等地的报道,当时国内是不可能看到的。全靠这幅画登了出来,起了讣告的作用。在他生前,老友叶圣陶、钱歌川先生先后来沪时曾要求和他见面,陪同的人都不让见,使爸爸失去了与老友诀别的机会。
就在这1978年,广洽法师从新加坡来上海,致祭于爸爸的灵前,洒了一地泪水。香港中文大学老师卢玮銮小姐(笔名明川、小思,后为中文系教授)来到上海,在她慕名已久而终未谋面的艺术家遗像前泣不成声。还有难以计数的虔诚的读者为一代艺术家写悼诗,表哀思。
1978年年末,上海文艺出版社为《往事与哀思》一书来约我写一篇回忆爸爸的文章。我从来没有写过文章。他们介绍我去向王西彦先生请教。1979年1月,我写出了《回忆我的父亲丰子恺》一文,近一万字。
1980年,那时我刚从上海译文出版社转到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室,不久就有浙江文艺出版社来向我和宝姐约稿,要我们编《丰子恺文集》(7卷本,其实就是全集)。1990年9月,文集艺术卷4本出版(共322篇文),1992年6月,文学卷3本出版(如日记一天算一篇,诗词和书简一则算一篇,则共753篇)。全集共3184000字,收1075篇。由于我身在外国文学研究室而做的却是“丰研”工作,就没有评上高级职称。退休后补申请,才得了一个“副译审”的空名衔。
文集出版后,宝姐和我就开始计议编《丰子恺漫画全集》。其实从1988年开始,我们就已开始在徐家汇藏书楼里啃面包找资料了。1998年正逢爸爸百岁诞辰,京华出版社得知我们正在编漫画全集,便来约稿。1999年2月出版,起初出16卷本,共收漫画四千多幅。2004年4月又出9卷本。
到我写这段文字时,重新出版爸爸作品的书已经多达162种。研究介绍他生平作品的书也已有85种。还有拍成电视介绍他生平和作品的纪录片也已有13个。
妈妈也走了
爸爸1975年离世后三年,我的小家庭和母亲就于1978年5月23日搬到了漕溪北路。那时还没有可以买卖房屋的规定,要搬家,只能以房易房。漕溪北路当时是市稍,不大有人愿意把市区的房子换到这里来。但我们看中了这里的房子是一套套单独的,不必爬楼梯。我们急于离开是非之地,所以通过画院由文化局替我们调换成功了。
妈妈搬到这里,高兴极了。因为陕西南路不仅已有了三四家邻居,而且我们住在二楼,厨房却在楼下,很不方便。有一次妈妈在床上呕吐,双手捧着污物,叫唤厨房里的保姆凤珠阿姨却叫不应。一直等到我女儿放学回来上楼才看到。如今一家人和厨房洗手间都在一个平面上,妈妈不仅唤人方便,还可以到厨房去看看煮什么菜,上厕所也不必跨几步扶梯。
妈妈在这里度过了5年安稳的生活,于1983年4月10日去世。她比爸爸寿长10年。爸爸是虚龄78岁去世,妈妈则是88岁去世。妈妈是1980年跌了一跤骨折,躺了几个月后虽能搀扶着走路了,但终于因脑血栓而去世。
由于那时我在爸爸的事上已开始忙起来,所以服侍妈妈的主要是我丈夫阿崔(崔锦钧)他当时已退休回沪。他是至孝的人,而且吃苦耐劳。我至今还记得送妈妈去龙华医院复查接骨情况时的情况。那时不但没有私家车,连出租车也无法叫到。我们雇了一辆“黄鱼车”,就是人踩的三轮货车,由宝姐扶着让妈妈平躺在车上去医院。黄鱼车踩得很快,我跟不上。六十多岁的阿崔硬是小跑步紧紧跟随着。虽是隆冬,到达时他满头大汗。得知接骨情况良好,可以慢慢锻炼了。那时也是阿崔双手搀着妈妈双手,自己退走,在走廊里甚至扶梯上慢慢地让她锻炼。妈妈后来得了老年痴呆症,发作最厉害时大骂我和阿崔,这是患这种病的人的特征之一。不过不发作时还和常人一样。
我和宝姐在妈妈已不再能走动只能坐在椅子上的一段时期内,经常陪妈妈说话解闷,还利用录音机把我们说的话录下来。例如给她念诗词,念心经,讲故事等等。宝姐不来或我没空时,我就把录音重新播放。妈妈青光眼,“文革”时期一只瞎了,开了刀,保留了另一只,那时也不大看得清楚了。她以为我们又在她身旁讲了。录音机这东西真管用。
妈妈长期卧床时,我们怕她生褥疮,异想天开地把她的上半身垫高。那时元草哥正好回沪探亲。我们两人去买来一些沙发内用的棕榈条,加上棉花,加上布套,制成了一块十几厘米高的正方形的床垫,让她的上半身睡在这垫子上。我买来一个橡皮扁马桶放在她的下半身。这样,既解决了大小便问题,又不至于生褥疮。
可是,千方百计,还是留不住妈妈。有一天她突然没声音了。赶快送淮海医院,才知她得了脑血栓。经医治后出了院,我们托卢永高先生买来一只医院用的病床,可以摇起来让她换换姿势的。可是这床才睡了几天,1981年4月10日半夜,妈妈说了一句模糊不清的话,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事后,我一直在想妈妈最后说的那句话。共5个字,发音是“我拂神功了”。那时新枚正在上海。我们琢磨了一阵子,恍然大悟。妈妈是要告诉我们“我不行了”。用石门话来说,是“我不成功了”。“成功”在石门话里是“行”的意思。我至今一直在想:人凭什么感觉知道自己快死了?在电视里常看到快死的人往往有此预感。可从来没有人再活过来告诉我快死时是什么感觉,就像从来没人死了又活过来告诉我究竟有没有“阴间”?有没有“天堂”?有没有“地狱”?有没有“轮回”?
唉,这些都不去想它了。在世的时候好好做一个人,多帮助别人,多造福人类,这才是现实的事!
重建缘缘堂
爸爸在《还我缘缘堂》一文中说:
“在最后胜利之日,我定要日本还我缘缘堂来!”
可是,日本终于没有还我缘缘堂。缘缘堂是靠我们政府自己和新加坡广洽法师的捐款造成的。
1983年2月,故乡传来雪恩娘病危的消息。我和阿崔赶到南圣浜去看她。后来她去世了,我家竟未去人。为了此事我遗憾终生。在这方面我受爸爸影响太深。爸爸一直强调要慰问活着的人,要善待活着的人,不要在去世后做形式上的一套。我则变本加厉了。连葬仪也没去参加。乡下的人对此是很重视的:娘舅家怎么没人来?后来我向表弟正东致歉时,他反而十分宽容地安慰我说:“你们忙啊!”唉!再忙也不该忘了礼仪啊。
就在我和阿崔探望雪恩娘经桐乡将回沪时,桐乡宣传部副部长吴珊同志和我们谈了一件事。她说:她快要退休了,但在退休前要办两件事,一是开放茅盾故居,二是重建丰子恺故居缘缘堂。
这个消息做梦也没想到。爸爸要日本“还我缘缘堂”,抗战胜利到1983年已经38年了,日本不还。桐乡却没有忘记运河之水哺育成长的一代艺术家,发起要重建他的故居。我马上把这好消息告诉新加坡广洽法师。法师汇来三万元助建。那时三万元已够建造缘缘堂的房子。但要造就得造在原地,而原地已建造着一家玻璃纤维厂。要让他们搬走,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要给他们另置土地,还得付拆迁费等等。这一大笔就由政府包下来了。
1985年9月15日爸爸去世10周年那天,举行缘缘堂落成典礼。广洽法师亲自从新加坡来石门参加典礼。各地来的宾客不计其数。石门镇万人空巷,争着观看这盛典。
缘缘堂对外开放后,海内外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
就在这一次,广洽法师离开石门后就到杭州,把6册《护生画集》的字画原稿各450幅无偿捐献给浙江省博物馆,于9月17日举行了捐赠仪式。这套《护生画集》后来出了种种版本,深受读者喜爱。
爸爸魂归故里
这一节的内容,我要借助二姐之子宋雪君和大姐之女杨朝婴的文章(登在丰子恺研究会《杨柳》内部资料上的)来向读者交代。是的,出版这本传记时我已80岁,是该由下一代来接班了,何况爸爸骨灰归故里时我正生病,没有随车同去。下面是宋雪君登载在2006年3月《杨柳》第56期上的文章《丰子恺骨灰归故里》的全文:
我们的外公丰子恺,于1975年9月15日在上海逝世,1979年6月28日,骨灰安放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革命干部骨灰室。
外公是在十年浩劫中惨遭迫害含冤去世的。他的在天之灵也许知道,读者始终都在怀念他。2002年起,由他的大部分亲属主办了“上海弘丰文化艺术公司”,开设了“丰子恺艺林”,大力弘扬丰公的艺术。现在,他最大的愿望也许是早日叶落归根吧。是的,外公1975年春曾回故乡,至今已三十多年了,应该回家了。
2006年3月11日,我们丰公的第三代一行8人,担负起了护送外公骨灰回家的重任。他们是:外孙宋雪君、乐岚夫妇,外孙女杨朝婴、倪培良夫妇,外孙杨子耘、施雅芳夫妇,外孙女崔东明等。8时30分,我们开着两辆小汽车到达龙华烈士陵园,将骨灰箱从安放处冷冰冰的箱柜中小心翼翼地取出。朝婴说:“外公,我们带你回故乡去了!”然后将骨灰装入一个大红布袋,放到子耘驾驶的汽车内。雪君驾驶的汽车在后护送,徐徐起步,踏上了回乡之路。
不久,比天气预报提前而至的春雨飘洒而下,似乎也早早赶来为外公送行。一路上,外孙女、外孙媳们不停地向外公介绍经过的地方,还要仔细地说明一些外公也许听不懂的名字如立交桥、高速公路等,当然还要介绍外公当时还不认识的第四代甚至第五代。外公的后代再也不会遇到像“文化大革命”这种黑暗的时代了,他的后代现在已挑起大梁,要继承和弘扬丰公的艺术了。
丰公的研究工作已经在社会上广泛开展,相信一定能够千秋万代流传下去。
十时多,两辆汽车奔波近160公里,到达浙江省桐乡市石门镇外公故居缘缘堂。缘缘堂的负责人工作人员褚万根、姚震天二位冒雨出来迎接并放鞭炮。大家隆重地将外公的骨灰送进缘缘堂正厅灵台上,正面放上照片,两侧是花篮,桌上放满供品。全体三鞠躬。就这样,外公的骨灰事隔三十多年,顺利到达故居,完成了他的一个心愿。今年4月22日上午,骨灰将安放到南圣浜原来的衣冠冢内,与我们的外婆、二位姑外婆合葬在一起。墓地现正由政府大加修缮。那时,必然面目一新,而且还会有更多的亲属朋友前来参加葬礼。
宋雪君执笔2006年3月12日
接下来,是杨朝婴登载在2006年6月《杨柳》第57期上的文章《外公丰子恺魂归故里》的全文:
2006年4月22日,早就预定好的、盼望已久的这一天,我们亲属和朋友在浙江桐乡石门镇南圣浜,将外公的骨灰盒安葬在重新修葺过的墓地中。终于,自1975年外公最后一次回故乡看望亲戚后时隔31年,外公魂归故里,入土为安。
上海、杭州、香港,很多亲属参加了这次仪式。总共大约有60人:丰公的孙子丰羽一家,我母亲(丰陈宝)和我家、我弟弟子耘一家,先娘姨一家,软娘姨一家,小娘姨一家,秋娘姨一家及咬胜娘舅和咪咪娘姨,卢永高伯伯夫妇,一共开了6辆车过去。再加上当地的亲戚,桐乡、嘉兴两地的领导和有关人员,还有两地的电视台记者,热闹得很。
众人先到石门镇的丰子恺故居缘缘堂,由丰羽郑重地捧出丰公的骨灰盒,上车开出时放鞭炮。
墓地在离开石门镇不远的南圣浜,今非昔比,已由当地政府修缮一新。虽然还没有完工,但其设计看得出很符合外公一贯的作风:简洁,明快,大方。一条青青的石板路,两行葱葱的松柏树,直通微微高起的墓地。墓地上地面已经平整,还添了石凳供人小坐。环绕四周的松柏是当年雪姑母的儿子正东娘舅亲手种下的,如今已经高大无比,像高高的华盖,保护着长眠地下的外公外婆和姑外婆们。据当地人说,这里风水很好,这使我们心里更多了一点安慰。
嘉兴市的党委副书记发言,说得很有人情味;还有桐乡市的领导等等都讲了话,最后是丰羽代表家属致辞,言简意赅,出口成章。他们除了称颂外公在绘画、音乐、文学、翻译等领域的成就外,更多的是对他人品的赞扬。是啊,看到太多的勾心斗角、争名夺利、尔虞我诈、贪赃枉法……回头再看看外公的一生,他的朴实正直、淡泊名利实在令人敬佩和景仰。
丰家的后代很少有做生意或做官的,读书人居多,而且大多心境平和。他们在求知和做学问方面锲而不舍,而对物质生活则知足常乐。虽然这年头老实人往往吃亏,可丰家的后代们仍然按照外公的轨迹走下去,一直走下去,第三代、第四代……
仪式结束后,镇领导在桐乡东方大酒店设宴招待各方人士。宾主频频举杯互相致谢,倍感暖意融融。
昨晚下雨,大家都很担心今天的天气。我们出发时还下着毛毛雨;仪式开始时就好转了,甚至出了一点太阳。
是的,太阳也想窥视一下永远活在读者心里的这位大艺术家的落葬仪式啊!
潇洒风神永忆渠
随着春回大地,纪念活动日益频繁。
1981年5月9日至22日,在上海美术展览馆举行丰子恺画展,展出其遗作彩色漫画数百幅。
1984年8月19日,宝姐和我发起成立了“丰子恺研究会”。参加者有毕克官、毕宛婴父女,殷琦,曾路夫,陈星,胡治均,潘文彦,丰陈宝,丰宛音,丰元草,丰一吟共11人。印发内部参考资料《杨柳》。
1987年12月3日至8日,在新加坡大会堂举行“丰子恺遗作书画展览”,观众空前踊跃。
其他各种形式的展览不胜枚举。在爸爸诞生100周年时,桐乡、上海、杭州、绍兴都展出他的作品或以不同形式纪念他。
1992年5月3日,浙江省桐乡县(1993年改为市)文联正式成立“丰子恺研究会”,继续给会员印发《杨柳》。
1996年11月9日(丰子恺诞生98周年之际),浙江金华我们丰姓的祖地汤溪成立了“金华丰子恺研究会”。1998年丰子恺诞生100周年时又隆重纪念,在黄堂丰姓五村的中心地立了一块纪念碑,上刻“丰子恺祖地”5个大字。背后的碑文记载了丰子恺是从黄堂迁往石门的丰圣文的17世孙。
1997年10月30日,杭州师范学院(今杭州师范大学)成立了“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不仅研究丰子恺,还研究他最敬爱的老师李叔同弘一大师。由陈星担任主任。每逢诞生或逝世的重要之年,总举行种种纪念,吸引国内外的丰研专家们前来参加学术研究会或其他活动。
1998年爸爸诞生100周年时,在缘缘堂旁边建造了“丰子恺漫画馆”。
2000年6月,桐乡创刊了《缘缘漫画》杂志。
同年11月,丰子恺漫画学校在桐乡成立,并开始举行一年一度的丰子恺故里漫画周。
2001年11月,桐乡成为“中国漫画之乡”。同年举行首届“子恺杯”全国儿童漫画大赛。
2002年12月26日,丰公后代合力出资在上海创办了一家画廊性质的店面,叫“丰子恺艺林”,后来又成立了“上海弘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艺林”归属该公司,供应一切与丰公有关的书画艺术品。
“丰子恺艺林”位在中山西路玉屏南路口的天山茶城三楼,由宋雪君、杨子耘和我主持其事。其他亲属都为这家店贡献自己的力量。两外甥各有各的职务,我也忙于丰研工作。没人有空考虑做宣传工作,也没钱做广告。居然凭着爸爸的艺术名望,支撑到今天已有6年了。我只要有空不生病,每周六下午3至5时总去坐坐。我在这里不仅遇到了旧朋友,而且认识了很多新朋友——爸爸的读者,乐莫乐于新相知,有不少顾客还成了我们的好朋友。
2005年丰子恺艺术幼儿园开园。
2008年3月,由桐乡团市委成立了“子恺少年漫画院”,由一位从山东来桐乡落户的“丰迷”青年吴浩然担任漫画授课老师,教少年们课余专门学习子恺漫画。
桐乡的种种有关丰子恺和他的漫画的纪念和宣传是说不尽的。
如今,爸爸诞生110周年,更有一番隆重纪念。我谨以这本拙作敬献于爸爸灵前,聊表女儿的一点孝敬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