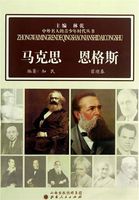土墙仓房的屋檐上,一群燕子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天色已暗,老燕子似乎还在不断给巢中的小燕子搬运食物。“这可以作为画画的题材吗?”隔着宽敞的中庭,在一间居室里,明智的老臣齐藤利三对客人说。客人是位叫海北友松的画师,不是诹访的人,大约五十岁吧。体格不怎么像画师,沉默寡言。暮色之中,只有在几个大酱仓库的白墙那里还能看到一点儿光亮。
“哎呀,在战争之中突然到访,光是跟您聊一些世外人的闲话……请多原谅,您一定军务繁忙吧。”友松似乎想告辞,开始从坐垫上向后退。“没事啊。”齐藤利三非常稳重,他稳稳坐在那里挽留道:“您好不容易来一趟,怎么能不见一下光秀大人就回去呢?主公回来之后,如果我禀报说他不在的时候您来过,他一定会训斥我为什么不留您。您再稍等一下吧。”他特意谈起新的话题,来挽留这位不速之客。
海北友松现在已经在京都安家,其实他是江州坚田人,也就是说出生在光秀统领的坂本城附近,有这样的渊源。不仅如此,友松以前是个武士,曾供职于岐阜的齐藤家,因此当时就和齐藤利三很熟。因为利三在跟随明智家以前也曾侍奉过齐藤一族中骁勇闻名的稻叶伊予守长通。
友松流浪一段时间之后,开始了画师生活,很明显的原因在于岐阜灭亡了。利三抛却旧主成为明智家的家臣,其中有很复杂的内幕,旧主与光秀之间的纠葛甚至被拿到信长那里接受裁决。可是现在人们都忘记了当时轰动一时的传言,人们看着他那苍白的鬓发,都会尊敬他的重要地位和人品,认为他是明智家不可或缺的人。
信长的营部所在的法养寺,住不下所有的人,因此一部分将士被安排到诹访镇上的百姓家中。明智的队伍驻扎在这个破旧的大酱批发店里,将士们刚刚从数日征战的疲劳中解放出来。房东儿子过来对留守家中的齐藤利三说:“家老大人,您不洗澡吗?武士们包括走卒们都已经用过晚餐了。”
“不,我要等将军回来。”“将军大人可能会很晚吧?”
“今天啊,营部那边举行庆功宴呢。将军虽然不能喝酒,也要喝不少呢。估计是太高兴了,喝醉酒了吧。”
“那您先用晚餐吧。”“不不,将军回来之前,我也不想吃饭。但是这样一来,就太对不起好不容易挽留下来的客人了。先把客人带去浴室吧。”“您是说白天到访的过路画师吗?”“是啊,他一个人蹲在牡丹花田那里,百无聊赖地看牡丹呢。你过去叫一下他吧。”房东儿子退下去了,然后绕到房后看了一下。海北友松孤单单地抱膝而坐,凝视着盛开的牡丹。过了一会儿,齐藤利三从柴门出去的时候,房东儿子与友松都已不在那里。
其实利三开始有些担心了。主公回来得太晚了。因为是庆功宴,估计今天是一个大盛会,所以会持续很久,尽管如此,他还是感觉到了一些不安。走出茅草顶的大门,就是一条湖畔的大道。诹访湖西面的天空中,夕阳的余晖还有些光亮。齐藤利三站在道旁,朝远处眺望了一会儿。
也没什么好担心的,很快,他的主人就朝这边走来,率领着一群侍臣,牵着马、拿着长枪。然而,随着他的身影临近,齐藤利三的眉毛又拧起来了。因为他感觉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气氛,看上去不像是从庆功宴回来的人。本应当英姿飒爽地骑在马上,那些侍从今天也应当喝醉了酒热热闹闹的,然而光秀却悄然徒步而归。小厮牵着他的马,闷闷不乐地走在后面,侍从们也同样垂头丧气地默默跟在身后。
“我到这里来迎接您了。您累了吧?”利三上前躬身道。光秀似乎吃了一惊,抬起头来说:“是利三啊!是我考虑欠周,回来晚了,让你担心了。抱歉,抱歉!今天酒吃多了,为了醒醒酒,特意沿湖畔走回来的。虽然脸色有点苍白,不用担心,我现在舒服多了……”
看来他遇到了不快的事情。齐藤利三在主人身边服侍多年,不可能瞒过他。可是他并没有多问,这位老臣费尽心思想要宽慰一下主人,进入寝室后,依然在主公光秀身边照料。
“先坐到那边喝杯茶怎么样?还是换衣服的时候顺便洗个澡呢?”利三到了战场上,足以令敌人闻风丧胆,堪称猛将,此时却不用小厮帮忙,亲自为光秀换衣服。这位老臣如同和蔼的岳父一般照顾自己,光秀心里很清楚,“洗澡啊?是啊,这时候洗个澡也许很爽快吧。”
“那您就洗吧,我带您过去。”利三赶紧走在前面。一听说主人要洗澡,隔壁房间的小厮马上去告知房东儿子。房东儿子手持火把在浴室入口处蹲着。“是乡下的浴桶,非常简陋,招待不周,还请恕罪。”光秀看了一眼房东儿子,默默走入浴室,小厮和利三候在外面。
里面响起一阵水声,利三在外面说:“将军……我给您搓背吧。”光秀说:“小厮在吗?让你这个老人动手我过意不去。”“没事,没事。”利三说着走了进去。他用小桶装了热水,绕到主人背后。虽然从未这样做过,但这里不是战场,正好又赶上今天主人神情异样,他也是想尽力改变主人的这种心情。
“你是名震一方的大将,怎么能让你搓澡呢?”光秀非常谦虚,即使对家臣也总是这么客气,这既是光秀的特长,也是他的缺点。利三等人认为他性格的这一面并不是好事。
“哪里的话,我这把老骨头,是在您的桔梗旗下才有了名声,有明智家才有我,而不是有我才有明智家。因此,有生之年在为您效力之时,给主公搓一次澡也算是珍贵的回忆呢……”利三撩起裤裙,把一只袖子用带子束起来,为他搓背。
在朦胧的水汽和灯光中,光秀尽情享受着老臣的服侍,低着头沉默不语。他将齐藤利三倾注给自己的关心与信长和自己之间的君臣关系相比较,深深地反省自己。“唉,我错了。”光秀在心中痛切责备自己,“有什么不高兴的呢?要怀恨在心、痛苦到什么时候呢?拥有信长这么好的主公,自己的忠义与情操还不如这位老臣呢。唉,太丢人了。”利三从背后泼来热水,他感觉就像泼向自己心头的凉水。
“果然洗了个澡好多了。看来我不仅是醉了,还累了。”“您心情好转了吗?”“齐藤利三,已经好啦。让你费心啦!我现在非常轻松舒畅。”“今天您的神色,可不是一般的不高兴,其实我一直挺担心的,这下真是太好了……那我要向您禀告,您不在的时候,有位稀客到访,一直在等您回来。”
“嗬,这个战场上的临时驻地,会有什么稀客?”“画师海北友松大人正好路过甲州,就算不去拜访别人,也一定要拜见一下您,向您问安。他中午就过来了。”“他现在在哪里?”“我让他在前面房间等候着呢。”“是吗?那我们去那边吧。”
“如果将军亲自前往,客人会感到惶恐吧。过会儿我带他过来。”“不不,客人是风流才子,无须拘礼。”正房的大厅里已经为光秀准备好豪华的晚餐,他却在齐藤利三房里和客人海北友松一起吃了一顿极为简朴的晚餐。和友松见面之后,他越发恢复了开朗的表情,询问南宋北宋的画风,论述东山殿的爱好,比较土佐的作画场所,话题从近世的狩野山乐等狩野派到荷兰画的影响,显示了他平日在这方面颇深的造诣。他又进一步说:“我也想老了以后安享清闲,像幼年时那样画些画儿。你什么时候有空帮我画一本画册吧。”
“遵命,画得不好,不过一定为您画。”这也是友松发自内心乐意接受的事情。他也希望光秀能够保住晚节,引导他接近闲雅,不想让他玷污了自己的名声。因为白天齐藤利三也曾在此谈论过这件事。
友松模仿中国的梁楷的画风,与狩野、土佐不同,最近开拓了独具一格的画境,终于得到了世人的认可。不知为什么,信长委托他给安土的隔扇作画时,他却称病没有答应。他是被信长灭亡的齐藤家的遗臣,用他的笔装饰信长的居室等于毁了自己的清白,这种心情也不难理解。
说到友松的人品,外柔内刚这个词非常贴切。他平时就提心吊胆地看着光秀身上聪明与理性的这两个极端。光秀这种冷静与睿智只要有一步走错的话,不知何时灾难的大河就会决堤,他将置身于浊流之中。因此他认为光秀今晚能主动提出来要画一本画册,这才可以保住他的晚节。他也明白了光秀已经在反省自身,于是想立刻为他作画。
光秀当晚睡得很香。因为洗了个澡,也多亏来了意料之外的佳客。拂晓时分,士兵天还没亮就起来了,给马喂草料,穿上铠甲,腰里裹上随身携带的军粮,等待主人出门。今天早上要到法养寺集合,离开诹访,前往甲府。然后经由东海道凯旋。
“将军,该准备起身了。”“哦,是齐藤利三啊。昨晚我睡得很好。”“那太好了。”
“出发之前给友松一些盘缠吧,就说是我的一点儿心意。”“可是我今天早上起来一看,友松大人已经不在了。看来他是和士兵一起起来的,天还没亮,戴着一顶斗笠,拿着一根拐杖,飘然而去了。”“真是逍遥啊……”光秀喃喃自语道,他望着早上的天空,又说,“真是令人羡慕的境界。”齐藤利三在他面前展开一轴画卷,说:“他留下了这个东西。我还以为是遗忘了呢,仔细一看,墨痕还未干……我想,昨夜您托他画册一事,他之后一定是不眠不休画到早上吧。”
“什么?不眠不休?”光秀将目光落在画卷上。曙光中的白纸上画着一大朵牡丹,角落里写着一行字:“无事是贵人。”
“无事是贵人。”光秀嘴里念着将它卷起来,眼前出现一大幅芜菁图,题字是:“客来一味药”。这一抹水墨画成的芜菁,看似丝毫未费苦心,但看得入迷以后,一阵土香扑鼻而来。芜菁的生命仅靠一根茎干上的叶子与饱满的根部维持,它的野性显得天真无邪、无忧无虑,似乎在嘲笑光秀的理性。光秀没有说话。再往后看,什么都没有画。空白部分占的更多。
“看来画完这两幅图天就亮了。”齐藤利三也喜欢画,因此也伸长脖子一起欣赏。看着看着,光秀觉得那芜菁仿佛是光着身子的婴儿伸开手在打哈欠一样。比起寻找美,他的心渐渐倾向于酌量哲理。光秀不敢长时间看了,“齐藤利三,卷起来吧。”
“我帮您收起来吧。”此时,远处的天空中传来号角声。总部法养寺开始催促镇上各支队伍做准备。在充满血腥的战场上听到的号角声带着悲怆的余韵,总有一种说不清的凄凉,而今天早上的号角声从容悠闲,让人觉得非常舒畅。“来吧,去集合吧!”光秀很快也骑上了战马。今天早上,他的眉间如同甲斐的群山一样,没有一丝阴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