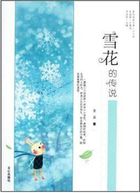显然是她剪的,她为什么要剪裁自己的文章?
他好奇而又有几分激动,拉了拉老板台的抽屉,都上着锁。又走向墙壁处的书柜,发现里边除了一些文学名著、企业管理类的书刊,还有很多发表过自己文章的书刊,打开看了看,文章也都被剪下去了。难道,她在搜集自己写的文章?他急急地翻动了一下书柜,终于发现一个厚厚的红色封面的剪贴簿,打开一看,扉页上赫然是自己的照片,边则是关于自己的介绍,包括自己的基本情况和发表有影响文章的情况。其实,记者虽然经常发表文章,可自已的情况却往往鲜为人知,更少见于报刊。这个扉页上粘贴的是他写过的一本纪实报导文集前面的作者介绍,想不到被粘贴在这里了。再往下翻,粘贴的全是自己在各个报刊上发表的文章。
这意味着什么?
女人哪……
张大明沉重地叹口气,停止了讲述。肖云却急急地追问起来:讲啊,后来呢……可真够浪漫的,想不到,这里居然有这样的女人,真叫人挺感动的!
志诚也有点感动,可没有说话。
在肖云的逼问下,张大明沉了沉又讲起来:后来就没什么了。一下午她也没露面,直到晚上才带着晚餐出现,是饺子。我吃完后才发现她脸色挺难看,问她出了什么事。她说她打听了,你——志诚,我是说你,她说你可能被抓回来了。我一听就急了,再也难以安稳,马上就要离开。她说,她也不知咋办才好,想了好久才决定,既不帮我,也不害我,让我自己想办法,逃出去逃不出去听天由命。不过,她还是拿来一件棉大衣和一支手电,然后就离开再没回来……我耐心等到晚上10点多钟,觉得人都睡了,安全一些了,就把被单扯成布条,连结起来,从后窗溜了下去。可是,尽管我加了小心,还是很快被两个缠红袖标的发现了。我拼命逃跑,他们在后面紧追不舍。后来,又来了几个人,还有开车追的,我只好往荒野中跑,眼看跑不脱,突然发现一个残破的井口,跑到跟前看了一眼,还是个斜井,就钻了进去,结果重蹈覆辙,你好不容易把我救出去,我又进来了……当时,我听到井口外面有脚步声和人的说话声,还有人往里找了一段……后来没有动静了,可我知道他们一定守在外面,不敢往外走。谁知等了一会儿,忽然一声爆炸响起,井口被炸塌了,我再也出不去了……对了,肖云,后来就遇到了你!
肖云说:这……哎,大明,你想过没有,你怎么那么容易被他们发现,是不是那个女人出卖了你,这边放你走,那边就告诉了她哥哥……不能,张大明急忙否定,绝对不能,她想出卖我何必费这么大事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她不是那种女人!
肖云急急地说怎么不能?我看你是头脑发昏了,她不是那种女人,是哪种女人……我不就是上了一个女人的当,被骗到井里来的吗?忽然想起什么,使劲打了志诚一下,对了,我才想起跟你算账,原来她是你……这么多年,你一直在瞒着我,原来,在乌岭还有你一个老同学,一个情人,你可真行啊!
志诚已经知道怎么回事,急忙抓住肖云的手:你别胡说,我们已经八年没见面了,这次是偶然碰上的……肖云挣扎着要把手抽出来可你们感情未断……对了,她跟我说了很多,包括和你从前的关系,你……你……肖云,你别闹了,其实,我也是她骗到井下来的,现在,她已经死了……什么肖云和张大明突然惊呼一声。
志诚低声讲了一遍经过。听完后,肖云不闹了,好一会儿才低声说这……想不到她是这样的人……怎么会发生这种事?用身体轻轻撞了他一下,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从来没有跟我提过她,为什么要瞒着我?
志诚沉沉地说:有什么必要,都是过去的事了……再说,提起这事我心里不舒服,我想彻底忘掉她,我也没想到还会见到她……我是什么样的人你知道,我现在对她只有怜悯,同情,也为她痛苦,可是,过去的一切已经成为过去……对了,肖云,你还没讲是怎么被她骗下来的!
肖云悻悻道:那还不好猜?这个女人,简直毒如蛇蝎,她完全摸透了我的心,用的是和骗你同样的手段……我说过了,他们把我关在地下室里,虽然没有自由,可饿不着渴不着。可是,昨天晚上却没按时送晚饭来,饭时过了很久,我都饿了,也没人送饭,同时,看守我的两个小子也离开了。我感觉好像发生了什么事,又着急,又害怕,又惦念,就在这时她突然来了,还带着饭菜。我本来挺戒备的,可听了她自我介绍就放松下来,她说是你在警校时的同学,包括和你当时的关系都说了……对了,她长得可真漂亮啊,说话也动听,我很快相信了她……她说,她当年对你感情很深,可因为年轻,加上家穷,被李子根骗了,现在虽然很有钱,可是并不幸福,还说非常羡慕我……接着,她对我说来找我了,包括你最初到乌岭和她的接触及第二次返回的情况,都跟我说了。我听了非常激动,就问你在哪里,她说,你刚刚被他们扔到一个废井里去,我一听就哭了,可她又说你还没死,她想去救你,一个人不敢……我一听,就求她把我放出去,和她一起救你,她还假意犹豫了一下才答应。这样,我们俩就从地下室出来,上了她的车。她早有准备,车上还预备了安全帽和矿灯……其实,我应该能看出是骗局,因为我出来得太顺利了。可听说你为了找我两次来乌岭,现在有生命危险,就完全昏了头,毫不犹豫地跟上她。到了井口跟前,我们下了车,她帮我戴上安全帽,还教我如何开关矿灯,我们就从井口慢慢往下走……当时,因为惦念你,我已经把害怕扔到脑后,什么也不顾了,就那么连滚带爬地往井里下。可走了不远,她突然站住了,说车还在外面,怕被人发现,让我一个人先走,她去把车开到一边隐藏起来。我没多想就答应了,边往下走边喊着你的名字,喊着喊着我还真听到里边有人答应,以为是你,非常激动,可就在这时,身后轰的一声爆炸,井口被封死了……和欺骗自己的手段如出一辙。
可是,此时志诚已经没有了仇恨,没有了愤怒。
后边的经过已经不用再问,井下那个声音就是张大明,他们两人就这样遇到了一起。而现在,他们三个又遇到一起。
命运把他们紧紧地联到一起。
沉默片刻,张大明叹口气说了句广可是,人跟人不一样,我了解二妹,她不会害我,她和齐丽萍不是一种人!
肖云轻笑一声:你怎么知道她不是那种人,你们已经好多年不来往了,人是在变的……志诚,我想齐丽萍当年也不是这样吧,要不,你也不能……是不是?
志诚没有回答,没有必要回答。
肖云却认为他默认了,自顾对张大明说:要我看哪,这乌岭没好人,他们的心都被煤染黑了,如果有好人的话,他们敢这么干吗?依我看,这个二妹肯定也是一路货色……肖云,张大明制止道,你别这么说,她肯定不会害我,她不是那种人。
你是不是对她有了感情?肖云轻笑一声,想不到,你也有这样的弱点。你们男人哪,都这样,都容易被漂亮女人欺骗……显然是双关语。她说着用臂肘撞了一下志诚,轻轻笑了一声。她也真是,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开玩笑。
可是,张大明的话却被勾起,他又叹息一声说:肖云,你别开玩笑了,我哪有这种心思,你知道我的情况……现在,我特别惦念她,如果我就这样死去,离开这个世界,她该怎么办……我真是死不瞑目啊!
他声音里透出一种深深的悲凉,肖云不出声了。志诚这才想起,张大明有个植物人妻子躺在医院里。
沉默片刻,肖云歉意地低声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你别往心里去。
他轻轻叹息一声:没什么……你就是不说这些,我也一直在惦念她。我本想带给她幸福,不想,却给她带来灾难,带来这种命运,一想到这些,我就特别痛苦……他的声音中透出一股刻骨铭心的滋味,志诚被打动了,忍不住问:这……你们……她……我还真不知道,你和她……沉默了好一会儿,张大明才叹口长气说:反正也没有事,就跟你们讲讲吧。其实,关于我们的事儿,肖云你也并不完全清楚。她……心神不宁。从昨天开始,这种感觉一直伴随着平峦县公安局刑侦副局长陈英奇,并越来越强烈,弄得他吃不好睡不香,早晨洗脸时,发现嘴上起了大火泡。
昨天晚上,他和儿子通了个电话,问他对程玉明说的话到底是真是假。儿子跟前有人,应付了几句没回答。后来专门回了电话,笨嘴笨舌地说当时看照片面熟,像六号井见过的爆破员,可所长和其他人都否认,他也不能肯定了。把陈英奇气得骂了好几句混球。
早餐喝了两口稀饭就再也吃不下去了,早早赶到办公室,刚坐下,儿子突然又打来电话:爸,矿里不让我在派出所干了,把我调到办公室当秘书,还给我加了二百块工资……什么?
儿子继续说:可是,我不愿意当秘书,我还是愿意在派出所,你不是说过吗,让我好好干,将来有机会转成正式警察。爸你跟他们说说,给我加工资我同意,可还是让我在派出所干吧……爸,我来之后,按你说的,每天写一篇小楷,我现在的字比以前写得好看多了,前天程大队来还夸我来着……别说了!陈英奇听得心中冒火,一边暗骂儿子傻,一边压着火低声说,让你去你就去吧,啥也不要说。今后要学会少张嘴,多动脑,听见没有?
听见了,那……让我上办公室去不去?
去,陈英奇说,让你去你就去,啥也别说,不过,这些日子眼睛要睁大,看到什么不对头的事就跟爸说,明白吗……对了,这两天你们矿里有没有什么不对头的事儿?包括你们派出所?
这……儿子说,爸……啥样的事儿算不对头哇?要我看,他们一直都不对头,所长表面上对我挺好,可啥事也不带我,就让我看家,一点意思都没有。前些日子,他带人出去抓逃犯,也不让我参加……等等,你说什么,你说他们前几天出去抓人来着?抓谁?
我也不知道,那天,乔猛喝多了,唠嗑时露出来的……爸,这事不对头吗?
陈英奇脑子一阵混乱,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又问了儿子几个问题,回答都不得要领,就不再往下问,只是再次嘱咐儿子多用脑袋,少说话。
放下电话,摸着下巴琢磨了一会儿,他拨了几个电话,有的打通了有的没打通。然后,又摸起内线电话找程玉明,没人接,打手机,原来去医院看那个昏迷者去了。问情况如何,程玉明说还没清醒过来。他让他马上回来,有事研究。等了好一会儿,程玉明才匆匆走进来。他不高兴地问怎么这么半天,程玉明说,在医院碰到汤义了,唠了几句才回来。陈英奇警觉起来汤义?他去医院了……跟你唠什么了?程玉明说没说啥,他说身体有些不舒服,去医院检查一下,然后又看了看那个昏迷的人,还说如果我们队人手紧,忙不过来,他们治安大队可以帮忙……哎,你不问我还没多想,他那人我知道,从来是无利不起早,今儿个怎么了?陈英奇脸色严峻:别说了,从现在起,你们必须保证二十四小时有人守在这个人身边,并且不许向任何人泄露他的情况。
知道了。你找我有什么事?程玉明看看他的脸色,哎,你脸色可不太好……昨晚没睡好?
你把昨天去乌岭的经过再说一遍。
不是跟你汇报了吗?
哪来这么多废话,让你再说一遍就再说一遍。
程玉明只好再说一遍。陈英奇听完,沉吟片刻说你们在调查走访时,蒋福荣一直跟在旁边?
是,程玉明点头说,不管咋说,他也是警察,还是派出所长,他要跟着,我也没法撵。所以,我觉得,那些矿工们的表现可能和他在场有关。停了停又问,你跟小陈联系了吧,他怎么说的?他能说啥,这孩子,脑瓜不灵,说的话我也信不着……不过,有个事儿挺奇怪,他刚才告诉我,矿里忽然调整了他的工作,把他调到了办公室当秘书,还给他涨了二百块工资!
这是好事啊……哎,这能不能和昨天的事有关?你没问问李子根,为什么这么做?
我想问问你,这意味着什么?
程玉明干脆地说肯定和昨天的事有关。这表面上是照顾,实际上是让他离开派出所,免得碍眼。
那么,这又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小陈昨天说的是真话,这个昏迷不醒的人真是乌岭煤矿的人,真的在六号井干过……对,这也说明,六号井那些矿工没说实话。我跟你汇报了,在我们到矿井之前,乔勇刚刚离开。我估计,他是提前做了安排,肯定是这样。
继续说,这还意味着什么?
这……程玉明忽然变得不那么干脆了,走到门口往外观看—下,又把门关严,才回过身低声说,这……昨天我也想过,你没深问,我也不好说,自己也有点不相信……能有这种事吗?如果这个人真是乌岭煤矿的矿工,真在六号井干过,真是那个爆破员,他们却竭力阻挠我们查清他的真实身份,这就说明,他们和这事有牵连,或者说……这……说下去。
或者说,这事就是他们干的,这个人是他们害的……陈局,这……我有点害怕,他们要干什么呀,他们还是警察吗?
陈英奇愤愤地说:如今,穿着警服败坏警察名声的事儿还稀罕吗?
程玉明咬着牙:对,他们根本就不是警察,只不过穿着警察的衣服……这么看,公安部取缔企业派出所的意义大着呢,咱们公安机关形象都让他们破坏了……可有什么办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无论什么事,只要有人一活动,啥政策都能变通,都走样了!陈英奇看一眼屋门,低下声音:现在,我再跟你说一件事,前几天,蒋福荣曾经带人出去抓过逃犯!
这……他一个企业派出所,抓什么逃犯?逃犯由我们大队统一掌握,他抓逃犯我怎么不知道……天哪,这要联系起来一想,肯定是这么回事了……陈局,怎么办?
我要问你!
问我?那好,查,下力气,不信查不清他。昨天我瞧出来了,那个姓赵的汉子和姓白的小哥儿俩,可能知道点真相,可他们就是不说。又换了为难的口气,他妈的,这事儿要是发生在别的地方都好办,可是乌岭……你也知道,乌岭的黑幕厚着呢,可谁也别想揭开。远的不说,前年有两个河北来打工的哥儿俩在他们那儿凭空就蒸发了,有传言说那哥儿俩不太听话,让他们给处理了,可咱们一点办法没有。跟你说实在的吧,那个李子根,还有乔勇,也包括蒋福荣,我看都不是好东西,他们手上都有鲜血,可就是动不得。也就因此,乌岭没人敢不听他们的,这也是我昨天撤回来的原因,留下也没用,肯定没人跟你说实话。
陈英奇半晌无语,手摸下巴好一会儿才说:我看这样吧,等一会儿,你给蒋福荣挂个电话,就说从那个昏迷不醒的人身上提取了子弹下准备送往省厅检验。
程玉明眼睛一闪乐了:你是说,给他来个诈唬……对,如果这事真和他们有牵连,恐怕有人就慌神了,狐狸尾巴也就露出来了。好,陈局,你这招儿高!
陈英奇却一点笑容也没露出来,依然摸着下巴想心事。程玉明问还有事吗?
陈英奇看了程玉明一眼,仍然不说话。程玉明半开玩笑地说:怎么,我猜猜,你在惦记着一件事,惦记着一个人?
陈英奇的表情松弛了一些。他最满意程玉明的就是这点,脑瓜好使,反应快,跟他在一起,无论说话办事还是破案,都特别省劲儿,有时,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表情,对方就知道了什么意思。
程玉明边想边说:是啊,如果前面的假设都是事实,那么,你惦念的这个人可能也出事了……我和他们单位联系一下,看他回去没有?
陈英奇说已经联系过了。我不但给他单位打了电话,还给他家挂了电话,手机也打了。
这……或许他还在路上,或者像他们说的,去别处找他爱人了。我想他们胆子再大,也不敢动他吧,他终究是警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