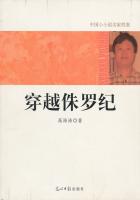从那一天起,林原跟胡云形影不离了,他开始跟着胡云练剑,笨拙地从最基本的一招一式做起,这个文弱的书生每天沉潜于剑术的晦暗之中。他的内心慢慢积蓄着力量,他竭力想成为一个内心强大的人。
对于胡云来说,林原的到来了结了他多年的心愿。他太孤独了。他没有朋友,也没有对手。如果说前一种情况让他觉得寂寞的话,那么,没有对手的状况,让他彻底地陷入了孤独。也因此,胡云一直有一种独立寒秋的感觉,仿佛头顶飞雁掠过,零星落下的,是苍凉的啼鸣。胡云一直想证明什么,但是,他拿什么来证明呢?又要证明什么呢?
胡云经常带着林原四处浪迹,荒草湮没的路径向他们敞开着,他们夜宿在山林里,在溪流边,有时则像一对乞丐一样流浪于街头。只要一有空闲,胡云教林原的,不是剑术,而是聆听。他叫林原仔细地分辨自然的每一种声音,站在桥头看夏季某一天的阴影在周围退缩和消失,听晨光中白喉雀和布谷鸟的歌唱,观察一只松鼠如何在很高的树梢上摘取枫树的翅果。胡云与林原经常徜徉在乡村的道路上,有无垠的干草田,八哥在搜索蟋蟀和蝙蝠,在检查干草搭成的洞穴。风吹落叶的声音,与吹拂蒹葭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在草丛中,蜥蜴在泥路上犹豫着伸伸缩缩的声音,与螳螂在草叶上跳跃的声音,往往夹杂在一起。阳光也是声音的推手,一棵松树,在正午的阳光下,松针会齐刷刷地站立起来,它们也是有着欢喜的尖叫的。傍晚时分静止下来的空气,弥漫着一种潮湿土壤的香味。在它们周围,野百灵鸟吹哨一般的声音,知更鸟和暮雀在白天里唱的最后一首歌曲,在静寂中传得很远。
林原从自然中学到了很多很多东西,也一天天地消除着我执的影子,一天天地让自己融入周围的自然。他能辨别出剑尖刺向不同部位发出的不同声音,确切地说,那不是剑的声音,而是风的呼啸声,有时像金丝一样坚韧,有时像丝绸一样细滑。不仅如此,他还发现了诸多击剑姿势的本质,发现了剑花闪烁那一瞬间的美丽和芬芳,还有剑锋封喉时的果敢与畅快,以及致命处渗出的红的花瓣。总而言之,这时候林原已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剑客了。他沉醉于一种创造,执著于一种创造,同时也明白,毁灭也是一种创造。当然,直到这个时候,林原还不知道自己练剑的目的何在,他慢慢变得渴望对手了,也渴望成为英雄。也希望有一次寻找对手的旅行。他的眼神开始变得坚韧了,也充满着欲望。他有时候焚香端坐,吟诗作赋;有时候身如侠客,疾步行走。他开始注意人们的姿势和行动,观察人们的动作和神情,判断人们是否具有某种攻击性。他甚至渴望被人杀死,用自己的颅骨为令人尊敬的对手做出精美的酒器。
总而言之,林原终于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剑客了,他的剑术炉火纯青;他的内心,也完全变成了一个剑客的内心,安之若素,无欲而刚。在剑术中,林原得到了自己的乐趣,也找到了自己在风雨飘摇中的影子。虽然他从不知道自己练就剑术是为了何用,但他显然是从剑术之美中忘却了功利。自己的击剑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功名?功名永远离剑术很远。报仇?自己根本无仇可报。在很多时候,他像一个贪玩的孩子一样,沉湎于自己与剑之间的游戏,就像沉湎于两个人之间的私密和情爱一样。
当林原沉湎于自己的剑术之时,年老的胡云总是神态庄重地站在一边。他很少看林原的所作所为,林原所做的,无非就是当年自己所做的罢了。他也懒得再去回味和品尝了。胡云这时候所做的事,就是注视遥远的天际,让自己灰白的长须在晚风中飘摇。他内心一直有一个想法。他确信在未来的某一时间里,一定能跟自己的愿望相遇。相遇的结果,是那个人的鲜血从喉尖中,如细雨一样飘扬。
虽然已经数十年了,但江湖上关于胡云的传说没有渐渐飘散,反而,如一团云一样,变得越来越浓烈。胡云的名声传遍乡村、城堡、巷道和寺庙,当整个江湖传闻胡云竟数年剑未出鞘时,许多人感到受到了奚落以至于异常愤怒。不知什么时候,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如蛇信子一样伸伸缩缩:只要有人胜了胡云的剑法,他就是江湖公认的领袖。在如此诱人的传闻下,剑客们趋之若鹜。他们总是在白天或者晚上的某一个时间突然出现在胡云的面前,逼着胡云动手。而胡云对此却表现得异常冷漠和孤傲,甚至连正眼也不看一下这些大侠小侠们。他不愿意跟这些人动手,即使他们杀掉自己也不愿意。在胡云的内心深处,他觉得这是一种对完美的亵渎。
林原的出现正好阻止了他的悲哀,也正好使他内心一种濒临深渊的情结暂时得到稳定。胡云变得无所作为了,他只是等待、思考和戒定,对于他来说,世俗就像一颗颗沉向水底的石子,他无须行动,也无须激动,他只是被牵引并且任凭自己沉落。他只为自己的目标所牵引,他不允许任何扰乱自己目标的东西进入他的灵魂。
五
没有人知道胡云去黄山祥符寺的目的。那座寺院,深藏在像七十二朵莲花一样开放的山峦之中,显得那样幽深静谧、空灵遥远,就像埋藏着一个遥远的梦一样。这个寺院,为什么对于胡云有如此的吸引力呢?没有人知道,只有胡云心中明白,有一个人在那个地方一直等着他。而每次当林原问起此行的目的时,胡云总是缄默不语。胡云沉默的时间太多了,确切地说,他是太爱沉默了,沉默就像反刍,会让记忆的沉渣泛起,而他喜欢这样的感觉。他愿意将自己的精力与智慧都集中于他的思想,不外露,也不泄气。他宁肯拙于言语,也因为他不相信语言。他自己也清楚地明白这一点,除非迫不得已,对于胡云来说,他已不喜欢说话了。
黄山汤院是佛教净土宗(莲花宗)还是禅宗的寺院,这些,对于胡云来说,已变得不重要了。门派都是路径,它们的背后都是同一个归宿。对于胡云来说,这已经变成简单的道理了。当年志满大师在黄山溘然长逝,留下硕大的舍利子在汤院,这在江湖上已秘密流传。有无数江湖高手对这七彩舍利子觊觎已久,垂涎欲滴。不过碍于汤院无极禅师的威名,谁也不敢轻举妄动。林原暗自以为,胡云此去祥符寺,似乎是对志满大师的舍利子有想法。当林原试探着询问胡云时,胡云只是莞尔一笑,不作回答。林原对于这一件事的怀疑立即云消雾散了。在他看来,胡云应该没有这样的想法,一个人,到了师傅这样的境界,心思显然不挂于物了。在林原看来,胡云之所以到黄山祥符寺,目的很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他想会会祥符寺的无极禅师,也就是当年人称天下第一剑客的骆一奇。
骆一奇二十年前曾是笑傲江湖的绝顶高人,他的一柄风月剑出神入化,传说当他的剑直指天上飞翔的鸟雀时,鸟雀也会哑然落下。他剑尖上嗞嗞冒出的寒气可以摄取几十米内一等高手的魂魄,或者扰乱你的心智,让人心猿意马。所以当他在华山顶上连败十二位高手夺取天下第一的桂冠时,任何人都不觉奇怪。然而奇怪的是,骆一奇突然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杀妻携子神秘地失踪。这就令江湖人大为不解了。
江湖有一种传说是骆一奇练风月剑乱了心智,连正常的生死界线也不明确了。在这种情境上,有些匪夷所思的行动,在江湖练武之人看来,似乎再正常不过了。一种技艺,如果登峰造极,也难免会走火入魔。毕竟,魔与神,相隔只有一张纸。人们可惜骆一奇的走火入魔,也可惜他在鼎盛时期隐退江湖。有关骆一奇退出江湖之事就这样被人们慢慢地淡忘了。
有关胡云与骆一奇以及骆一奇的妻子阚氏的故事,其实跟这个声色世界所发生的所有爱情故事一样,并没有什么样的不同。只不过一个人坠入其中,就以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那时候的胡云与阚氏也是如此。胡云与阚氏的故事,显然发生于那一场华山比武之后,当那一场比武因为胡云的搅局变得不欢而散之时,只有名门之媛的阚氏注意到了胡云,注意到了这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的不同凡响,也注意到了他的神秘之处以及巨大的蛊惑力量。而这时候,骆一奇一心练武,冷落了阚氏。清秀的书生剑客胡云,唤醒了阚氏生命的激情。于是故事便有了开头,也有了出人意料的结尾。
在此之后,阚氏安排了骆一奇与胡云的见面。骆一奇很快也为胡云无师自通的剑术感到震惊,在当时已是天下第一剑客的骆一奇看来,胡云的剑术所代表的,并不是一种派别,也不是一种技艺的成熟,而是一种幽秘理念的体验。这种幽秘的理念,似乎就潜伏在这个世界的某一处,时隐时现,让人无法捉摸,它总是通过一些东西别出心裁地表现出来。在他看来,在胡云的身上,似乎正暗藏着这样的神秘之花,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似乎无不在规矩和道德之中。于是,两个高手言谈甚欢,他们一起商讨剑道,磋切剑术。他们缓缓地把剑从剑匣中抽出,就像展开一幅画轴一样小心翼翼。在剑抽出那一刹那,他们原本阴晦的表情也会随着剑的寒光而变得灿烂起来,只要剑一到他们手中,他们的气质便会立即变得超凡脱俗起来。接着便是一股旋风掠过,空中开始旋转无数白亮的剑涡。草木在他们身边颤抖,发出瑟瑟的声响。他们的剑刃锋利无比,飞扬的树叶被一一削成缤纷散乱的细屑……他们的每一次比武,就像是飞花摘叶,一次完美的双人舞。
在这样的情境之下,阚氏也分不清自己到底是爱着哪一个了。骆一奇与胡云,就像雌雄宝剑一样,她都不愿舍弃,都视为自己的钟爱了。
一女共侍二夫的情景,在当时的社会看来,无疑已是惊世骇俗。但对于胡云和骆一奇这样的高人来说,在起初的那一段岁月中,双方似乎都没有把这样的事情放在心上。他们的心思全不在世俗和人情之上,他们的心思全在如何破解对方的剑术密码之上。这时候的女人,包括绝色佳人阚氏,双方似乎并没有完全地放在心上,他们的身体在这个世界上行走,而他们的灵魂却一直高蹈地在云端上起舞,没人注意伦理,也没人意识到道德。他们只关注一点,那就是如何成为一个胜利者,如何以自己之剑,击除对方胸前的大门。
那真是一段奇怪的时光,也像是云上的日子。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一直到阚氏在春天来到百花烂漫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才戛然而止。胡云、骆一奇以及阚氏都不约而同地从云端跌入尘世:这一个将要出生的孩子,究竟是谁的?这个问题像一个晴空霹雳一样,将他们全部炸醒,一种突然降临的道德感重新左右了他们。于是,骆一奇和胡云停止了切磋,骆一奇带着阚氏绝尘而去。胡云像中了魔似的,苦苦相追。就这样,从中原一直追到塞外,然后又追至江南。疯狂的骆一奇在阚氏生下孩子后,悲喜交集之际,竟突然精神错乱,将阚氏杀死,抱着孩子突然消失。
阚氏的死对于胡云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在很长时间里,胡云内心里一直深埋着复仇的愿望。但慢慢地,随着骆一奇的杳无音信,也随着胡云关于人生意义的认识改变,这一件事慢慢脱离了仇恨的本身,只单纯变成了个诺言,变成一件必须履行的任务。胡云的复仇欲望深埋于时间的积累里,充塞着他的每一个毛孔。它比饥饿更令人难以忍耐。在这种情况下,胡云想象他与骆一奇的见面,更像是饥饿的人想象一场盛宴。他经常想象着自己用冰冷的剑锋与骆一奇温软的血肉撞击时的那种无声的快感,不完全是复仇,而是自己完完全全地战胜了骆一奇。胡云知道真正饥饿的不是他的肚肠,而是他的剑。即使时间使自己慢慢地麻木,但他的剑却没有因此而失去灵性和欲望。它仍执著地去寻找那堆逐渐变得腐朽的肉体。
外人,包括林原在内,都以为胡云此行去汤院,是一个绝代高手向另一个绝代高手的挑战。他们之间的论剑即将名垂千古。没有人知道胡云与骆一奇相聚的另一层隐意。那是一个秘密,一个曾经的情爱故事,也是一个复仇的故事。
在这种情况下,胡云全部的人生,就只是找到无极禅师,逼他出剑,一争高低。仇恨是谈不上了,挂碍于他心壁的,仍是谁是天下第一高手的悬念,他一直想着,在有生之年,诠释这一疑问。这是胡云去汤院的唯一目的,也是他深省自己时日不多后的最后抉择。
六
然而林原不懂得这一切。
林原永远像一个未成熟的大孩子一样,对世上的一切都感到新鲜,都有浓厚的兴趣。他感兴趣日月星辰的升起和落下,感兴趣花的原野鸟的啁啾,甚至凝神顾盼路边美丽动人的女子。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新鲜的,凝神练剑竟然召回了他心中已经遁去的童心,这不由使缄默的胡云感到诧异了。每到一处,师徒憩歇下来之后就是林原忙碌着一切。这个俊美的男子悉心地为师傅安排住宿,采购食物。胡云熟睡时,林原便会细心地替他掖好被角。虽然林原越来越变得童真,但由于他像对待父亲一样尊敬胡云,所以,他的冥顽并不妨碍他对胡云的伺候。
起先,林原还对他一路之上杀了那么多江湖高手而忌惮,但后来,他似乎对比武一事抱有极大的兴趣,对他剑下的生命惘然无顾了。
“真有意思,他怎么就那样轻易地倒下了呢?我的剑锋在他的咽喉上只是划了一个小口,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重新比划着姿势,讷讷自语,就像杀了一只鸡一样。生命与死亡在林原眼中,已不具有某种质的区分了。胡云充耳不闻。
这一天,他们到了离黄山还有三十里地的一个小镇——仙源,这个小镇古朴优雅,安宁静谧。也许是路途疲乏,找到客栈之后,胡云立即脱衣而眠,不一会儿就响起了轻微的鼾声。在林原看来,师傅真的有点老了,很多时候,精力明显不济了。
林原无所事事,便走出了客栈。
街景并没有什么可观赏的,南方小镇,冷清宁静。林原看了一圈后,见不远处有一片红红火火的枫树林,映着晚霞分外艳丽,心头一热,便走了过去。
走进林间,定步远眺。这时就听到缥缥缈缈地传来一阵歌声。
萋萋青草
端端林木
灿灿之彩霞
衰衰的人
歌声婉转动听,从背影看过去,那女子一身缟白,一袭黑发,在灿若流火的夕阳与枫叶之中,显得分外动人。林原不由看得呆了。
女子似乎一边吟唱一边做些什么,对不远处的林原丝毫没有理会。林原便轻轻地走到她的身边。他这才注意到,这女子是个丹青好手,她正凝眸于画架上的一幅画,润笔涂抹,画上层林尽染,萧瑟秋风中夕阳如血。
女子发现了,抬起头来四目相对,女子轻轻地“呀”了一声。
林原简直呆了,这女子美若天上的仙女,起码在林原所见到的女子中,她是最出色的一位,气质高雅,超凡脱俗。并且林原也知道,他以后再也见不到比她更出色的。
女子也审视这个眉清目秀,有着儒雅气质的年轻人。
“你是本地人吗?”林原问。
女子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