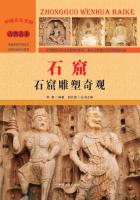2013年伊始,中国电影主管部门公布了2012年中国电影产业的“佳绩”:总票房170.73亿元,电影产量893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电影生产国(位列印度、美国之后),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电影消费市场(北美是108亿美元,中国是27亿美元)。虽然2012年国产电影票房略微低于进口票房,只占据全国总票房的48.46%,但是相比好莱坞电影对其他民族电影市场的绝对优势(如2012年澳大利亚本土影片的份额是4.3%,俄罗斯是15.2%,西班牙是17.9%),这种本土电影市场能够在近十年时间里稳定占据半壁江山的现象并不多见(除了日本、韩国等本土市场偶有超过50%的份额之外)。也就是说,中国民族电影工业如同中国经济一样正在走向复兴与崛起。考虑到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从2001年开始,这种把电影作为“文化产业”的历史并不长,中国电影完成这种“华丽转身”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多次转型有关。
电影作为一种高度现代分工协作,需要大资本投入(不管国营还是民营)的艺术商品,其生产和消费方式受制于社会的基本制度环境。再加上电影作为一种现代大众媒介,自诞生伊始就成为文化、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其叙事形态又与主流意识形态有着密切关系。正如好莱坞既是美国文化产业出口的重中之重,又是美国精神及价值观的最佳中介。在这个意义上,探讨这三十年中国电影的发展之路,离不开对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认识。可以说,中国电影观念及功能的每一次重大调整都是在中国社会巨变的背景中产生的。改革开放之初,政治、经济等不同的社会领域处在分化调整之中,彼时的中国电影形成了主旋律、娱乐片/商业片、探索片/艺术片三足鼎立的格局,政治、资本与艺术成为支撑这种局面的三重力量;九十年代之初政府推进激进市场化改革,电影领域的大事件就是1994年好莱坞重新进入中国,商业大片的盈利模式涤荡着处于瓦解之中的计划性电影生产与发行体制;新世纪以来中国加入WTO,为了应对好莱坞的巨大挑战,主管部门启动了更加市场化的电影产业转型,中国电影重新回到建国前以市场为规则的运作模式。
在这里,笔者把“体制”视为理解中国电影与社会转型的关键词。在中国的语境中,“体制”经常被认为是看得见的社会主义制度(如计划经济、行政干预和单位制),而把看不见的市场之手看成是一种“非体制”、“反体制”的力量,这本身是一种刻舟求剑式的误读,其悖论在市场化、“非体制”化的推手恰好来自高度集权化的国家。在笔者看来,“体制”有双重含义。一方面,“体制”是指一种特定的社会生产、运行的制度安排,在这个意义上,“体制”并非特指计划经济下的社会主义“体制”,市场化的、资本主义的制度规则也是一种“体制”,在后冷战的意义上(以美国胜利、苏联解体为标识),前者被认为是保守、僵化、效率低下的“旧体制”,后者则是充满竞争精神、高效率、灵活的“新体制”。另一方面,“体制”不只是一系列具象化的制度,还是维系体制运转的文化软实力。正如电影体制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电影制片厂、发行网络等电影生产与消费的方式;二是电影叙事承载着重塑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体制的这两个方面一硬一软,要不美美与共,要不唇亡齿寒。体制并非一成不变、固定不动,这三十年体制经常因势、因时而动,这成为当下中国电影及社会的基本形态。
一体制的晚钟
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电影一方面全面恢复生产(在“文革”初期被中断,1970年到1972年拍摄了10部样板戏电影,1973年恢复拍摄故事片,到1976年9月共拍摄76部故事片),另一方面几百部在“文革”中被禁、被批判的电影解禁,包括“十七年”电影(“十七年”故事片总产量603部)和新中国成立前的左翼进步电影,与此同时,不定期举办外国电影放映周(日本、美国、欧洲电影开始进入中国)。这个时期也创造了中国电影观影人次的最高纪录,1979年中国观影人次达293亿,如此之高的观影人次与五十至七十年代社会主义电影体制有关。
建国之初,首先,1946年在东北接收日伪电影企业“满映”成立了东北电影制片厂(后改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1949年北京、上海解放后先后没收国民党党营电影企业成立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同年中央电影局成立,专门管理电影剧本的审查与发行。五十年代后期又陆续组建了八一、珠江、西安等八大电影制片厂。这成为新中国电影工业的基础。其次,1951年全国,主要是上海地区还有七家私营电影厂,1953年完成公私合营,电影领域的合并与其说是国家强制赎买,不如说是民营公司在1949年后陷入经营困境、渴望与国营厂合并,自此,电影厂全部为国营事业单位,直到九十年代末期民营资本、外资才以间接方式进入电影业。再次,全国从上到下建立了与各级行政部门平行的电影发行公司,覆盖全国每一个角落,即使偏远地区也有基层电影放映队的身影。这种电影管理方式采用计划经济式的统购统销的方式,国家是投资人,生产者也是购买者,新中国电影从根本上改变了电影只局限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消费的状态,使得电影从都市市民或小资产阶级的艺术变成全民可以共享的艺术形式。不仅如此,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电影是仅次于或与文学比肩的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第一次全国范围的文化批判运动就是由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引发的,这场批判成为树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次运动。电影之所以具有如此高的地位(“文革”中成为重灾区也正因为其重要),与列宁把电影作为党/国家的主要宣传工具有关(列宁认为电影是“一切艺术部门中最最重要的”),也与电影成为二十世纪最具大众性和群众性的传媒方式有关,直到八九十年代电视才开始挑战电影在中国的影响力。即便在当下电视、互联网虽然比电影具有更为广泛的受众群,但是对于电影的审查依然比其他的媒体要严格得多,这种管理的惯性来自电影作为二十世纪文化政治风向标的象征意义。
新时期是通过思想解放运动以及“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文学运动拉开序幕的。如同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电影领域则是从“文革”中复出的“第三代”(以谢晋为代表)、“第四代”(以拍摄《巴山夜雨》的吴贻弓、《小花》的黄健中、《苦恼人的笑》的杨延晋为代表)。与此同时,电影理论界开始“丢掉戏剧的拐杖”(白景晟,1979)、“戏剧和电影离婚”(钟惦棐,1980)、“让电影从舞台框里解放出来”(陆建华,1980)、“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张骏祥,1980)、“‘电影的文学价值’质疑”(张卫,1982)等一系列回归电影本体的讨论,就如同八十年代文学界出现“文学主体论”、“回到语言自身”,经济学界出现“企业本位论”、“回归企业本体”的讨论一样。从这种文学、电影与经济领域之间的“共振”效应可以看出;一方面,八十年代“改革共识”被各个领域、学科共同分享;另一方面,这种“共享性”的前提在于社会尚未分化,社会主义体制尚未瓦解,各个领域“心照不宣”地用同样的模式回应共同的主题。如果说以“谢晋模式”(用家庭苦情戏的方式回应“文革”及五十至七十年代的苦难)、“第四代”的人道主义论述依然与八十年代中前期的主流意识形态(“拨乱反正”、推动社会改革)相吻合,那么更为年轻的“第五代”导演的作品(以张军钊导演《一个和八个》、陈凯歌导演《黄土地》为代表)则走得更远。就像朦胧诗通过语言的不透明性来挑战社会主义现实文学语言,“第五代”的贡献在于用一套新的电影语言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电影叙事划清了界限,“第五代”也成为八十年代先锋电影、探索片、艺术片的主体。这种体制内的“先锋”叙事尽管与电影审查机制偶有抵牾(如《一个和八个》的结尾八路军打死被日军俘虏的女护士),但总体上受到电影及文化界的鼓励,正如八十年代的改革都是依靠体制内的改革派并受到体制的支持和默许一样。
“第五代”的“横空出世”还有赖于八十年代特有的文化制度的保证。第一,这种以导演的代际命名的方式是八十年代的“发明”,也与当时对青年、对代际更迭的崇拜相关(正如五十至七十年代出现了一套关于老年/保守与年轻/革命的文化想象)。正因为“第五代”的被命名,“第四代”、“第三代”在一种“逆向推理”中被建构出来。不过,从“第三代”大多是“十七年”导演,“第四代”是“文革”前期完成学业,以及“第五代”是电影学院78级学生来看,这种代际划分确实属于不同的历史时代,而与九十年代用“80后”、“90后”、“00后”等自然年龄来划分艺术现象不同。第二,代际命名是一种针对电影导演的命名方式,这种把电影导演视为电影制作核心的制度(相比明星中心制、制片人中心制)是五十至七十年代电影生产的基本原则。导演并非“天然”是电影生产的组织者和命名者,这种导演中心制与其说来自五六十年代法国新浪潮确立的“作者电影”制度(作者电影催生一大批欧洲电影大师,其拍摄的艺术电影与苏联电影、好莱坞商业电影成为冷战时代的三大电影格局),不如说来自苏联电影传统中的导演中心制。第三,“第五代”刚刚毕业就获得独立拍片的机会,相比从学徒到导演漫长的现代企业内部的等级制,“第五代”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除了以“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的身份格外受到青睐之外,张军钊、张艺谋等“第五代”电影人恰好是从广西、西安等相对偏远的电影制片厂起步的,再加上当时的厂长,如吴天明的“开明”和扶持,使得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有了登上历史舞台的机会(八十年代末期“第六代”也想如法炮制却已经没有这样的历史机遇)。这些电影导演与作家、艺术家一起成为在八十年代发挥重要社会功能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之所以在八十年代成为格外耀眼的文化英雄,是因为当时社会经济改革依然需要文学、“文化革命”来提供合法性,这延续了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化革命”作为社会、政治革命主导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仅从艺术家/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看,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断裂远大于八十年代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历史延续性。
1984年中国改革的步伐从农村改革(用家庭联产承包制取代人民公社)转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扩大国营企业经营自主权等)。与此同时,电影理论界出现“为娱乐片正名”的争论。在强调电影的娱乐价值之时,依然延续了七八十年代之交把五十至七十年代电影指认为政治、说教电影的理念,这种论述方式却看不到五十至七十年代电影固然是政治意识形态斗争的组成部分,且以电影制片厂为基础的国营企业也是创造利润的大户,正是八十年代的市场化话语屏蔽掉了社会主义也有商业以及商品交换,只是两者调配资源的方式不同的事实。八十年代中前期在“第四代”、“第五代”电影吸引文化理论界目光之时,已经出现了以《神秘的大佛》(1980)、《少林寺》(1982)等武侠片和以《黑三角》(1977)、《猎字99号》(1978)、《保密局的枪声》(1979)等反特片为代表的商业片。如果说武侠片作为被左翼电影所批判的娱乐片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历史中销声匿迹,在八十年代又通过与香港电影人合拍的方式“回流”,那么这些带有惊险、侦探等娱乐元素的反特片却携带着五十至七十年代革命电影的印痕。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社会与政治的转型并不能简单地阻断文化的延续性。直到新世纪以来由反特片演化成的“间谍”片成为热播影视剧的重头戏(颇具负面意味的“特务”变成了“007”式的“间谍”)。1987年中国电影迎来了第一次娱乐片高潮,曾经借重原有社会主义制片厂制度庇护的探索片遭遇票房滑铁卢,就连已经获得国际声誉的“第五代”导演也纷纷转型拍摄商业片,如田壮壮的《摇滚青年》(1988)、张艺谋的《代号美洲豹》(1988)等,更具标识意味的是1988年出现了王朔电影年,有四部王朔的小说被改编为电影(即《顽主》、《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轮回》、《大喘气》)。
就在娱乐片刚刚获得合法性时,1987年出现“弘扬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说法,国家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投资拍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政府及其文化/宣传部门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命名为“主旋律”,承担着讲述执政党的合法性以及改革开放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可以说,主旋律是在主流意识形态或执政合法性遭遇危机的状态下出现的,也是电影在八十年代去政治、去革命的背景下出现的再政治化,只是此“政治”已经与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化政治斗争的“政治”发生巨大的转移,是一种掏空了阶级斗争、工农兵政治的去经典社会主义政治的政治。如果考虑到1988年张艺谋的《红高粱》获得第38届西柏林电影节最高奖金熊奖(二十五年之后《红高粱》的原小说作者莫言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被作为八十年代文化“走向世界”、被世界认可的标准。值得指出的是,彼时的“世界”依然被笼统地想象为“欧美”世界,而九十年代以来,就像冷战终结之后的世界局势一样,西方/欧美世界被简化为冷战的胜利者美国,正如新世纪以来好莱坞是中国电影的唯一参照,借用《北京人在纽约》的歌词“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你不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
至此,八十年代出现了三种电影形态或格局:一是体制内的艺术片(或者说严肃创作),二是追求娱乐和商业价值的娱乐片,三是国家投资的主旋律。这三种电影在八十年代的文化生态中可以说势均力敌,甚至容易引起争议的艺术电影更受到重视。在这个意义上,八十年代凭借着不计成本的社会主义电影体制,造就了艺术片最后的辉煌。在回望的视角中,可以看到八十年代电影的主题异常丰富,不仅有农村题材,在八十年代前期《咱们的牛百岁》、《喜盈门》等农村电影获得了市场和政府的双重褒奖。这种按照工、农等行业划分为不同的题材的方法,本身是一种计划经济下的文化生产方式,或者说用艺术片、娱乐片、主旋律的分类来取代工业电影、农业电影、少数民族电影是七八十年代社会/文化转型的结果。此时的电影放映体系并没有瓦解,覆盖全国各个地区,恰如中国社会城乡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差距不大,电影依然被当成一种最具大众性和群众性的艺术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