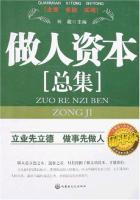红颜虽然易老,总有少女时的容光和羞涩,比如西子捧心,李清照倚门嗅梅含羞一笑,比如《罗马假日》里的奥黛丽?赫本,还有不可思议之魅惑的苏菲?玛索。再如青楼中才貌双绝的苏小小,卒时不过十九,她却没有感到悲哀,觉得此生得到那份风流己经足够。也许这样,那些爱她或她爱的人记住的才是她永远水灵媚惑的容颜。
中国传统的诗人是游吟江湖的胡琴,是寄情山水的古筝,是欲说还休的琵琶,心总是寂静的,是冷的。只有禅宗,开始说大俗大雅的语言,如孩童般率性而为,深得自在的好处。
景岑招贤禅师是南泉普愿禅师的弟子,他素以美而有哲理的语言而出名。“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典故也是出自他之口,用来指修行的持续性。招贤禅师一天游山去,见到住持,住持问:“你从哪儿来?”招贤禅师说:“游山来。”住持说:“到什么地方来呢?”招贤禅师说:“始随芳草去,又逐落花来。”住持说:“好像很有春天的意象呀。”招贤禅师说:“也胜秋露滴芙蕖。”
这则禅宗间的对话,正是“银碗里盛雪”的风格,“秋露滴芙蕖”,好艳的字眼,却无一丝俗意。这种风格,在日本的连歌和俳句里可以见到。国学大家李叔同去日本学过音乐、油画和戏剧。 王国维在日本治学。可见这个民族在传统文化方面还是有不少值得学习的地方。现在日本还有年轻人热衷于和歌的创作,相对曾经被他们膜拜的盛唐而言,我们面临着诗歌没落的状况,有乞讨的“诗人”,有娱乐化的“梨花体”,直至讨论诗歌有没有存在的必要,真是一种莫大的悲哀。
王国维论美,一为壮美,一为优美。禅宗的“妙语”无疑属于后者,在西方的音乐里属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的风格,是古筝的急奏和小提琴的慢音,是高山流水碧海蓝天,是深情缠绵悠然神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道家的隐士作派,从南山到桃花源,“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说的就是优美的意境。楚辞之艳,清高内悲。宫廷诗之艳,难脱做作之嫌。诗经之风,至简至纯,于此遥相呼应。
这种感情的放纵,在西方文化里比较普遍,而中国文化悲天悯人的精神内核,也自道家而至禅宗,始有片刻的忘机和自得。泰戈尔融中西文化之长,徐志摩创新月派,也是对唯美精神的延续。关于“永和九年”的美,是王羲之唯美精神在书法和东晋大写意里的最高峰。
那种冲淡隽永的美,正如历史里仕女弹琵琶吟唱的剪影,如此我见犹怜。
阳关三叠
静
流动
杜康酒
美人如玉
胡笳十八拍
杏花烟雨江南
采菊南山下
伐木丁丁
秋蟹肥
邀月
明
春日
一江水
马蹄踏香
燕过了无痕
追忆似水流年
平明寻白羽
泼墨山水
大写意
纸伞
影
羞涩
青铜爵
蓦然回首
楚王好细腰
醉里挑灯看剑
一夜鱼龙舞
欲说还休
柳梢头
黄昏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