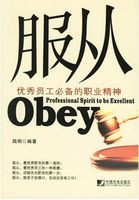民领我们爬树掏鸦雀窝的那年,我十岁,他十四。
十四岁的民在我们孩子当中自然成了“群龙之首”。
在村东的禾场上有一棵参天刺柏。在刺柏的杈桠上有个鸦雀窝。
这天,民在刺柏树下,很是“领袖”地对我们说:“现在我要爬上刺柏掏鸦雀窝,你们在树下一定用布衫兜好,甭让鸦雀蛋打碎了!”
我们抬眼瞅刺柏上的鸦雀窝。鸦雀窝蓬蓬大大,在权桠上随着微风的吹拂,摇摇欲坠。
民是第一个敢上刺柏掏鸦雀窝的人。我们都为他感到欢欣鼓舞。
民便束好裤腰,系好鞋带,朝手心里“呸!呸!”啐两口唾沫,然后轻舒双臂,捷如猿猴,“噌噌”几下爬上刺柏丈许。民被我们用充满钦佩的目光一直送到树梢。
民在树梢上晃晃悠悠,宛若寒风中的小鸟。民的每一举手投足都极为小心翼翼。有几次,眼看着民的指尖够住了鸦雀窝,但又总是差那么一点点。我们都为民捏了一把冷汗。
后来民的手终于伸迸了鸦雀窝。民从鸦雀窝里抓出一团棉絮似的羽毛。民便把这羽毛缤纷扔下。
树下的我们,早就抻开衣襟,作好一切准备工作。
但我们做梦也没想到,随着羽毛纺纷而下的还有一条蛇!
那是一条花花绿绿的蛇。在我们幼小的年龄里,根本没有更多知识判断它是一条怎样的蛇。我们只知道很多人被蛇咬过后的痛苦,因此每每谈“蛇”色变。
那天,当肉坨一样滑冷的蛇“扑嗒”一声摔在我们脚下时,很多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只有眼尖的一个孩子大嚷一声“蛇!”我们才如马蜂窝里被人捣了一棍,“訇”的一声四处炸开,叫的叫,逃的逃,根本忽略了还在树上的民。
民乍初还没弄清这是怎么回事,正顺着树干往下爬,下到半截,忽然看见有一条蛇,昂着头,张着粉红的口,吐着黑色的信,正如扭曲的软剑一祥,向上直刺而来。
民惊叫一声:“打蛇!”
可我们愣怔在那里痴傻了一般,没有一个人去打正在爬树的蛇。
危急中,民纵身一跃,跳下树干。
跳下树干的民,再也没有站起来。
民的脚踝粉碎性骨折。
过后,我们才知道那是一条不咬人的蛇,我们这里俗称“汗蛇”。据说,每当夏夜我们熟睡的当儿,它还专门爬到床头上舔我们脖颈上的汗呢!
再后来,民的脚踝一直没有医治好,成为永久性的陈旧性骨折。
每当见到一瘸一拐的民,我们都很痛悔。痛悔之余,我又深切希望民能原谅我们,假如那时民抓的是一只老鼠而不是一条蛇,我们就会勇敢地冲上去把它扑打下来,民的今日就不会是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