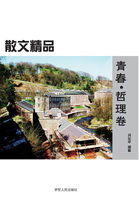我与日本学者似乎有不解之缘,虽然我不懂日语,1979年以前又从未到过日本。
1974年,我被借调到北京《历史研究》编辑部工作。“文革”虽然还没有结束,报刊控制仍然极严,但对我这样长年在批斗下过生活的知识分子来说,境遇已经是很大的改善。人民出版社正在出“学历点史”丛书,负责此事的编辑林言椒很快便来约稿。我抽空赶写了一本《辛亥革命前夜的一场大论战》,介绍当年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斗争。其所以如此选题,一是由于我对辛亥革命史较熟,写来比较顺手;一是符合毛泽东所强调的路线斗争,如冰炭之不相容。但我对所谓儒法斗争是有所保留的,曾在编辑部内部坚持认为“近代无法家”;此书有些贴近儒法斗争的词语,是出版社为应付当时政治氛围加上去的。
说来令人汗颜,就是这么一本仓促写成的小书,竟受到京都大学文学部岛田虔次教授的重视。可能是由于当时在日本已买不到什么新出的中文学术书籍吧?所以便将此书滥竽充数,用做研究生的必读参考。1979年深秋我访问京都,岛田向我出示此书,上面用红色墨水圈圈点点,批注几乎把行间与天头地脚都挤满了,完全是中国老式读书人的习惯,但也更为增加我的惭愧,唯恐这本粗疏之作误导日本青年学生。
也许正是由于此书,1978年日本历史学者访问武汉时,往往要求与我会见,这可以说是我与日本学者结交之始。
比较重要的会晤有三次:
首先是日本的中国研究所访问团副团长北山康夫一行来汉,好像是在1978年春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出的翻译兼全陪,是我一向景仰的范老(文澜)的孙女。北山康夫原在奈良大学任教,已经退休,与岛田虔次是同一代人,并参加岛田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主持的辛亥革命研究班(相当于我们的研讨班,但延续时间较长,且不限于本校学者)。他主要是研究清末民初的会党,所以一开始便介绍这方面的情况。我也介绍了国内研究辛亥革命的情况,顺便还谈到黄一欧(黄兴长子)对宫崎滔天一家的深情回忆。我不知道范老孙女是如何翻译的,可能是增添了年轻女性的柔情,北山老人深深感动了,面色渐红,眼眶湿润。他郑重地对我说:“我珍藏着当年宫崎编的《革命评论》,日本全国也只有两处保存,现在愿意赠送给章先生,供中国辛亥革命研究者参考。”我喜出望外,感谢不迭,认为这是中日友好的历史见证。会见后,北山说在日本再见,我以为是礼貌性语言,并未在意。
但不久中国研究所就寄来正式邀请函,只是由于该所经费有限,无法提供全部食宿、交通费用,我的访日申请因此未获上级批准。不过北山倒是言而有信,很快就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访日代表团把《革命评论》捎给我。这是极为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至今还珍藏于华中师大历史研究所。我也信守对北山的承诺,凡需参考者都可以利用,从不视为私有。
北山之后的来访者是狭间直树,他随同汉学大师吉川幸次郎率领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访华团来汉,是团中少数年轻学者之一。吉川的中国古典文学根底很深,提出要去襄阳拜谒孟浩然墓。湖北省外办一时想不起适合人选,便要我陪同前往。唐代文学史非我本行,孟浩然的诗也只记得几首,可说毫无研究,因此内心非常惶恐。幸好当时“文革”疮痕还未完全平复,襄阳之行临时取消了,狭间便乘机与我单独磋商访日问题。狭间代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提出邀请,实际是根据岛田虔次的建议,预定1980年初在该校文学部讲一个月的课。我当即欣然同意。
紧接着东京大学的佐伯有一与古岛和雄两位教授也联袂来访。他们已得知中国研究所的邀请计划搁浅,表示愿向文部省疏通,促成我的访日成行。
回想起来,我觉得20世纪70年代末在海外有股“中国热”,遍及各行各业及社会各个层面,而学术界热度尤高,谁都想首先邀请中国学者访问,而且越多越好。美国、日本的学者恰好都在1978年同时选定我为邀请对象,这大概也是缘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