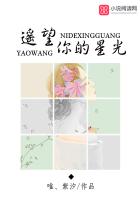九月十一日,星期二,晚上九点。
十分钟后,我们在东四十四街一栋富丽堂皇的老式褐石房子前按门铃。
一名衣着光鲜的管家前来开门,马克汉递上他的名片。
“请马上把名片交给贵医师,告诉他有要紧事。”
“医师刚吃完饭。”威仪十足的管家对马克汉说道,随即引着我们进入一间豪华的会客室,里面摆放着非常舒适的座椅,垂挂着丝质的帘幔,弥漫着柔和的灯光。
“典型的妇科医生住宅,”万斯看了看说,“我肯定这位医生也是位高尚优雅的人士。”
万斯的断言果然正确。过了一会儿林格斯特医师走进会客室,他看着马克汉的名片,仿佛这张名片上刻的是让他无法解读的楔形文字。年近五十的他身材高大,有着浓密的头发和眉毛,还有一张惨白的长脸。虽然五官不太对称,但还说得上是英俊。他穿着晚宴服,给人一种严谨且身份地位不同寻常的印象。在一张桃心木刻制的蚕豆形桌子旁坐下后,他用疑问却有礼貌的目光看着马克汉。
“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见教?”他慎重地请教马克汉。他的声调悦耳,说出来的每一个字都让人如沐春风。“你们很幸运能见到我,”不待马克汉回答,他继续说道,“我看病人只接受预约。”他似乎认为我们没经过预约程序就闯来,这对他来说是种侮辱。
马克汉本就不是那种虚伪矫饰、爱绕圈子说话的人,他直接切入主题。
“我们来访不是为了征询你的专业辅导,医师;而是跟你以前的一个病人有关——玛格丽特·欧黛尔小姐。”
医师若有所思地看着眼前的金色镇纸。
“哦,是的,欧黛尔小姐。我才看到她遭人杀害的新闻报道,真是让人难过。有什么我可以效劳的吗?当然,你们也知道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医生有义务保护病人的隐私——”
“我十分清楚这点,”马克汉打断他的话,“但另一方面,每位市民也有协助检警当局把谋杀案凶手绳之以法的义务。要是你所知道的事有助于我们抓到凶手,我非常希望你能告诉我们。”
林格斯特医师微微举起手,礼貌地说:“当然,我会尽全力帮助你,但你得告诉我你想知道什么。”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医师,”马克汉说,“我知道欧黛尔小姐是你的长期病人;而且我也相信,在她告诉过你的个人私事中,很有可能能找出和她的死有直接关系的线索。”
“但是,亲爱的——”林格斯特医师又看了一下马克汉的名片,“呃——马克汉先生,我和欧黛尔小姐之间仅是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
“可是,根据我的了解,”马克汉大胆地说,“虽然从技术上来讲你说得没错,不过,让我这么说吧,你们之间还有层非专业的关系。也许我这么说比较恰当些,在处理她的个案时,你的专业态度超越了该有的专业层次。”
我听到万斯在那里偷笑——而我对马克汉咬文嚼字、拐弯抹角的骂人方式也差点笑出来。但林格斯特医师似乎不受这些话的影响。在让人有点难堪的气氛中,他终于开口了。
“严格地说,我承认在我长期治疗她的这段期间里,我对这位年轻女子产生了一种——可以说是一种父辈的喜爱。但我想她可能根本没有感受到我的这份情感。”
万斯的嘴角微微抽动,他坐在那里一副想睡的模样,他用好奇又带点取笑的眼神看着林格斯特医师。
“她从来都没跟你说过,任何导致她焦虑的私事吗?”马克汉问。
林格斯特医师把十根手指合成金字塔状,显得十分认真地在回答这个问题。
“没有,我想不起她有过任何这方面的叙述。”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十分慎重而且文雅,“基本上,我对她的生活习惯大致还算清楚;但细节部分就不是我这位医疗顾问可能知道的了。根据我的诊断,她神经失调是因为晚睡晚起、亢奋、暴饮暴食,我认为这些都跟她放荡的生活作息有关。这位现代女子,在这个发烧的年代,先生……”
“请问,你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马克汉没耐性地打断林格斯特医师的话。
林格斯特医师显得很吃惊。
“我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让我想想。”显然他得很努力才能回想起来,“大概两个星期前吧——挺长一段时间的事了,我真的记不起来。需要我查看一下档案记录吗?”
“那倒没什么必要。”马克汉说。他顿了顿,亲切地看着他。“你们最后一次见面,是‘父爱式’的会面,还是‘专业式’的看病?”
“当然是看病。”林格斯特医师的眼神沉着而冷淡;但是我却觉得,他的心情清清楚楚写在脸上。
“见面的地点是在这里还是她的公寓?”
“我想是她的公寓。”
“医师,你时常去看她,有人这么对我说,而且没有固定的时间……这好像跟你只通过预约看病的说法不太一样吧?”
马克汉的语气虽然不会让人感觉不舒服,但我知道他的问题本身隐含了对这位伪善医生的不满情绪。我也感觉他有所保留。
林格斯特医师正要回答,管家出现在门口,指着桌旁矮台上的电话,表示有外线。连声抱歉后,林格斯特医师转身拿起话筒。
趁这个机会,万斯在一张纸上写了不晓得什么东西,然后偷偷递给马克汉。
接完电话后,林格斯特医师傲慢地站起来,带着轻蔑的态度冷峻地看着马克汉。
“难道检察官的作用就是,”他冷冷地问,“拿侮辱人的问题让备受尊敬的医生难堪吗?我倒还不知道医生看病人是非法的事——甚至是原罪。”
“我现在不是在讨论,”马克汉特别强调“现在”两字,“你有没有违法。不过,既然你提起了,我倒要问问——昨晚十一点到十二点间,你在哪里?”
这个问题产生了震撼效果。林格斯特医师突然像是一根紧绷的绳索,慢慢地僵直挺立;他冷冷地看着马克汉,原本优雅柔和的态度顿时全无,而我也察觉出他压抑在愤怒之下的另一种情绪:害怕。他的愤怒中透露着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感。
“我昨晚在哪里,不关你的事。”他非常吃力地说出这话,呼吸相当急促。
马克汉一动不动、冷静地看着眼前这个发抖的人。这样的冷静攻势倒是完全瓦解了对方的防御,林格斯特医师的情绪显得有些失控。
“你在这里指桑骂槐地羞辱我,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大吼着,变得面目狰狞,脸色铁青;两手痉挛,不停地抖动;他全身颤抖不止。“滚出去——你和你的两名跟班。在我叫人把你们轰出这里前,立马给我滚!”
马克汉发火了,就在他准备接腔时,万斯拉住了他。
“林格斯特医师正温和地示意我们离开。”他说,并巧妙地把马克汉拉到身边,然后硬拉着他离开林格斯特医师家。
我们坐上车,在回到史杜文生俱乐部的路上,万斯一直在愉快地窃笑着。
“好厉害的家伙,简直偏执狂一个。或者,更像是精神错乱的躁郁病患者——那种大脑有问题的人:时而疯疯癫癫,时而神智又很清楚。总之,林格斯特医师就是属于精神不正常的那种——这都是因为性需要没法得到满足引起的。而他也正好到了这种年纪。神经衰弱——这位神经科名医现在就是这个样子,随时都会突然发动攻击。哎呀!幸亏我及时救了你,这个家伙简直就跟响尾蛇一样的‘安全’。”
他故作沮丧状地摇头。
“说真的,马克汉老家伙,”他继续说下去,“你得好好研究那家伙的脸,正所谓相由心生。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位绅士宽阔的前额、不规则的眉毛、淡里透亮的眼睛和上缘薄而突出的耳朵?这人是个聪明的魔鬼,但却是道德的蠢蛋。小心这些梨形脸的人,马克汉。就让他们把那些古希腊式的挑逗暗示留给那些会上当的女人吧!”
“不知道他真正知道哪些事。”马克汉生气地埋怨着。
“噢,他肯定知道一些事——这毫无疑问!要我们也知道的话,我们的调查将会有相当大的进展。从另一方面来看,他隐藏的事实,多少和他不愉快的经验有关。他的优雅作风有点过头了,礼多必诈。他下逐客令时的暴跳如雷,才是他真正的心情。”
“没错,”马克汉同意。“问到有关昨晚的事,他跟吃了炸药一样。为什么你要我问他这件事?”
“理由有很多——他佯称自己才刚看到欧黛尔小姐被杀害的报道,显然很虚伪;他声称保护病人隐私的话过于虚假;他自认为对那女人充满父爱情愫的告白,过于谨慎却不够真实;另外,他拼命努力地要想起他最后见她的时间——特别是这点,让我更加怀疑;还有,他那发狂的表情。”
“嗯,”马克汉承认,“这个问题发挥了作用。我想我得再见见这位上流社会的医师。”
“你会的,”万斯说,“我们刚才只是出其不意地找他,不过下一次在他有时间思考并且编造说法后,他会有能力反击。今晚已经告一段落,到明天前你有足够的时间好好思考对策。”
不过对大家关心的欧黛尔谋杀案来说,这一晚还不算告一段落。我们回到史杜文生俱乐部的休息室没多久,一名男子朝我们所坐的角落走来,很有礼貌地向马克汉行了个礼。让我意外的是,马克汉站起来跟他寒暄问好,并且指着位子让他坐下来。
“我还有一些事要问你,史帕斯伍德先生,”他说,“假如你有时间的话。”
就在听到他名字时,我更加专注地看着这个男人,因为,我承认我对这位昨天晚上陪死者外出吃饭看戏的神秘护花男子十分好奇。史帕斯伍德是典型的英国贵族,动作一板一眼、慢条斯理而保守,穿着时髦雅致。他的头发和胡子泛着灰白——毫无疑问,这更加衬托出他皮肤的白皙,身高六尺的他身材比例十分匀称,不过稍稍有点瘦。
马克汉介绍他和万斯与我认识,并且简单说明了我们和他一起在调查这件案子,让他完全信任我们。
史帕斯伍德刚开始还怀疑地看着他,不过很快地他就决定听从马克汉。
“我把自己交给你了,马克汉先生,”他回答得相当有教养,不过声调有点高亢,“你认为任何有帮助的事,我都会配合。”他面带歉意地向万斯微笑。“我的处境不妙,所以我有点敏感。”
“我主张扬弃道德论,”万斯轻松地说,“无论如何,我都不是个道德论者;所以我对这件事的态度相当开放。”
史帕斯伍德浅浅地笑了笑。
“我真希望我的家人也有你这样的态度;但恐怕他们无法容忍我这状况。”
“我想我应该告诉你,史帕斯伍德先生,”马克汉打岔说,“到时候,我很可能会传唤你出庭作证。”
这名带着贵族气息的男子立即抬起头来,满脸忧郁,没有说话。
“其实,”马克汉接着说,“我们即将展开逮捕行动,我们需要你出面作证,说明有关欧黛尔小姐回公寓的时间,同时证明在你离开后有人在她房里。你听到她大声呼叫求救,这可能是将凶手定罪的重要证据。”
史帕斯伍德似乎对他和死者的关系即将曝光感到相当不安,他两眼无神地坐在那里。
“我了解,”他终于开口,“但这件不名誉的事一旦公开,我这辈子就完了。”
“或许不会传你出庭作证,”马克汉安慰他说,“我向你保证,除非必要,否则不会传你出庭。现在,我特别想问的是:你认不认识一位林格斯特医师?据我了解,他是欧黛尔小姐的私人医师。”
史帕斯伍德显得一头雾水。“我从来没听说过这号人物,”他回答,“而且,欧黛尔小姐没有跟我提起过任何医生。”
“那你有没有听她提起过史基或是汤尼这样的名字?”
“从来没有。”他的答案非常肯定。
马克汉失望地不发一语。史帕斯伍德也沉默不语地坐着发呆。
“你知道吗,马克汉先生,”过了几分钟后他说,“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但其实我真的很在乎这个女孩。我想你们已经封锁了她的公寓……”他欲言又止,眼神里几乎充满了乞求,“要是可以的话,我想再到她的公寓看看。”
马克汉同情地看着他,但还是摇摇头。
“不行。你一定会被接线生认出来——也可能会被记者看到——那时候我就无法保证你和这件命案没关联了。”
这人显得很失望,但没再说什么;接下来的几分钟又是一阵沉默,没人开口说话。这时,一直窝在椅子里的万斯稍微坐直了一些。
“我说,史帕斯伍德先生,你还记不记得,昨晚你跟欧黛尔小姐从剧院回来后和她在一起的半小时里,她有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
“不寻常?”他的语气中充满了讶异,“没有啊。我们聊了一会儿,没多久她似乎累了,于是我向她道晚安,并且约她今天中午一起吃午餐,之后我就离开了。”
“不过,现在看来,可以相当肯定的是,似乎当你还在那时,就已经有人躲在她的公寓里了。”
“你说得非常有道理,”史帕斯伍德同意万斯的说法,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她的尖叫似乎说明了在我离开后没多久,那个人就从躲藏的地方出来了。”
“听到她喊救命,难道你就不觉得奇怪和怀疑吗?”
“一开始我确实这么觉得。可后来她告诉我没什么,要我回家,所以我以为她只是做了个噩梦。我知道她已经很累了,我走的时候让她睡在靠近门边的一张藤椅上,而呼叫声似乎也就是从那里传出来的;所以我很自然地以为她已经睡着,只是因为做了噩梦才惊叫。假如当时我不这么认为就好了!”
“真让人痛心。”万斯沉默一会儿后又问,“你有没有注意到,当时客厅里衣橱的门是开着的还是关着的?”
史帕斯伍德皱着眉头,努力地回忆当时的情景,但不能确定。
“我想应该是关着的。要是开着的话,我应该会注意到。”
“那你也应该不知道衣橱上的钥匙当时是否在钥匙孔里?”
“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衣橱有没有钥匙。”
就这样,这个案子又讨论了半个小时,然后史帕斯伍德起身离去。
“怪事,”马克汉说,“这么一个有教养的男人,怎么会被一个胸大无脑、水性杨花的女人迷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很平常,”万斯回说,“你的道德标准太高了,马克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