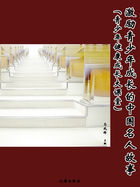(1909年12月10日)
拉格洛夫几天前,晚霞散尽时,我乘上了开往斯德哥尔摩的列车。车厢内灯光幽暗,车窗外夜色浓重。疲惫的旅客们休息了,只有我静静地坐着,谛听火车撞击铁轨的吭吭声。
我浮想联翩,以往去斯德哥尔摩旅行的情景一幕一幕地出现在眼前:通常,是为了去办些麻烦事——去通过考试啦、为手稿找个出版商啦,等等,而这一次,我是去领诺贝尔文学奖,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整个秋天,我离群索居于韦姆兰的一幢老房子里,而现在我却要在大庭广众之中抛头露面。我已经过惯孤独隐遁的生活,对喧闹繁华的场面甚为不适。一想到要面对那么多人,不禁惶恐。不管怎么说,我内心深处,对接受这一殊荣充满了欣喜。我想象着那些分享我的幸运的人们高兴的脸庞。他们中有我好的朋友,我的兄弟姐妹、我那年迈的母亲——她仍留在老家,非常欣慰地在她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一天。
我又想起了我的父亲。一种深切的悲哀占据了我的心田——他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再也无法走到他身边,告诉他获奖的喜讯。我知道没有一个人会像他那些听到这一喜讯后更加兴高采烈了。我从未见一个人,像他那样酷爱文学作品并尊敬它的作者。我真希望他的在天之灵能获悉我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是啊,我无法亲自告诉他这一消息,这是我心中最大的遗憾。
有过在奔驰的列车中过夜的经验的人都知道,当列车毫无震颤地平稳滑行,万籁俱寂中,“咔嚓,咔嚓”的车轮转动声变成了节奏安详的旋律,它能抚平人们心中的一切烦恼和忧虑。这时,朦胧入睡的旅客往往会产生在浩瀚的宇宙中飞翔、飘浮的感觉。是呀,我当时就有这种感觉。恍惚中,我坠入了幻想——我也许是搭车前往天国,和父亲去重逢!火车行驶得那么轻快,像是驾虚凌空一般,我的思绪比列车的速度更快。
父亲像往常那样,坐在前廊的摇椅上,面对着阳光明媚、鲜花盛开、小鸟啾啾的庭园。他正念着《弗里提奥夫萨迦》。当他看到我时,便放下书,把眼镜高高地推到前额上,从椅上站起,朝我走来。他或许会说:“你好,我的女儿,见到你很高兴!”或许会说:“嗨,你来啦!你好吗?我的孩子!”——这些都是他以往常说的。
然后他重新坐上摇椅,揣测我为什么会来看他。“孩子,你一定碰到什么困难了!”他会这样突然地问道:“不,父亲,我一切都很好。”我回答,想把这好消息告诉他。可话到舌尖又咽了回去,我想把它说得含蓄点。“我是来向您讨个主意的,父亲,”我说:“因为我欠了一大笔债。”
“如果是为这件事找我,我恐怕爱莫能助。在这天国,虽说样子很像韦姆兰老家,什么东西都不缺,可就是没有金钱。”
“我欠下的不是钱,父亲。”我会这样说。“那更糟糕,”父亲说,“你还是从头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吧,我的女儿。”“我想求你帮忙不算过分,因为这是您开的头,父亲。您还记得吗?您以前常弹钢琴、唱贝尔曼的歌给孩子们听。每年冬天,您至少让我们朗诵两回泰格奈尔、鲁内贝黑和安德森的作品。不是吗?我现在欠的债就是从那时开始的。父亲,就是您使我喜欢上那些童话故事与英雄传奇,热爱我们的国家,无论在贫富荣辱、顺境逆境中都要热爱人生,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才能偿还这笔债。”
父亲一定会从椅子上站起来,点头微笑,显出全然放心的神态,说:“能够使你欠上这笔债,我倒是很高兴的。”
“是呀,父亲!但问题是,您还不了解我欠下了多少债!”我说:“使我获益匪浅的人可真不少呀!父亲,还在您年富力强的时候,就常有一些贫穷的、无家可归的流浪艺人,在韦姆兰演唱歌曲和表演喜剧,他们的粗犷、欢闹的街头艺术,使我增长了不少见识。还有那些森林边上的灰色小农舍里,老爷爷、老奶奶曾在我童稚的心灵里灌输了许多聪明、美丽的小姑娘以及小水怪、小精灵的故事,他们也是我的启蒙老师。他们使我懂得,冷峻的岩石、幽暗的森林,是那么的富有诗意。再想想那些隐居在幽静的修道院里的那些脸色苍白、颧骨高耸的神职人员讲的传奇故事吧!他们讲述亲眼见到的怪诞景象和亲耳听到的奇妙声音,令人难以忘怀。我在作品中借用了他们那些口头创作的故事。还有我们那些徒步走到耶路撒冷去朝圣的农民,他们这一非凡的举动为我提供了很多的创造素材。难道我不曾欠下他们的债吗?不仅我欠了人间的债,对大自然,我也欠了债。因为,飞禽走兽、树木森林、鲜花青草,无不向我吐露了他们的秘密,无不使我的创作得益。”
父亲脸上绽露出笑容,显示出一点都不担心的神色。“难道你不明白,我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我说道,表情越发沉重:“在人世间,没有人说得出我怎样才能还清这笔债,但我相信身在天国中的您有办法帮助我。”
“是的,我会帮助你。”父亲说道,神色仍然像往常那样漫不经心的从容自如,“别担心,孩子,你的困难总会有法子解决的。”“父亲,可我的债还不止这些呢!那些创造了我们的文字、语言,并把它铸成那么称心如意的工具,那些教会我写一手漂亮的瑞典文的人,也是我的债主。还有,那些把写作变成一门艺术的先驱者,在我们时代之前的散文、韵文好手,对在我孩提时代就受其恩惠的我国的、挪威的大作家们,我不是也负债累累吗?我有幸躬逢其盛,生活在我国文学的鼎盛时期,文坛泰斗与后起之秀都以呕心沥血的作品滋养了我,激发我的想像力,砥砺我投身文学事业,使我的梦想结出丰硕的果实,难道我不欠了他们的恩泽之债吗?”
“是呀,是呀,”父亲称是,“你说的对,你果然债台高筑,但不要担心,我们总得找出个还债的办法。”“父亲,我认为您还不了解这对我有多么困难。我还承受了我的读者对我的多大恩情,从派我去南方旅行的年迈的国王与他的小王子,到读了《骑鹅历险记》之后用童稚的笔迹写信向我致意的小读者,我实在欠了无法偿还的债。要是没有人读我的书,我岂不是一事无成?我也不会忘记写文章评论我的人士。一位丹麦的著名评论家仅写了几句话,就为我在那个国家赢得众多的读者。而在他之前,还没有文学批评家如此炉火纯青,把胆汁般的批评与佳肴般的褒扬融合起来,谆谆地教诲我。可惜现在他已谢世。还有在国外为我写文章的那些人,无论是赞扬或批评都是对我的鞭策。”
“是的,是的,”父亲虽仍是这样说,但我的神色凝重起来,他一定开始明白,我的难处还不好办呢!
“我会记住助过我一臂之力的人们,父亲”,我说:“感谢我忠诚的朋友赛尔德,当我还默默无闻时,就为我四处奔波,帮我打开事业的大门。我的好朋友、旅伴,不仅带我去南方,看到许多珍贵的艺术品,而且使生活本身更愉快幸福,使我拥有伟大的爱、崇高的荣誉和名声。这些情谊叫我如何报答?父亲,您明白我为什么要求助于您了吗?”
父亲低头陷入了沉思,似乎不那么有信心了。“我同意你所说的,我的女儿,要帮你解决这些麻烦,还不容易。不过,除此之外,你大概没有再欠别人债了吧!”
“唉,父亲,前面所说的债务已经使我难以偿还了,可是我最大的一笔债务还没说呢!这就是我特意来听取您指点的原因。”
“我真不明白你怎么旧债未了,又背上了新债!”父亲不解地说。“事情是这样的,”我回答说,接着把获奖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我简直不敢相信,皇家科学院?”父亲吃惊地看着我,从我的表情中他觉察到,这一切是千真万确的。他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因喜悦而颤动着,眼中满是泪水。
“对于提名我当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和授奖决策人,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父亲,他们给我的不仅是名誉与金钱,他们对我充分信任才把我拔擢出来,把我的名字传遍全世界!我怎样才能偿付这笔天大的债务!”
父亲一言不发地坐着,他的手擦着兴奋的泪花。他举起拳头捶着摇椅的扶手,对我说:“这些债务无论天上或人间都是无法解决的!所以我也不必伤透脑筋了!你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我高兴都来不及了,顾不上担心别的了!”尊敬的国王陛下,尊敬的王储殿下,女士们、先生们——在我没有找到更好的回答之前,我只能荣幸地请你们与我一起,为瑞典文学院干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