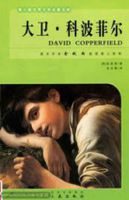小天回来了,她在财政局学了两个月,花掉单位一千多元,带着一个鲜红的结业证回来了。按说她该喜气洋洋红光满面才对,有人给拿学费,又不来单位上班,学习学累了还可以中途休息两天,和财政局的人弄明白关系,收据还可多开一点儿。小天占了这么多好处,却没有一点儿高兴的意思,相反她的脸颜色铁青,灰里带黄,她的眼睛肿成一条缝儿,看东西都要努力睁。主任杜马最先发现了小天的异常,他像看女儿一样看了小天有一会儿,就差伸出手扒一扒小天的眼睛。他惊讶地问道: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
小天的年龄真可以做杜马的女儿。小天今年二十三岁,杜马都四十八岁了,杜马若高产生小天这个年岁的孩子都能生俩,小天看我在场,就回避说:没怎么呀,肾炎你不知道哇?
杜马知道她不会说实话,就说:你这么小就肾炎怕是不可救药了,像你这么大的女子,得得尿路感染就不差啥了,所以你得注意不洁性生活。
小天把手套打在杜马的脑袋上,杜马一边捂头一边道歉,说:你看,我不过是和你开开玩笑,你怎么学习几天连主任都不认识了。小天就扑哧一声笑了。
我正在摆弄我的手机,满克把它给修好了,他一分钱没要,说是权当向我赔罪了,说我们以后扯平了,谁也不准再提那档子事儿。我见他诚实可信,依了他。
我正在想满克到底在配件上花了多少钱,小地背着包进屋来了。她一进屋就摔东西,摔包,摔书,摔桌上的算盘。算盘对小地来说是个幌子,她平日里算账都用电子计算器。计算器她锁在抽匣里,算盘却可桌子乱飞。她摔东西也是捡不值钱的摔,有用的她不摔,但是可摔的东西虽廉价,攻势却十分猛烈,她似乎有这方面的表演才能,只有出现响动与破碎她的心里才能安慰。大家都被她摔愣了,杜马想拦她又不敢,说:你抽什么风?你早晨来就抡风扫地,不怕一天晦气?
小地说:哎,我就是不怕晦气,你若怕你走哇,我巴不得清静呢。
杜马对小地永远没办法,他说:我可不想走怎么的,我这就走,我上楼开会去。
杜马趁机溜了,杜马的高明之处在于在关键之处如何斡旋,他谁也不得罪地生活在三个女性之间。他和他的手下的科员老年一样,不管什么复杂的情况都不忘记抽身,老年比他表现得更甚,老年是事不关已高高挂起,你这头翻了天了,他都会手捧他的书,戴着他的老花镜在那里孜孜不倦。做个假设吧,如有人在他眼皮底下爱得如胶似火,想有肌肤之亲,都不用挂帘儿,就地执行一点问题没有,他保证连看一眼都不会。上次杜马媳妇的事那是他一步赶上,不然就是给他点金银财宝他也不会出来。偏偏他机体的免役力又强,不会出现异常反应,甚至连心都不会颤一下。
小天见杜马出去,她也跟了出去。她有事要和杜马说,别看小天二十三岁,可就像三十二岁一样诡谲多变会使绊子,做事做人都是算尽天机滴水不漏。她若恨谁不当面表现,她会背后让你疼上一年,下一年你再见到她时老早就躲,不躲你也会不自觉摸摸麻麻的脊背,再胆大的人也憷她三分。平日里没人敢惹她,谁惹她,她会记你一辈子,一辈子加小心一个场所可能,加小心一个人却很难,谁都不能一如既往,谁都有松懈的时候,妥了,来干儿吧。因此大家防范小天比防范小地用心十倍,虽然两个人一明一暗,一水一火,又都是单位的中枢神经,但是谁都知道,那分量是一样的,若想对付她们,唯一的招数就是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水不来先憋坝。
所以小天一出去,门外进来的老年就点头哈腰对小天说:回来了,天小姐,我还给你准备了一只手镯呢,你们三个人人有份,不过,老年压低了声音,你的比别人的成色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