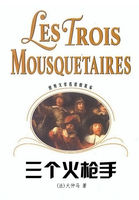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然会想起点点。有时是在梦中,有时是在一本书或一个电视画面、甚至是某一个人的一句言辞中,她总会像一只不期而至的红蝴蝶,翩然扰动我的记忆。回到故乡时,我也常会找时间到学院走走。远远地看见古罗马城堡般的物理楼,或者,漫步在物理楼后花木掩映的假山上,看着那除了漆色焕然而其它几乎一成未变的红亭子,我的呼吸便情不自禁像耳畔的清风一样悠长,我的眼前便会清晰地闪现点点脑后那会随着她的话音轻轻晃荡的红头结。我常常会惊异于几乎是沧海桑田般的巨变后,学院怎么还如此完好地保存了这座陈旧的大楼和古老的八角红亭;更会叹惜我那不中用的记忆,怎么就再也不能完整地复原哪怕一会儿点点的容貌呢?
也许是点点的红头结太抢眼了吧?
如果不是某种特殊的原因,我和点点也许算得上是青梅竹马的小伙伴。我们住在一个大院里,父母长辈都是学院的职员。虽然我们不在一个班级,毕竟也是同一所小学同一级的同学。很小的时候,比如三年级以前,我们一度和同院的孩子们成天在一起嬉戏,有时星期六晚上还会成群结伙地溜到学院去,在大草坪上玩官兵捉强盗,在物理楼后的假山上玩捉迷藏,直到哪家的家长来大呼小叫地催唤。由于点点年纪小,又是女孩,就常常成为待人来解救的“牺牲兵”。有一回就是我借着夜色和个子小而不为人注意的优势,从假山后的竹林中一跃而出,成功将点点救出。她冲我发出的狂喜的尖叫声,以及她死命攥紧我的手,吃力地随我撕脱“敌人”堵截圈时沉重的喘息声,在此后好些时日里都不断回荡在我的脑海中,让我热血沸腾,回味不已!
还有一个片断也已成为我记忆中不可磨蚀的亮点。
我们的家属大院里有一道特殊的风景,那就是院子中央,有一幢在那些年代里不可多见的欧式洋楼。三楼三底,前后两个门,各住着一户人家。每户人家门前还有一个百把平方米的独立花园。其中一家住着学院的副院长,还有一家就是点点家,住着点点父母和她外公、外婆一家。点点的外公是从解放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是学院里两个级别最高的教授之一。我家和其它各家的大人们见到点点的外公莫不谦卑而恭敬。部分原因还在于他的月工资竟有275元之多,而我的父亲作为数学系的讲师,工资只有50元出点头,连他的零头都不到!
点点家的洋房也是很高级的。是民国初年创办学院的英国传教士的住宅。红墙、尖顶,带有老虎天窗的阁楼。底层下还有一个约有一米高的隔空层,以防潮和通风。隔空层四面有8个可容一个人钻进去的方口,以便于检修和通风。我们这帮孩子们中胆子大些的便经常会钻到里面去玩。里面大极了,就是太矮,仅够一个小个子的孩子勉强坐着。进出则要爬行,而且越爬越黑,有时头顶上还有弯弯曲曲的管道。但捉迷藏是个再理想不过的的藏身处了。
有天我刚钻进一个口子,点点居然也拖着个书包,兔子似的一蹿一蹿地紧追着我爬了进来。我赶她走,她向我翻白眼,还拣小石子砸我。我只好暴露了我的“司令部”。所谓司令部是我自己命名的。我在一个比较高敞些的隐秘角落铺了些稻草,还放了一小截蜡烛和火柴。我经常会在下课后领几个听命于我的院外同学到司令部来,点上蜡烛在那儿呆一会,沉浸于一种神秘的满足之中。这时候,我常常乐于将自己想像成威虎山上的座山雕,还将其他人封为八大金刚。
这回,只有我和点点两个人,围着微微颤动的烛光相对而坐。头一回钻进这里来的点点很兴奋,特异和神秘感让她平时有点苍白的脸上浮泛着鲜润的红晕。她不停地问长问短,还用手好奇地扇动烛光,甚至还深深地嗅几口我觉得有些呛人的烛烟,说是真好闻,我简直是来到我梦中的童话世界啦。可能是为了以后能经常来这里,她甚至还从铅笔盒里拿出套刚发行的新邮票给我看,说是她外公刚给她买的,一般人她才不让他们看呢。我那时候迷集邮,但薄薄的一本邮票本里全是跟人换或者赌来的盖戳邮票。那套新邮票馋得我心都快跳出嗓子眼了。点点偏着头,得意地欣赏着我的贪婪,直到我恋恋不舍地将邮票还给她时,她竟莞尔一笑,大方地说:送给你吧。
我心花怒放,连声道谢,还把我的“宝座”让出来给点点坐。其实我的司令宝座也不过是用一块从家里偷出来的大毛巾裹着的两块方砖而已。但毕竟它是一种权威的象征,点点坐上去还是高兴得手舞足蹈,不停地说这说那的。我则努力显示出习以为常的主人气派来,嗯嗯哈哈地很少说话。我在点点面前从来就有一种下意识的拘谨。这自然因为我自己也还小,生性也不太活泼。可是点点也不大。我们那年都刚升三年级。主要还是因为我和点点在身份上的差异吧。在我们这个大院里,除了这小洋楼里的两户人家有较高地位,其余都是一般教职员工家属,都住在洋楼周边的平房里。而这个空间,包括我的这个司令部的头顶上,实际上都是点点的世界,我在她面前免不了就有些当时还说不清道不明的卑怯感。所以当点点突然冒出那句完全出乎我意料的话来时,我彻底地乱了方寸而脸颊发烫,以至怀疑耳朵出了问题而迟疑地僵着不动。
实际上,30年后的今天,当我想起这句话来,还会感到心血的潮动。
点点说的是:哎,我们可以在这里睡一觉哩。说这话时,她已一脸满足地躺下来,头枕着我的“宝座”,两腿在松软的稻草上啪啪乱蹬。见我僵着不动,她又拉了我一下:睡下来呀,这稻草床真舒服,我还从来没有睡过这种床呢,太好玩了。可我还是没敢躺下去。因为铺稻草的地方不多,我要睡下去的话,就要和她紧紧挨着了。点点吃吃地笑了,身子往里让了让又说,睡下来嘛!
我终于小心翼翼地睡了下去,尽量不碰到点点的身子,头也歪到一边不敢看点点。没想到点点一个侧翻,一手撑起面颊,两只大眼睛闪烁着异样的光泽,活像两团跳荡的烛火,就那么笑盈盈地看着我。现在想来,那一刻实际上并不长,因为通风口外忽然传来杂乱的人声,似乎正有人试图进来捉我们。但当时我的感觉却恍若度过了一段梦一般漫长的时间。我被点点逐渐深重起来的呼吸包围着,其中还杂揉着点点身上某种特有的气息的汗味。这让我更觉神思恍惚了。
你讨厌我吗?点点有点撒娇似地问了一句。我赶紧摇头否认。那你怎么看都不看我一眼?大人们不都是这么睡觉吗?他们还抱在一起呢!
摇曳的烛光在我眼前幻化出一圈又一圈光晕,点点的笑容也越来越像是一朵怦然绽放的昙花。我真想就此抱住点点,可是终究还是没敢那么做。我还是太卑怯也太没有思想准备了。我鼓足勇气才小心翼翼地将手搭在她背上。可只是一小会便触电般抽了回来。不知是这儿太热还是怎么的,她的背上竟是滚烫的,隔着一层轻薄的布衫,我还是能感觉到手上湿湿地,沾了她的汗。有人进来了。我讪讪地说了一声,便吹熄蜡烛,招呼点点迅速从另一个出口爬了出去。直到今天(恐怕是永远),我都异常清楚地看得到点点爬出洞后留给我的那个奇怪的表情。我相信那决不仅仅是因为洞外那晃眼的阳光的刺激。我想扶她起身,却被她推开了。并且,伴随着一个娇嗔的鼻音,鼻子和嘴巴紧紧地挤作一团,她给了我一个当时只觉得莫明其妙的白眼。
三年级下学期,点点突然随她的父母离开外公家,调到北京去了。但两年后,她不知怎么又单独回到了外公身边。并且又回到原来的小学上学。这以后,直到六年级小学毕业,我们因文革爆发而呆在家里的一年多里,我们还是经常会有在院子里或学校里照面的机会,但却几乎成了陌路人。从北京回来的点点似乎是突然长大了,也许是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份与性别和我们的不同。给我的印象是她变得高傲起来,不再参与同院小伙伴的游戏不说,放了学也很少出门。令我不快的是,有时她就从我身边擦肩而过,居然连正眼也不给我一个!当然,父母不在身边了,外公外婆对她管束紧了也说不定。
不过,我更愿意相信她是瞧不起我了。因为就从她去北京时起,我父亲为补家用的不足,在家门口的空地上围起了一个栅栏,养了八只成天嘎嘎乱叫的鸭子。不仅嘎嘎乱叫,八只肥胖得屁股都快坠到地上的鸭子还把围栏里拉得满地是屎,使人老远就能嗅到扑鼻的腥臭。它们还喜欢扑扑地乱扇翅膀,结果又把零乱的鸭毛弄得四处飘飞。别说点点,别的小伙伴也经常嘲笑我们家成了农民了,我则成了道地的小鸭倌了。
然而我虽然有些自卑,心底里还是很喜欢我的鸭子的。毕竟在那个贫乏的年代里,它们让我们一家5口有了一个丰富的营养源。八只鸭子都是母鸭,进入产蛋期后几乎每只鸭子都天天下蛋。而这主要是我的功劳,所以我与这伙看着它们长大的母鸭们有了一种别人难以理解的感情在。它们也特别喜欢我,每天早上只要我一搬开它们睡棚的盖板,八只鸭子便争先恐后拱出窝来,团团围住我呷呷乱叫,还一个个鸡啄米般拼命向我点头,有的还急不可耐地啄我的裤管。
它们之所以这么着急,之所以这么肥胖,这么会下蛋。原因就在于它们每天都会吃到我亲手为它们逮来的蜗牛。那些蜗牛个个鲜活肥满,对于鸭子来说,无疑是最为滋补的美味。一般人都想不到用蜗牛来喂鸭子。我也是偶然看到一只鸭子生吞了爬到鸭棚里的蜗牛,才知道它们爱吃蜗牛。岂止爱吃,我的鸭子见了蜗牛简直是不要命。起先我还怕它们噎着,每天逮了蜗牛回来先要用锤子将它们砸碎才喂,后来才明白多此一举。我的鸭子等不及我砸,早就把嘴伸到我的小铁桶里,一口一个,一个接一个的大个儿蜗牛便顺着它们逞得老长的粗脖颈滑进了嗉囊里。八个鸭子每天都要吃掉我用一公斤装的空漆桶装得满满的一桶蜗牛。
那么,我从哪儿逮到这么多蜗牛呢?
自然是学院里了。学院那么大,又没有旁人和我竞争。所以我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拎上小铁桶到学院去。蜗牛喜好栖居于阴湿的屋角、树根或乱石堆处。因此学院的物理楼后面的墙根处及不远处的假山四周、灌木丛、亭子脚处便成了我的必到之处。
有一天,我刚拣完物理楼后的蜗牛,一扭头,意外发现假山上的亭子里有个人。确切地说,首先引起我注意的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个十分抢眼的红头结,远远看去,宛如一只硕大的红蝴蝶,在淡淡的晨雾里隐隐绰绰地浮动。定睛再看,我认出那个人就是点点。而那鲜艳的红头结,其实是一条红领巾,只不过她把它当作头巾,挽在了脑后蓬松的黑发上。这时的点点,个子明显比两年前高了许多,站在亭子上,显得更高,细细长长的,就像一棵亭亭玉立的小树。她穿着一身白竹布的连衣裙,配上鲜红的红头结,显得分外窈窕而招人。
我借着树荫的遮掩,悄悄向她靠近。只见她在亭子里缓慢地踱着步,并不时地向物理楼方向张望着,有时还会伸出双手向那里招摇一下。她这是干什么呐?我感到纳闷。却不敢再近前去,怕给她看见我在拣蜗牛。可假山和亭子一带石头多,草木也密,是蜗牛最多的地方,我的蜗牛因此少拣了许多。而且以后的几天里,点点好像存心要和我过不去似的,居然天天出现在亭子里,我再怎么等,她也不会先我离开。有时手里还多了一本书,看了会就起身徘徊一阵,却怎么也不离开那个高高的八角红亭。
我不得不改变办法,次日起了个大早,哪儿也不去,抢在点点前先拣假山周围的蜗牛。果然,点点不在。可是正当我拱在亭子边上那异香扑鼻、垂满紫色铃铛般的紫藤架下搜寻得起劲的时候,耳后忽然感到一股热乎乎的鼻息,扭头一看,点点正弯着腰,伸长着脑袋打量我手中的铁桶,一脸的惊讶。我不禁红了脸,倏地跳开去。你别躲我呀!点点叫住了我:告诉我,你拣这些脏东西干什么?
我没躲你呀?我蹑嚅着,却不肯告诉她我拣蜗牛的目的。点点却把它说破了。她说她早就知道我家的鸭子都是吃蜗牛长大的,还颇有几分嘲讽地说她真不敢想象我们家人怎么吃得下这种鸭子下的蛋。我的自尊心大感伤害,以至忘却了难为情,尖锐地反驳她:怎么吃不下?鸭子吃什么东西,下出来的还不都是一样的蛋?我还问她知不知道所有的菜呵米呵都是用大粪浇出来的?难道你就不吃饭了吗?点点怔了一下,笑了。然后用和解的口气说:好了好了,我跟你说说玩玩的。何必生气呢?可是你还要回答我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这几天一见我在亭子里就不过来了?就因为我家是黑五类,你看不起我了吗?
怎么会呢?我连忙解释:我不就是不想让你看见我拣蜗牛吗?再说了,是你先不理我的。你从北京回来就不理我了,像个了不起的公主似的。
这回轮到点点吃惊了。她大叫道:原来你也是这么想的?我还一直在生你们气呢,自以为大了几岁就看不起女生了!你骗我吧?不然怎么会这样呢?
说着话,我们不知不觉地已在亭子上坐了下来。互相间的猜疑和敌意也像萦绕在身边的清风一样,在不断延展的话题中飘逝了。可是,谈得正开心的时候,我一不小心又把刚刚热络起来的氛围给破坏了。我问她为什么这些天天天到亭子上来,一坐老半天的,害得我少拣了不少蜗牛。我甚至还问她是不是忘了,红领巾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你老把它当头巾系在头上,恐怕是有点反动呢……
你瞎说!没想到点点一下子生起气来,脸色红一阵白一阵的,扭过头去好一阵不理我,我转过去看她时,她迅速擦了擦眼角,恨恨地说:我才不管那么多呢,反正我现在是黑五类子女,也没资格戴什么红领巾了。我把它系在头上,只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显眼一点。我天天到这里来,也就是为了让我外公能看到我。他被关在那里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外婆急得天天在家里掉眼泪,我不知怎么安慰她才好。只好天天晚上躲到阁楼上去。过去干干净净放满书的阁楼上,现在已是空空荡荡,书架上满是浮尘。我趴在老虎天窗上,望着天上的每一颗星星,求它们帮助我。最好能派来一只飞船,把我们一家都接到天上去,永远也不要再回来……你别这么看着我,我说的都是真话。外公外婆早和我说过,如果运动结束后他们还能活着,一定要申请回乡下老家种地去,再也不当教授了。外公说,我们老家可美了,水清得能当镜子,草木绿得像碧玉,新米做出来的饭又香又糯,只要有几筷青菜,像我这样的小孩都准会一顿吃它三大碗……
点点还说,她现在经常会在梦里见到外公:而且我清楚地听到他对我说,点点呀,我真想你呀,为什么你不来看看我呢?可是,我到物理楼去看他,那些造反派根本不让我进,连给他送点吃的也不行!
我顺着她的视线望去,一下子全明白了。点点的外公是物理楼里的高级教授。一个多月前,造反派抄了他们的家。并把点点外公“隔离审查”关在了物理楼。而这个亭子正对着物理楼她外公原来办公室的窗户,点点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让楼上的外公有可能看见她!可是,谁知道她外公现在被关在哪一间房子里,能不能看到她呢?
我的心揪紧了。一个月前造反派抄点点家那恐怖的一幕,又浮现在眼前。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点点外公竟有那么多的藏书,简直赶得上一个图书馆了。一大伙造反派调来一辆卡车,装走了满满一卡车,又回来再装第二趟。惊得四邻八巷的人都来看热闹。需要交待一下的是,我们这个家属院四面有一圈一人高的围墙。墙外有一条蜿蜒的河流,河上有一座月牙般弯弯的拱桥,桥下面便是学院的大门。点点家的小花园就紧靠在我们的院墙边上。因为我人小,所以就被人群挤到了院墙边。就在这兵荒马乱的当口,忽然看到点点的外公赤着脚,穿着件老头汗衫,从紧挨花园的一扇窗户里跳了出来。我正在奇怪,只见他纵身一蹿,一下子就攀上了矮墙,片刻也没犹豫就跳了下去!紧接着便爆起一片大呼小叫:有人跳河啦!反动学术权威跳河自杀啦!
顿时,看热闹的人和气急败坏的的造反派们潮水般涌向围墙边。有人失声呐喊,有人嘶声叫骂,还有许多人兴奋地拍着巴掌或尖利地吹着口哨,但都眼睁睁地看着点点外公像个大麻包一样,在混浊的河水里浮上沉下地挣扎,就是没有一个人跳下去救他。就在这时,又一个更让人惊骇的事情发生了——瘦小而因紧张而脸色像一张黄裱低一样难看的点点,突然不声不响地从人群中钻出来,正好挤到我身边。她的个子比我还矮半个头,却一下子攀住墙头,拼命往上蹿。我还当她只是想看看河里的外公呢,就抱住她的腿托了一把。哪知她一爬上墙,立即飞身一跃,就那么穿着一身连衣裙,像只轻盈的燕子般扎入水中!
我惊呆了。所有的人在那一刻都惊呆了,以至现场出现了一瞬间的静默。只见点点吃力地游向已向水流下方漂去的外公,一把抱住了他。我知道点点会点水,两年前我们在学院泳池一起学过游泳。可那时她顶多也就会仰着头游个十来米,又是这么瘦小的一个女孩子,还穿着裙子,怎么可能救得起外公这么大的一个人呢?果然,水里的两个人刚抱在一起没多久,很快就扑腾着沉了下去。
但是,点点的勇敢还是起了作用。不知是谁带的头,扑嗵扑嗵,十来个围观者一个接一个跳进了河里,有人还找来一架木梯伸进河里,很快就把点点祖孙俩救了上来……
我忽然觉得身上有点凉,抬头看看天,刚才还神气地浮游于亭子东南角上的太阳,不知几时已被一大团黑云吞没了。那些先前还在柳树梢上“思他、思他”地聒噪不已的知了们,不知为何也都闭上了嘴巴。亭子周围一下子显得分外寂静,静得能清晰地听见亭后那两棵高高的白杨树叶,在渐渐强劲起来的风中飒飒的呻吟。我感到心里很阴郁,还有一种莫明其妙的异样感。再看看亭子周围,竟然一个人影也没有。今天怎么啦?都快中午了,学院里的人都到哪去了呢?怎么会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呢?哦,可能又到学院后面的大操场去开什么批头会或者誓师会了吧?可是不对呵,开这样的大会,学院里的高音喇叭照例是要一遍遍地播放通知、或者造反有理等语录歌的呀?对了,好像今天还没听见喇叭响过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心里越发有些发毛。想对点点说说我的疑虑,却又怕她笑话我胆小。于是便提起我的铁桶,对点点说:我们回家吧,不然恐怕会下雨呢。点点看看天,又站起来向物理楼方向张望了好一会,终于点了点头。
走出亭子时,点点又张开双臂,向物理楼使劲挥动,并大声喊着:外公,我回家了。你当心点呵,明天我还会来看你的!
可是陈旧的物理楼上大多窗扇紧闭,一片死寂,没有任何回音;在越来越昏暗的天光里,我们也根本看不清任何一扇窗户后的秘密。
回家的路上仍然没有碰见一个人。
我越发感到奇怪,并有一种越来越浓厚的不安感,像天上的黑云般紧紧包裹着我的心。再看点点,她显然没有我这种奇怪的感觉,反而还有些兴奋,一路上都在和我说这说那。特别让她伤心的是她外婆的眼睛。因为哭得太多,有一只已经什么也看不清了,到医院去看吧,又因为是反动学术权威家属,不但没开到什么药,反而被一个医生恶声恶气地训了一通……说到这里,她嘤嘤地哭了,步履踉跄。一只手紧紧抓住我的手,簌簌地抖个不停。我很想安慰她一下,可又不知说什么才好,只好暗中叹气,并握紧她的手,牵着她暗暗加快脚步。
我们还是比灾难迟了一步。
刚刚拐出学院大门(我这才注意到,学院的门卫室居然也门户大开,鬼影也不见一个),一个锥心的叫嚣晴天霹雳般炸响:不许动,举起手来!
我们呆住了。人,一大群全副武装的民兵,有的端着步枪,别的举着冲锋枪,有的戴着钢盔,有的戴着柳条帽,刚好从学院门外的石拱桥上猫着腰小心翼翼地闯进学院来。突然看见我和点点,他们也明显吃了一惊,走在最前面的一个人紧张地盯着我手中的铁桶,一挺枪跳过来,寒光闪烁的枪刺差一点就刺中了我的鼻尖:什么东西?
我猛然醒悟,赶紧扔掉铁桶,高高地举起了双手。铁桶落地的■啷声,加上四散滚落的蜗牛,把头前几个民兵吓了一跳,他们惊恐地跳开去,同时所有的枪口都瞄准了我。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只有电影里才见识过的场面,一时魂飞魄散,只觉得天地乱旋,仿佛自己已被挑起在枪刺上凌空乱舞。我想求饶,却什么话也说不出,甚至连哭声也发不出来。与此同时,一股灼热的尿流却顺着裤管淌进了鞋里。
就在这时,啪,啪啪……耳后响起一阵凌乱的枪声——大队人马扔下我,放着枪,喊着给自己壮胆的杀声,潮水般冲进了学院。
第一阵枪声是冲着点点去的。他们以为点点是给里面报信的。事实上点点担忧的只有一个人——外公。趁着那伙人的注意力在我身上的时候,点点突然一个转身,飞快地跑回了学院,一边向着远处的物理楼尖声喊着:外公,快逃呀,有人来杀你啦……
里面的枪声越来越密,桥上下来的民兵也越来越多,像一大群形状怪异、尖刺利甲且裹挟着呛人的血腥气的大甲虫,前呼后拥、躲躲闪闪地爬进了学院。太阳恰在此时又挣出了云层,枪刺的反光辉映着惨淡的阳光,反而让眼前的一切都显得格外虚幻却又格外恐怖。我惊惧地闭紧双眼,只觉得地在摇颤,天在旋转,世界末日嘎嘎狞笑着轰然降临。我几乎都忘了呼吸,像具灵魂早已出窍的木偶,身子紧贴在门房的墙壁上,直到那股怪异的浊流完全消逝,学院里的枪声渐次停止,大地也不再战栗时,才敢放下麻木的双手。
我这才哭出声来,一边抹着汹涌的眼泪,一边趴着墙角向学院里窥探。民兵们早已散失在学院深处,眼前重又变得像我们出来前一样,空荡荡而死一般沉寂,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然而,我身边却分明少了个点点。
她就那么头朝地地趴伏在距大门口几十米远的一棵高耸入云的老银杏下。鲜艳的红头结却依然抢眼,像一只飞倦了而暂时小憩的红蝴蝶,一动不动。
我在距点点几米远的地方跪了下来。我不敢近前,也无法再近前。我泪流满面,僵挛得就像发了羊癫的病人。我满心愧疚,充满着对自己的鄙恨。为什么我没想到要护住点点,不让她乱跑?为什么我不敢拦住罪恶的枪口,反而卑怯得湿了裤子?
我嘶声呼唤着点点的名字,却再也听不到她的回答。只有老银杏那金黄的落叶,沙沙悄响着,泪雨般飘落在点点身上。
老银杏至少已有百年寿诞了,可谓阅人无数,饱经沧桑。可是它未必见识过今天这么一幕。毕竟它始终生活在文化氛围浓郁的学院里,呼吸着的、滋养它的,都是所谓的人文精神呵!
不,我宁愿相信轻抚着点点的不是老银杏的落叶,而是从她向往的星空飞来引领她的天使。而点点正在安静地羽化,羽化成一只即将翩翩飞向天国的红蝴蝶。因为仍在汩汩流溢的鲜血,眼看着就要将她那洁白的连衣裙洇化成鲜红的羽翼。
虽然我早已嗅到了某种异样和危险的气息,却绝不可能想到会是这样一种危险。此后我才从大人们口中得知,占领学院的造反派,头天已探知城外的对立派将来偷袭,连同他们控制的批斗对象一起,全部撤到了西郊。那天的学院实际上已是一座空城——如果我们早知道这些,点点也不会失控而跑了……
那年,点点和我一样,刚满十四岁。
原载《翠苑》2007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