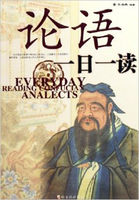赛金花是一百年前的“北京宝贝”,比当代所谓的“上海宝贝”还要先锋,还要另类。“上海宝贝”们提倡“用身体写作”,可赛金花的步子不仅迈得更早一些,而且迈得更大一些:她是用身体搞外交(抑或外贸)。可见古今的“宝贝”们异曲同工,都无师自通地掌握了行为艺术的真谛。想当年赛金花穿过刀山火海拜见攻占北京的八国联军元帅瓦德西,也充满了以酥胸抗衡列强的坚船利炮之勇气。她为联军筹措过军粮(可从粮商那儿吃点回扣),但毕竟曾经劝说敌酋不要对平民百姓施暴,效果好像还挺明显。赛金花的挺身而出,“使不可终日之居民顿解倒悬,至今犹有称道之者”。(引自1922年出版的《赛金花事略》)
将赛金花称为“北京宝贝”,是诗人刘半农的创举:“中国有两个宝贝,慈禧与赛金花。一个在朝,一个在野;一个卖国,一个丢脸。”(转引自叶祖孚著《燕都旧事》)当然,我们必须注意,他所说的“宝贝”,是带引号的。有乱世活宝的意思。
与慈禧相比,赛金花的经历更充满了乱世佳人的意味。至少,尚有可同情之处。慈禧畏洋人之锋芒,逃往西安避难去了,而作为一个烟花女子,赛金花自然只能继续留在红尘里苦苦挣扎。她和所有的北京市民一起,被惜命的太后抛弃了。她又能怎么样呢?难道必须像圣女贞德那样慷慨就义?如果非要以花木兰、穆桂英等古典女英雄的品质来比照赛金花这样的弱女子,就近乎苛求了,或者说是不太现实的。赛金花的政治觉悟不可能那么高,她在乱世里也必须混口饭吃,而自己其他的生存技能早已退化,因此只能干老本行。然而,赛金花千不该万不该把八国联军当成自己的主顾,因此沾上了永远洗刷不清的污点。毕竞,在中国的妓女阶层,也曾经出现过李香君这样的人物。《桃花扇》是血染的风采,而赛金花呢,则只配被写入《孽海花》之中。
曾朴以赛金花为模特儿著述的小说《孽海花》,将许多虚构的情节安在赛金花身上,对读者造成了误导。譬如说她随洪钧出使德国时,“浪漫放荡,天天交际,夜夜跳舞”,并且勾搭上了瓦德西,以致瓦德西后来率军侵占北京,公务之余四处査找老情人赛金花的下落,终于重续前缘。“赛金花出入禁城时,与瓦帅携手以行。或结发辫,头草帽,足缎靴,拉一白马,招摇过市。人遂以赛二爷呼之。”瞧她还着男装、穿皮靴、骑战马,与敌酋并驾齐驱,并且喜欢别人以“爷”相称,这不跟后来的川岛芳子似的吗?幸亏赛金花在战前即是一代名妓,否则人们非怀疑她是女间谍不可。
瓦德西与赛金花,都是因绯闻而遭到街谈巷议,就像百年后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与莱温斯基一样。因为绯闻的缘故,后人才记住了八国联军的统帅叫瓦德西,他的相好叫赛金花。绯闻,居然比惨痛的历史本身更有感染力。更耻辱的,是居然还有人津津有味地编造瓦、赛二人在仪鸾殿同床共枕的情节。
对赛金花这样的女性,我们为什么不能再宽容一些呢?从根本上来说,她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在天灾人祸面前,她们同样也有求生的本能。在那个非常时期,赛金花纵然千错万错,说到底仍然不过是一位铁蹄下的歌女。她替南城的商贾与平民说情,也算是尽了一己之力了。
1934年,刘半农向得意门生商鸿逵倡议写一本赛金花的传记。采取口述实录的方式,由刘亲自出面,约请赛金花在王府大街古琴专家郑颖荪的私宅访谈,由商执笔记录。这样的会晤共进行了十几次。其时赛金花已是美人迟暮,但仍操着一口吴语侬腔,将往事娓娓道来。这本署名为“刘半农初纂、商鸿達纂就”的《赛金花本事》,由北平星云堂书店出版,畅销一时。结果引得影后胡蝶也萌动了饰演赛金花之心,函请商鸿逵陪同赛金花赴上海,谈判拍摄电影之计划,却遭到婉拒。看来,知识分子的商业头脑并不是随便就可以开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