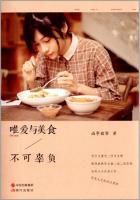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
——庄子《齐物论》
《尚书·舜典》:“诗言志。”《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即心意志向的外化而为语言,此乃抒情诗之传统。“志之所之”,可谓关键,“所之”,所到达。诗即体现着由“志”到“言”的“意向性”生成过程。然而,这“志”究竟为“个体”之志,抑或为“群体”之志,却并不明确。同时,无论其为群体的,抑或为个体的,都似乎表征着人类文明的一种主体化心态。后人领悟到最初的诗或最原始的诗,并非是“人”的独语,而是“人”与“世界”的“应和”。于是,《诗纬·含神雾》有云:“诗者,天地之心。”文中子亦云:“诗者,民之性情也。”《艺概》通而言之:“诗为天人之合。”“诗”挣脱了“主体”的自是和独大心态,指向了天地人神的感应,指向了宇宙间众语喧哗的应和酬唱。
刘勰指出:“诗者,持也,持人情性。”这同样抛弃了单纯从人类主体角度规定诗之意义的狭隘取向。“持人情性”,便标明着“内”与“外”的响应,“我”与“他”的对语。“持”,乃是某种平衡、抑制、约束,这意味着“诗”乃是“自我”情感志向的“向他”而“化”,诗是“我”的言说,却又照应着“他”的存在,从而不可让“我”的情性无限度地扰乱“他人”的“世界”,这正是《毛诗序》所谓的“发乎情,止乎礼义”。这里已隐含着诗不仅是“自律”的,亦同样是需要“他律”的。在面向他者中,诗成为指向更宏大人文境域和天地境界的超越性存在。
庄子借南郭子綦之口说:“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此亦指出了“诗”之三重境界:所谓“人籁”者,人文之音,有我之境也;所谓“地籁”者,自然之音,无我之境也;所谓“天籁”者,天人感应的和声,是我非我,非我是我之化境也。最高境界的“天籁”之“诗”超越了功利境界、自然境界、道德境界,而化出了一种天人感应的和声境界。天籁就是最本真的诗,是真情的自然流溢,是心灵与语言的动态物语。《庄子·渔父》云:“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一部《庄子》书写的就是这种法天贵真的精诚之情。
追寻“天籁”的“歌者”,中国历代不乏其人。《易经》在始源画符中歌唱出了天健坤顺、阴阳和谐的秘密。老子在“道可道,非恒道也;名可名,非恒名也”的辨析中指向了文明机制硬块化背后的非现成化的因缘。屈原在“邃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的“天问”中,表达了天人对话何以可能的困惑。庄子在从“有待”走向“无待”的路上,摒弃了文明的疆域化偏执,而呈现出万物不断向他在化去的缘域化境。如果说这些都还仅仅是在个体化的吟唱中逼近“天籁”,在追问“神圣”,那么,值得注意的是,魏晋两代,却出现了中国诗史上罕见的“群体性”的试图逼近“天籁”的那一群诗人的歌唱。
这些诗人和这些歌唱,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玄言诗人”和“玄言诗”。这些诗人的玄言诗作水平参差不齐,但在期待从传统的抒情化和主体化的文学走向新时代的宇宙化的天籁的文学方向上,却颇为一致。嵇康是这些诗人中出现较早的一个,如其《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诗人从“兰圃”、“华山”、“平皋”、“长川”的游历,指向了“我”和“物”、“心源”和“太玄”交流、对语和酬唱,并最终从“可言”引向“不可言”的“独一”之诗的追寻。嵇康可谓魏晋时代倾情于人文与自然、个体与玄道关系之吟唱的较早的诗人之一。
继其踵者,有孙楚、何劭、陆机、顾秘、陆云、张载、张协、闾丘冲、曹摅、潘尼、棘腆、刘琨、李充、郭璞、温峤、庾阐、张骏、江逌、卢谌、王胡之、郗超、曹毗、张翼、许询、王羲之、孙绰、孙放、王献之、谢安、谢万、孙统、孙嗣、郗昙、庾友、庾蕴、曹茂之、华茂、桓伟、袁峤之、王玄之、王凝之、谢道韫、王肃之、王徽之、王涣之、王彬之、王蕴之、王丰之、魏滂、谢绎、徐丰之、曹华、王彪之、王嘉、苻朗、殷仲文、刘毅、刘程之、王乔之、张野、王齐之、湛方生、王康琚等六十余人。
在绵延近两百年的玄言诗创作中,这批诗人不能说都是成功的,甚至可以说大部分是失败的。他们在诗歌创作上大多失败的原因倒不在于他们忘记了倾听“天籁”,反而在于他们太想唱出那不能“言说”的“独一”之诗,导致了“玄道”的绝对本质化和神秘化,也就失去了多元的和声。我们试看最初的一些玄言诗人的诗作,如何劭《杂诗》:
道深难可期,精微非所慕。勤思终遥夕,永言写情虑。
顾秘《答陆机诗》:
恢恢太素,万物初基。在昔哲人,观众济时。
陆云《答顾秀才诗五章》:
芒芒上玄,有物有则。厥初造命,立我艺则。
爰兹族类,有觉先识。斯文未丧,诞育明德。
闾丘冲《招隐诗》:
大道旷且夷,蹊路安足寻。
经世有险易,隐显处存心。
嗟哉严岫士,归来从所钦。
曹摅《赠王弘远诗》:
道贵无名,德尚寡欲。俗收其华,我执其朴。
这些诗的特征,正如钟嵘在《诗品》中所批评的: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左,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钟嵘的批评在论及玄言诗的特征和缺陷时,还是公正客观的。但他认为,“玄言诗”是“建安诗”精神旨趣的完全丧失,或者说是“诗”的退化与堕落,这却是未能看到“玄言诗”响应存在而超越现实的独特精神气质。
刘勰对玄言诗的批评,则是从时代学风的变化及玄言诗人对现实的逃避来论述的:
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
刘勰的批评指出从西晋以来流行的玄学逐渐影响到诗文创作,并成为东晋诗人借以逃避混乱浊世的精神鸦片。这种批评只是看到了玄言诗的消极性,而未能发现玄言诗人们创作玄言诗乃是某种有意为之、主动为之的超越性的精神指向和切身践行。
而史家的批评或更能体现后世官方对于玄言诗的主流看法,如檀道鸾《续晋阳秋》所载:
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许)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至义熙中,谢混始改。
在檀道鸾看来,《诗》、《骚》可谓中国诗之“正体”,而“玄言诗”可谓“变体”,这种“变体”的出现,导致了某种“雅正”的文学传统的消失,其罪不可谓不大。
然而,不管是檀道鸾所代表的史家,还是钟嵘、刘勰等所代表的权威的文学批评传统,都只是从《诗》、《骚》的“正体”观念来贬抑“玄言诗”,而未能看到“玄言诗”迥异于“诗骚体”的新异的诗学精神和人文特质。如果说,“诗骚体”的主流诗学精神在于言志抒情,那么“玄言诗”的主导诗学精神则在于体玄悟道。如果说,“诗骚体”的人文特质在于两极文化结构共谋下的御用化和物欲化传统,那么“玄言诗体”的人文特质则在于三极文化结构妥协中的个体化和精神化指向。
实际上,一种新的诗学精神和传统的形成和延续,必有赖于与其相适应的文化结构的形成和延续。中国主流抒情诗学传统及与其相适应的两极文化结构(皇权文化和平民文化的联盟)相对于玄言诗学传统及与其相适应的三极文化结构(皇权文化、世族文化、平民文化的鼎立)的压倒性优势,造成了玄言诗学精神和其所体现的世族文化特质被遮蔽,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一个极大的遗憾。
因此,研究玄言诗,不仅要从玄言诗生成的一般思想艺术根源入手,更应当从其所植根的三极文化结构特别是世族文化背景出发,方可能得以深入地探讨。从思想艺术的一般规律性来说,玄言诗是思想艺术自身运动的结果,体现了诗人挣脱现实羁绊,追问形上玄秘的内在冲动。从时代文化的特定背景来说,玄言诗只是在魏晋世族文化背景下才达到了其顶峰。玄言诗的形上追问与玄妙之思只有在魏晋世族空前强大的历史前提下,才能被真正激发。
长期以来,魏晋玄言诗被视为中古诗坛的一个异类,并受到诗人、学者的轻视。而在玄言诗研究方面,学界也多聚焦于寥寥可数的几个重要诗人,有关整体研究的成果亦相对匮乏。具体到时段而言,20世纪80年代前,可视为玄言诗研究的沉寂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魏晋玄言诗研究则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其艺术价值、历史地位都在经历着一个重新评价的过“诗骚体”的抒情诗学传统和“玄言诗体”的玄言诗学传统,可详见本书第七程。但相较其他诗体,玄言诗的研究仍显得远远不足。根据在权威的“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输入“玄言诗”关键词的统计,从1980年到2010年4月,相关论文总计约有544篇;又根据“中国知网·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的相关统计,以“玄言诗”为直接或相关选题的硕士论文有28篇,博士论文3篇。显然,魏晋玄言诗作为一种重要的诗歌现象和文体形式,相较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热点如《诗经》、《楚辞》、《乐府》等研究成果以数万计、数十万计的情况而言,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在海外,《诗经》、《楚辞》等研究也同样备受关注,而魏晋玄言诗研究却尚处于无人问津阶段。当然,这既与国内对魏晋玄言诗研究尚未引起充分重视有关,同时也和该领域尚缺乏极具分量的学术成果有很大关系。
魏晋玄言诗的研究是否具有价值,其历史地位如何,我们以为不能仅仅根据玄言诗盛极而衰中的流弊,或玄言诗作家轻视俗务远离现实,就轻易地贬低或否定这种文体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并由此导致对玄言诗所具有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及其带给中国文学的积极影响的漠视。值得欣慰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完全无视玄言诗历史存在的消极和片面态度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扭转,不少学者开始从具体问题、具体现象、具体作家和具体文本入手分析探讨玄言诗的义界、题材、主旨、流变、思维方式、艺术价值、创作心态、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背景。但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大多还停留于就问题论问题、就个案谈个案,大多不过走了从以前的全面否定到目前的部分肯定的套路,大多落脚于挖掘玄言诗和中国主流诗学标准吻合的修辞方式、表现方式与诗学精神,而未能看到玄言诗的独特价值恰恰就在于其不同于传统主流诗学标准的修辞表述和诗学精神。下面我们将对昔哲今贤的成果作提要式综述。因叙述是沿着某种逻辑顺序,故难免疏漏,较详细的引证可参见各章引文标注及书末的参考文献。
一、玄言诗流变史研究
较早对玄言诗流变史作出划分的,有南朝檀道鸾、刘勰、钟嵘、沈约等。檀道鸾《续晋阳秋》将玄言诗的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
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许)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至义熙中,谢混始改。
1.孕育阶段
以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扇起玄风为起点。刘勰与其观点相似,如谓“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文心雕龙·明诗》),“于时正始余风,篇体轻澹,而嵇阮应缪,并驰文路矣”(《文心雕龙·时序》),这同样是以正始年间何晏、嵇康、阮籍等宣扬玄学并以玄学思维方式创作诗歌为玄言诗孕育阶段。
2.形成阶段
以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道教贵生的游仙之辞渗入诗歌为标志。刘勰、钟嵘观点与其略异而实则相通。如刘勰谓“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文心雕龙·明诗》),钟嵘以为郭璞“创变其体”(《诗品·序》),“乖远玄宗”(《诗品·卷上》),都只不过说明了郭璞游仙诗对玄言诗流弊的革新意义而已。这里,檀道鸾侧重于郭璞与玄言诗人“会合道家之言”的一致性;刘勰侧重于郭璞“道家之言”中的“仙气”及在玄思中独抒怀抱的隽拔;钟嵘侧重于郭璞对玄言诗的“创变”,三人都并未否认郭璞写作玄言诗的事实。刘勰、钟嵘不同于檀道鸾处,在于他们指出了郭璞之前已有玄言诗的流行,檀道鸾则未说明郭璞之前是否已有玄言诗写作的事实。
3.兴盛阶段
以许询、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为旗帜。刘勰赞同此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文心雕龙·时序》)。钟嵘看法略异,“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左,微波尚传”(《诗品·序》),似乎认为玄言诗兴盛期在西晋永嘉,而东晋不过是玄言诗余波。钟氏与檀刘二人的说法似乎难以调和。但王钟陵认为:“檀道鸾之说,注目于过江以后的诗同中朝诗的区别,钟嵘之论,侧重于东晋诗与西晋诗之间的延续关系,都有道理。”王钟陵的解释应当说是可以接受的。西晋时,玄学发展至其顶峰。其时玄学名家辈出,前期有向秀、裴楷、王戎、乐广等;后期有王衍、卫玠、阮修、王澄、王敦、谢鲲、郭象等,并相应形成了王衍、乐广的虚无论、裴頠的崇有论与郭象的自生独化论。东晋玄学则无太多新创。从这方面说,东晋的确是西晋余绪。但钟嵘未曾认识到,玄学顶点虽在西晋,而玄言诗顶点却在东晋。显然,钟嵘模糊了玄学与玄言诗的关系,故其论述中难以辨清玄言诗的真实发展脉络。另外,钟嵘也未看到东晋中期佛教大小般若学说对玄学与玄言诗的革新作用。
4.衰落阶段
以义熙中“谢混始改”为尾声。刘勰亦认为,“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文心雕龙·明诗》),玄言诗在晋宋之际消隐了,代之而起的是书写山水情状的山水诗。沈约亦持此观点,“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宋书·谢灵运传论》)。显然,自东晋末年之后,一种新的诗歌书写向度诞生了,这种新的诗体中是否仍具有玄思或玄言的尾巴,姑且不论,但可以确定的是,作为以老、庄为旨归的玄言诗书写已不再是诗歌的主流。
自南朝齐梁之后,玄言诗的历史研究沉寂了一千余年。这其中或略有注视玄言诗者,如宋以后人重视其理趣、理语、理境,近人刘师培、朱自清、陈寅恪、马一浮、钱鍾书等学人对此亦都有所关注,但未曾对玄言诗作宏观的历史透视。其中唯王瑶先生写于共和国成立前的《玄言·山水·田园》一文,对玄言诗作了一个整体的历史观照。从总体上说来,王瑶仍主要是承袭檀道鸾说,但又别有胜解,且对刘勰、沈约等南朝诗论家之说法多有纠正。王瑶认为,郭璞对玄言诗表现手法创新有特殊贡献,并指出,历史上将玄言诗与山水诗严重对立的做法是不确切的。游仙、玄理、山水都只是玄言诗题材的变化,而不是主题的变化。这种从题材入手,而不是从简单的观念入手的研究方法,应该说是深刻而有创见的。
但遗憾的是,自共和国成立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研究因受意识形态制约,对玄言诗的评价基本上是否定性的,这样对玄言诗源起、兴盛、消退的历史,便很少有深入的探讨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批研究玄言诗历史演变的单篇论文或专著相继涌现。王钟陵《玄言诗研究》,陈顺智、张俊《东晋玄言诗发展述略——东晋玄言诗研究之一》等都是该时期论述玄言诗史的重要单篇论文。这些学者也多承继南朝檀道鸾以郭璞为玄言诗正式起点说,但一般都将玄言诗酝酿期追溯到东汉末期,这其中以王钟陵、龚斌为代表。不同的是,王钟陵仅视郭璞为玄言诗正式起点,许询、孙绰之时为玄言诗的鼎盛时期,谢混之时则为玄言诗阶段终点。龚斌则将玄言诗史分为三个时期:魏正始至西晋永嘉为形成期;东晋建武至义熙中为兴盛期;晋安帝义熙中为消退期。陈道贵对玄言诗风兴盛衰歇原因的考察是从文化视角切入,他认为门阀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影响是导致玄言诗兴衰的重要原因。这应当说是看到了玄言诗兴衰的复杂原因,然而缺乏对这种政治和文化结构的深入辨析。陈顺智《东晋玄言诗派研究》是近年来研究玄言诗的第一部专著。陈氏继承了80年代以来研究玄言诗的新成果,对玄言诗的历史演变作了更深入详尽的阐述。陈氏将玄言诗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东晋以前的玄言诗流演期;两晋之际与东晋前期;东晋中期;东晋后期。这种划分较为细致,但对其间的脉络缺少深入论述。
总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学术界已打破了历史上玄言诗史研究的沉寂状态,并获得丰硕成果。但不可否认,当代玄言诗史研究除将起源追溯到更早,并作出明确分期外,实际上还有诸多问题未能得到合理解释,其中如玄言诗与“三玄”(《周易》、《老子》、《庄子》)的关系,玄学对玄言诗的影响,玄言诗异于传统诗歌的思维方式变化,玄言诗在东晋以后的传播状况等,都是有待玄言诗史研究者作出考证与阐述的。
二、玄言诗文本研究
研究一种文学现象,必先从文本出发,在文本中揭示此种文学现象的义界、题材、主旨、风格、价值。只有深入作品内部,才能揭示作者的生存状态、社会时代背景及作品传播状况。在绵延一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玄言诗文本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由于受传统诗学观念的影响,难免体现出一定的局限性。
在概念界定上,南朝诗论家认为玄言诗是“寄言上德,托意玄珠”(《宋书·谢灵运传论》)、“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文心雕龙·时序》)的产物,对玄言诗的题材、主旨、风格都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们认为,玄言诗是魏晋诗人逃避现实的消极产物,其题材局限于老庄或佛教典故,殊少对现实的关注,其主旨不过是诠释老庄之意,而未能发挥儒家诗学讽谏的功能,其风格是平淡寡味,亦缺少传统诗篇强烈情感化的色彩。当代学者仍旧沿袭玄言诗是阐述老庄思想的旧说,从而只能将玄言诗看作和山水诗、田园诗并列的诗体类型,如王瑶《玄言·山水·田园》认为游仙、玄谈、山水都只是题材的变化。这种说法的不足在于仅仅将“玄”(玄言、玄思、玄道)看作题材,未能意识到玄言诗代表了一种完全新异的思维方式——“玄”(体道悟玄),而不同于传统以抒情诗体为主导的思维方式——“情”(抒情言志)。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不会仅仅把玄言诗视作阐述老庄思想的诗歌,而是会认识到即使《周易》、《老子》、《庄子》、《楚辞》中都有着大量可归属玄言甚至玄言诗的文字或诗歌,老、庄只不过是“玄”、“玄言”或“玄诗”之一种。
在思维方式的探讨上,即使有部分学者认识到应当从“玄”的思维方式上来界定,但不少人却简单地将“玄”等同于“理性思维”或“逻辑思维”,而以其与情感思维对峙,如周寅宾即以“逻辑思维”来概括玄言诗的思维方法。这种观点已遭到学者的反驳,如黄新亮《不能用“逻辑思维写的”笼括东晋玄言诗的特征》提出不能简单地将“玄”等同于逻辑思维,也不能将其与情感思维对峙。但这种“玄”的思维方式的独特性何在,却仍缺乏清晰的说明。“以理释情,以性统情”的说法都太过笼统。实际上,玄言诗的“玄”的思维方式既有对易学通感思维方式的继承,也有对文学哲学化时代的逻辑思辨理性的汲取,而这两者的结合才构成了“玄”的思维方式的本质,对这种“玄思维”或“玄学思维”的研究无疑将弥补这方面的空白。
但何谓玄学思维?20世纪末以来,学者在突破对玄言诗“玄学思维方式”的笼统概括中,逐步否定了玄言诗是对哲学思维方式“辨名析理”与“立象尽意”进行简单移植的看法,而发掘出玄言诗的独特思维方式——“理感”。钱志熙认为,东晋玄言诗的独特思维方式是“理感”,即“以感性的方式去体悟理性的内容,创造出特殊的象与理游的诗境”。钱钢、伍晓蔓等承此观点,进一步强调“理感”是玄言诗特殊的融合理性与情感的创作思维方式。“理感”说的提出,已不再囿于传统思维方法的论争,从而对玄言诗思维方式的深入研究有开创之功。这种“理感”既不同于传统的感性抒情,也迥异于西方的纯粹理性思辨,无疑具有其独特的价值。然而,“理感”说仍旧有模糊笼统之嫌,难以实现一种现代转换。
因为文本研究中存在的种种局限,玄言诗便仅仅被放到一个小时段来研究,如陈顺智《东晋玄言诗派研究》,就仅将玄言诗看作一个时代的文学,而未能从大视角、大历史中看到“非玄言诗体”的发达和“玄言诗体”的备受压抑实际揭示了中国社会文化和文学艺术务“实”不务“玄”的实用化道路,因而也相应地未能看到玄言诗在魏晋的繁盛表现了一种中国文化备受压抑的精神气质——玄学思维在魏晋时代的盛行——实际隐藏着基础性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历史,当然更未能看到这种变迁不能摆脱传统务实文化的影响而完全走哲学化的道路,因而在畸变中形成了一种既务“虚玄”又不摒弃“情感”的玄学思维方式。
总的说来,20世纪末叶前,玄言诗文本研究既难走出历史上“现实主义”的牢笼,也难突破传统“抒情诗学”的束缚。什么是玄言诗?玄言诗选用哪些题材?玄言诗的主旨何在?学界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百花齐放,但实际却大多是沿袭南朝诗学中已有的定论,或略加修补。其中略可称道的贡献或许在于某些学者已不同程度地突破了1949年至80年代中期笼罩在文学研究中的唯现实论与唯政治论的意识形态标准,有一种不自觉的怀疑与批判精神。实际上,不仅要摧毁近现代以来的政治化与功利化的研究尺度,而且更应当打破中国传统诗论中抒情诗一统天下的局面,这才可能是玄言诗阐释学的新方向。
三、玄言诗作者研究
魏晋玄言诗作者历来便遭到了诗论家的否定与批评,其原因不外乎传统抒情诗学与儒家讽谏诗学的囿限。如南朝檀道鸾、钟嵘、刘勰等都对玄言诗及其作家评价偏低。他们所列举的主要玄言诗作者如王济、杜预、刘琰、王蒙、许询、孙绰、桓温、庾亮等,都被视为“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代表。至于沾染玄风的嵇康、阮籍、郭璞、刘琨等因能写胸中之情、抒不平之气、存耿介之志,故受到较高评价。源于这种诗学观念,他们有关玄言诗作者的研究只能是零碎而难成系统的。相比之下,《世说新语》作为魏晋文化艺术精神的产物,则在奇闻趣事、谈吐风神中更多地显露出玄言诗作者的心态及创作风貌。故在研究中,以此类重要文献为切入口,或可突破南朝诗论家们的传统偏见。
当代玄言诗研究又因为不能从全新的思维方式、社会文化结构出发探讨,故而在玄言诗作者研究上,大多只能说某些诗人有某些思想而非完全是消极的,从而未能把玄言诗作者群落看成一个重要的阶层力量;还未能在玄言诗读者群落的研究上,认识到玄言诗读者在魏晋以后消失是源自传统两极文化封闭结构的恢复,从而导致玄言诗接受的市场或大众环境的消失;更未能认识到玄言诗所代表的是一种全新的诗学精神,是不同于传统抒情诗学,但又汲取了抒情诗学的某些因素,借鉴了异域佛教诗学,发展了一种新的体道式经验而形成的玄言诗学。因此,这种盲视和贫乏成为中国传统诗学在向现代诗学转型中始终缺乏创造力的深层原因之一。
目前,对于玄言诗作者的研究,当有五个方面值得重视:一是作者生平名号的考辨。主要从社会与历史的角度解读魏晋玄言诗人的性格及文风成因,对我们弄清魏晋玄言诗人与社会政治的关系问题有颇多启示,但仍缺乏对作者心理人格、遭际命运的立体性把握,故略嫌不足。二是作者思想背景研究。主要论述了魏晋玄学、佛学、儒学对魏晋作者的影响及其间的互动关系。三是作者人格心理研究。作者人格心理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人本主义心理学传入中国后出现的一个研究热点。这对于分析魏晋诗人的人格心理成因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诗人审美趣味的变迁,当有一定积极意义。四是魏晋玄言诗作家的生命观与命运主题研究。钱志熙以为中国古典文学表现生命主题的传统在唐代之前已经奠定,并深入分析了魏晋人的生命情结及其对文学的影响。还有论者指出魏晋玄学的命运观与六朝文士咏叹命运的文学主题切近,对传统的反叛及对未来命运的昭示、生命悲剧及其内涵意蕴在命运选择中的文学写作,亦殊可注意。五是魏晋玄言诗人的诗文集会研究。诗人聚集为一个团体写作各类诗文,表达相似的观念趣尚及艺术精神,历来是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魏晋后,文人集会渐成一种时尚和潮流。该方面的成果对我们继续研究魏晋诗人亦多有启迪。
总体说来,有关魏晋玄言诗作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作者的创作心态、人格特征及其与创作的关系上,而对作者的身世背景及其在特定的世族文化语境中的身份差别的研究尚嫌不足。且在玄言诗作者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方面也远远不够。笔者认为,魏晋玄言诗作者研究方面,尚有几个问题应当解决:魏晋玄言诗作者何以背离抒情诗传统而写作玄言诗?他们希望在玄言诗中投入何种情绪并解决何种问题?他们的创作心态与精神气质如何?要回答这些问题,就不得不深入玄言诗作者的生存状态,研究其生活背景,了解其思想变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到“同情地理解”和历史地批判。
四、玄言诗世界研究
诗人是时代精神的产儿,诗歌是诗人对所处时代的吟唱。这个时代就是诗人的生活世界,包括宗教世界、道德世界、世俗世界、人生世界等多重内涵。近年来,对玄言诗描写的世界或时代背景,主要集中于宗教世界特别是玄言诗与佛教关系之探讨,而对与其关系密切的道德世界、人生世界、世俗世界的探讨则相对不足。
先看宗教世界。刘师培、汤用彤等前辈学者都指出了东晋时期佛教深入中国本土文化,并成为诗人重要思想源泉的时代背景。近年来,相关研究不断深入。张伯伟、陈允吉、齐文榜、龚斌等探讨了佛教发展与玄言诗演变之间的内在关系,从不同文化的异质存在中,看到了义解僧和译经僧引佛理入文学,以文学表现佛,从而促进玄言诗发展和血液更新的作用,指出了当时“佛学与玄学”、“佛理诗与玄言诗”之间的浸润互融现象,对玄言诗产生的有利时机和条件等客观情势,作了切实可信的说明。
在道德世界方面,不少论著都探讨了汉末魏晋时期道德伦理的变迁,但在将道德变迁与玄言诗进行内在结合研究方面,却远远不够。罗宗强、李建中、许建良等从道德风尚与士人心态变迁角度,阐明了玄学生成的历史因缘,论述了正始名士、竹林七贤人格断裂的内在原因,并以此深入探析玄言诗兴起的缘由。这些研究成果对玄言诗研究中道德视角的开启,无疑具有重要意义。问题在于如何将道德研究与诗学研究结合起来。
在人生世界方面,专题研究不多,但大多数涉及玄言诗的论著却往往不可避免地涉及该问题。钱志熙对玄言诗促进文学的境界化发展方面也有精辟论断,其对玄言诗中的生命意识及山水境界的体认,极为深刻。杨仁立论述了玄言诗人生世界中人与自然的亲和。伍晓蔓在论述玄言诗的诗学生成机制中,对诗人心灵境界的发掘也殊可注意。
在世俗世界方面,因与民俗、经济、政治、制度等关系密切,涉及面较广,故可开拓空间极大。严杰从文学与节日民俗关系角度考察玄言诗的进程。徐国荣从主体创作心态发掘玄言诗潜藏的世俗情绪,认为玄言诗是一种“雅化的世俗”。王守雪从社会历史中的一个特殊细胞——“家族”角度研究家族诗人群体活动对东晋南朝诗学的作用和意义。罗宗强在论述受玄学影响的东晋作家陶渊明时指出,陶渊明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世俗情结的纠缠,而走向了物我泯一的人生境界。他认为陶渊明远离世俗的动力主要来自儒家固穷思想、佛家般若性空说及庄老玄学委运任化的人生态度。陈道贵从“政治”与“文化”的双重视角审视玄言诗,已挣脱了近代简单的社会经济决定论模式,但对于“政治”、“文化”和“玄言诗”变迁的内在关系,尚未能作出深入探讨。张可礼以为,东晋玄言诗的盛行与衰退都与门阀士族文艺世家有割不断的牵连。洪伟认为,东晋玄言诗是玄学政治意识影响的结果,优越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地位,让门阀士人的精神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和超越,由此其诗中充溢着一种乐观主义的精神。
应当指出,在玄言诗世界研究中,玄言诗受佛教浸润的宗教背景及受玄学影响的学术背景,已多为学者所注意,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玄言诗和本土宗教道教的关系问题则尚需注意。玄言诗的道德世界、世俗世界、人生世界研究无疑将是大有可为的学术园地。特别是从玄言诗的消长中阐明东晋世族文化的实质及其独特性,则尚是一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因为该方面研究的欠缺,导致学者们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的分析仍是简单的二元论式的,即将中国社会仅仅看作地主—农民、统治者—被统治者的两大阶级,而未能看到中国社会文化的结构并非如此静态地恒定,而是在魏晋时期也曾经发生过某种激剧的内在裂变,即形成了不同于传统两极文化结构(皇家—平民)的新型三级文化结构(皇家—世族—平民),正是这种三极文化结构中的新的世族文化力量构成了魏晋玄言诗繁荣的肥沃土壤。传统学者因为未能看到三极文化结构的重要性,仍旧把世族归属于统治—被统治的二元关系的前者,于是就忽略了世族文化的革新意义,从而不能看到皇家—平民的两极文化结构实际形成的封闭联盟关系,也不能看到这两极文化结构在第三极世族文化的消解下走向离散从而引发的社会解放、思想革新和文学嬗替。
五、玄言诗历史地位及与他种诗体关系研究
因为学者们没有看到玄言诗的“玄学思维”代表着一种变革性文化力量和社会力量,也未能看到玄言诗的独特的“诗学精神”和“人文特质”,这导致了对玄言诗的历史地位和他种诗体关系的定位不够准确。实际上,玄言诗历史地位如何,是关系到中国诗学话语体系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中国诗学话语是植根于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的,因而要重新评价玄言诗的历史地位,便必须突破传统诗学话语及文化语境的局限,而这正是新时代文学研究者的重要使命所在。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玄言诗历史地位的肯定性评价逐渐增多。章培恒首次对把“现实主义”作为评价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最高标准的做法提出了质疑。他没有专门论述玄言诗,但将“个人价值”的发掘及“文学与哲理”的结合作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一个总体倾向,无疑具有独到的眼光。王钟陵认为,评价玄言诗主要应着眼于其情感消释功能所开启的自然声色描写,玄言诗中也有一定数量的好作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玄言诗阶段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成为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环节。祝振玉认为,“玄言诗的流行不是中国诗歌发展的危机,而是向成熟转变的契机”,这不仅看到了玄言诗自身具有的审美价值及寄寓的理想精神人格,而且特别指出玄言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开始由“歌食歌事”向“写意寓理”的过渡。
玄言诗的历史地位问题又是与其他诸种诗体在比较中相对而言的。这也是我们评价玄言诗历史地位的一个重要切入口。从历史的宏观层面而言,玄言诗并非孤立的诗型,而是与他种诗体密切关联的。一方面,玄言诗既迥异于传统的《诗经》体、《楚辞》体、《乐府》体等诗型,也不同于与其时代接近的游仙诗、山水诗、田园诗、宫体诗。檀道鸾所谓“玄言诗体”出,而“《诗》《骚》之体尽”,就指出了玄言诗是不同于“兴观群怨”的《诗经》体与“发愤抒情”的《楚辞》体而侧重“玄理感悟”的新兴诗型。刘勰认为,郭璞“游仙诗”与“玄言诗”有别,如谓“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又认为“山水诗”是对“玄言诗”的革新,即所谓“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对于玄言诗偏离“《诗》《骚》之体”的倾向,刘勰从正统观点出发,持极不满意的态度。
另一方面,玄言诗与他种诗体在相异中又有着某种内在的互依性。如王瑶便在承认玄言诗与“《诗》《骚》之体”不同的基础上,又指出玄言诗与游仙诗、山水诗、田园诗的内在关系。在王瑶看来,玄言诗与游仙诗、山水诗既有差异,也有承传。如玄言诗和游仙诗只是题材不同,而非主旨不同。玄言诗中也有山水,并不与山水诗截然对立,初期山水诗也只是玄言诗的延续。另外,田园诗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玄言诗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玄言诗与山水诗关系研究逐渐成为热点,主流倾向是肯定玄言诗与山水诗的承续关系。但也有学者指出,山水诗并非脱胎于玄言诗,认为其兴起与道教有密切关系。另外,陈允吉认为玄言诗与佛教常用诗体“佛偈”有重要关系。这些对玄言诗与他种诗体关系的进一步探讨都具有启发意义。
从玄言诗研究史的回顾中不难发现,近年来掀起的魏晋玄言诗研究热潮是对其被冷落一千余年状况的反拨。学者们在对玄言诗的重新评价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作家、作品、世界、读者构成的文学四重整体的有机关联中,玄言诗的相关问题都得到了不断的拓展。但应注意的是,自南朝迄当代的玄言诗研究在总体上仍旧局限在传统抒情诗学观的视野内,对玄言诗的历史评价仍难有重大突破。引入新的研究方法与新的诗学观念,将是推进玄言诗研究的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