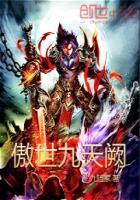栾栋先生指出:“20世纪以来西方寻求哲学的文史化、诗意化,但是中国需要而且必须进行文史的思想化、哲学化,二者在许多方面都可以择优而学,取长补短,在未来的国际化人文大潮中殊途同归而各呈异彩。”如果以这种世界眼光与历史眼光去重读古典,我们应当对魏晋玄言诗会归“诗”与“思”的努力作出全新评价。因而,我们有必要走出传统的阅读期待视野,让自己成为具有新思维、新眼光的新读者。
欲走出传统阅读期待视野,便有必要走出传统文化的束缚。中国传统文化因为源于宗法血缘制与小农经济基础的强大平民社会传统,以及在两极社会结构中形成的政治文艺的教化之偏,促成了中华民族自秦汉特别是唐宋以后,逐渐蜕变成一个重情感化之“诗”而轻哲理性之“思”的民族。
但是,“诗”、“思”从来都是一体两面的。“诗”如果不倾听来自“思”的召唤,就只能流于性情的浅层次吟咏;“思”如果不渡入“诗”的疆域,就将会蜕变为现成的言说。
中西方两千多年来“诗”与“思”同源而分流的历史,正说明了“诗”如何在沉沦,“思”如何在隐遁。
西方重“思”,也锁闭了“思”的“诗性”维度,“思”成为存在者的言说,存在同样被遗忘。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在20世纪以来,不断展开对“思”的批判,而回归着“思的诗化”。中国文化重“诗”,却导致“诗”的“思”之维度被遮蔽,生命存在的本源基础遂被遗忘。中国魏晋时代,也曾有那么一群诗人深入了“诗”的本质,而回归着“诗的思化”。
遗憾的是,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对“思”与“诗”殊途同归的体认,却大大滞后了。在西学大潮的冲击下,有识之士急急忙忙地引入欧洲古典的哲思,期望借此走上救亡图存的道路。殊不知,西方已走过了古典,走过了现代,进入了后现代。“后现代”并不是一个时代的称谓,更不是一个时髦的标签,而是意味着西方正在拯救“诗”,在实现着“思”向“诗”的转渡,正在通向一条哲学“文史化”、“诗意化”的未来道路。
然而,在20世纪的中国,“诗”与“思”却断为两截。钻研哲学的人看不起文学,认为文学不过是吟风弄月的虚矫,并自以为得风气之先。钻研文学的人又看不起哲学,认为哲学不过是教条化的空谈,并自以为集天地灵气。沉醉于中国诗歌领域的学者,时而也为西方哲学的“诗化”而窃喜于心,认为未来艺术是属于诗的,于是便自以为是地宣布中国在这方面早就领先了。但这种看法某种程度上只能说是自作多情,因为中国与西方将要走的仍是一条相通而又有差异性的道路。相通处在于中西方都要完成“诗”与“思”的会归,这方面西方是领先了;差异处在于,西方走的是“思的诗化”,中国要走的却是“诗的思化”。这就是栾栋先生说的“文史的思想化、哲学化”。
出于未来而重读古典,重读古典是为着走向未来。正是在“诗”与“思”会归的前提下,魏晋玄言诗应当被重新解读。这种解读就不再流于诗的独语,而必将建基于“诗”与“思”的复调交响。传统阅读期待视野下的读者,因为执著于“《诗经》”、“《楚辞》”、“乐府”体等“诗的独白”,显然已难以完成此项使命。当然,这里说的“诗的独白”是指读者将古典诗歌作品经验视为一种权威一元话语,实际上,这些经典作品并不仅仅是“诗”的独白,它在某些层面回响着“思”的召唤。《诗经》体、乐府体诗在这方面相对较弱,因为它们的“思”之本源更大程度上被现实层次上的歌吟遮蔽;《楚辞》体在这方面相对较强,因为《楚辞》体诗篇虽然仍多出于现实情感的抒发,但却更多地沉入个体的生命体验。但无疑,在古典作品中,唯有玄言诗在认真地实践着“诗”向“思”的转渡,在仔细地倾听着“思”的召唤。在转渡中,虽不免有摸着石头过河的忐忑,有着试验期的不成熟,但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当然也是一条艰难的不被传统读者所理解的道路。
新的古典文学读者,新的玄言诗读者,既不再是固执于“诗”之独语的传统读者,也不会是盲从于欧洲古典时代“思”之霸权的近代读者。新的读者是革命性的伟大的读者,他们将能理解生命的本源意义,也必将发掘世界的存在奥秘。生命的本源、世界的奥秘虽永难穷尽,但这些未来读者必将走上这样一条正确的道路。当然有关个体的喜怒哀乐、荣辱沉浮,有关社会的民生疾苦、美丑善恶,仍旧是诗的重要内容,也将会被新的读者解读,但这些内容却不再是诗的本质。重读玄言诗,就正是重新理解“诗”与“思”对话的秘密。
总之,因魏晋玄言诗读者群居相切磋之故,关涉言、文与道、意关系的问题遂得以深入探讨。立言尽意、微言尽意、言不尽意、山水以形媚道、以玄对山水、澄怀观道等文哲交叉、诗思磨合的深层理论亦得到广泛发挥。弱于哲思的汉民族在思想自由的魏晋时代又实现了一次理论的高度升华。这一切都应当说与世族文化兴盛造成的玄言诗读者群有极大关系。正是大批读者对理论思维的高度激赏,方才造成了魏晋文学理论的长足进步。南北朝文学理论的繁荣亦正是魏晋玄风浸润、玄思沉淀后结下的硕果。我们认为,没有世族文化酝酿出的大批擅长玄思、玄谈的名士型作者与读者,就没有魏晋玄学、玄言诗的高度繁荣。没有玄学、玄言诗的繁荣,也就没有后来或体大思精,或思致绵密的文学理论的真正成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必要进入下一步,去探讨促成了南北朝文学理论繁荣的魏晋玄言诗学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