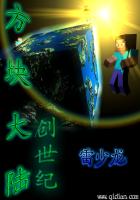夜已经深了,喧腾了一天的绵竹城内慢慢地平静了下来。那些尽情欢闹吃喝的兵士,大都折腾乏了,喝得酩酊大醉了,呼呼大睡起来。只有肉昧和酒气尚未散尽,仍在城中飘荡。整座绵竹城,就仿佛一个喝醉了的巨人,迷迷糊糊地倒在鹿头山下,躺在绵水之滨……
卫瓘从县衙的大堂回到驿馆时,已经是二更多天了。尽管他在庆功宴上并没有饮多少酒,更谈不上醉,但他却觉得胸中在剧烈地翻腾着,搅得他坐卧不安,根本无法入睡,只好在房中缓慢地踱起步来。随着沉闷滞重的脚步声,邓艾那得意甚至有些狂妄的模样,一次又一次地浮现在他的眼前;邓艾那饱含着牢骚和怨气的话语,一遍又一遍地回响在他的耳畔。这些都引起了他的猜疑和忧虑,同时也驱赶走他的睡意。
在卫瓘的印象中,邓艾是个不苟言笑、谈吐谨慎的人。可今日的邓艾为何与过去判若两人,变得如此张狂放肆、出言不逊?是他居功自傲,还是酒后失态?他所说的怨恨之语仅仅是为了发发牢骚,还是他悖逆不轨之心的真实显露?这一连串的疑问,像走马灯似的轮番出现在卫瓘的脑海,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他身为军司,虽然不便对邓艾的言行横加干涉,但却有权把邓艾的言行密报于司马昭。然而,如今的邓艾已是今非昔比,不仅功勋盖世,声誉鹊起,而且位列“三公”,威震朝野;如果他的密报泄漏出去,惹恼了邓艾,或司马昭念邓艾大功在身不予理睬,他都将自陷于危险的境地。可是,对邓艾的这些言行如果视若不见,听若不闻,隐而不报,要是邓艾真的闹出些什么事情来,司马昭轻则要指责他失职无用,重则要把他打成邓艾的同伙……
卫瓘正在为是否把今日邓艾在庆功宴上的言行密报于司马昭而犹豫苦恼着,亲兵进来禀报:“胡烈将军说是有紧要之事,请求见军司。”
“胡烈求见?”卫瓘自语了一句,思忖了一下,已经猜出了胡烈的来意,吩咐亲兵,“请胡将军到此相见。”
这座驿馆分为前后两院,卫瓘与他的亲兵住在后院,胡烈与他的亲兵住在前院,二人相距仅有数十步。工夫不大,胡烈便被请到了卫瓘的居室。卫瓘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轻声地问:“夜已深矣,胡将军为何尚未歇息?”
胡烈也故作轻松地反问:“卫军司不是也没有歇息乎?末将岂敢先睡?”
卫瓘打量着胡烈,又问:“胡将军深夜来此,有何紧要之事需告我?”
胡烈偷瞧了卫瓘一眼,掩饰地说:“末将明日一早就要返回涪城,特先来向卫军司辞行。”
“深更半夜,前来辞行?”卫瓘摇了摇头,一针见血地说。“此处乃深宅大院,隔墙无耳;我之亲兵,皆心腹之人,守口如瓶。胡将军不必多虑,有话直说无妨。”
胡烈迟疑了一下,吞吞吐吐地说:“末将乃一介武夫,不谙政事,因有一事不明,难以安卧,故而不得不深夜前来打扰卫军司。请卫军司多加指教!”
卫瓘明知胡烈的心事,但却偏不点破,而是旁敲侧击地说:“胡将军一向快人快语,为人称道。今日为何却一反常态。变得如此不爽快。”
“其实,末将所不明之事,与卫军司所忧虑之事,乃同一事耳。”胡烈不愿再继续和卫瓘捉迷藏了,便打开窗户说亮话,“末将冒昧请教卫军司,邓太尉今日庆功宴上之言行,是酒醉失态,还是酒后吐真言,醉后露真相?”
“我亦为此事而迷惑不解。”卫瓘不置可否地说,“以胡将军之见,此事当属于何者?”
“末将以为二者皆有可能,难以断定当属于何者。”胡烈恳切地说,“故而,末将才在深夜前来打扰卫司军,聆听卫司军之教诲!”
“我亦为无法断定此事当属于何者而坐卧不安。”卫瓘紧皱着眉头说,“胡将军此来,当助我判明此事,以便见机而行。”
“唉——”胡烈叹了口气,为难地说:“末将愚钝,实在无能为力?若羊参军在此,或许可助卫军司一臂之力。”
“唉——”卫瓘也叹了口气,烦恼地说:“我奉相国之命,持节监伐蜀诸军事,凡重大之事,均应报于相国得知。可此事真假难分,是非不辨,叫我如何是好?我若不报知相国,万一此事属于后者,岂不误了军国大事?我若报知相国,要是此事属于前者,岂不成了诽谤功臣?以胡将军之见,此事当报于相国还是不当报于相国?”
“这……”胡烈犹豫了好大一阵子才说,“相国善分真假,明辨是非。以末将之见,卫军司应该将此事报知相国,由相国去判断。”
卫瓘早就在等着胡烈的这句话,忙顺水推舟地说:“胡将军言之有理。我就依汝之言,将此事报于相国。不过……”卫瓘沉吟了一下,又说,“此事甚为重要,我一人之言恐不足为据;而耳闻目睹此事者,除陇右军诸将与蜀国旧臣之外,惟有我二人耳。请胡将军也能致书相国,以证实此事确凿无误。不知胡将军愿为否?”
“卫军司之命,末将岂敢不从。只是……”胡烈婉言推脱道,“末将官职卑微,若越过镇西将军直接上书于相国,恐有些不便……”
“无妨,无妨。相国礼贤下士,胡将军之书信更易于引起相国之重视。”卫瓘严肃地说,“此事干系重大,望胡将军切莫再推辞!”
“……”胡烈欲言又止,偷觑一下卫瓘的脸色,违心地说:“末将从命便是!”
“我还有一事,亦请胡将军相助。”卫瓘凑到胡烈身边,神秘地说,“邓太尉乃精细之人,酒醒以后,必为庆功宴上之言行追悔不已。我如果在近日内遣使前往洛阳,定会引起邓太尉之疑心。倘若其派人于中途截获此书信,则后患无穷!故而,我欲将随汝来此之亲兵留下两名,而将我之两名亲兵装扮成汝之亲兵,随汝一同离开绵竹。只要我之信使过了涪城,邓太尉便鞭长莫及矣!”
胡烈闻听此言,惊奇地瞅着卫瓘,将信将疑地说:“卫军司是否有些过虑……”
“此乃有备无患也!”卫瓘狡黠地说。
“末将遵命!”胡烈无奈地说。
当邓艾与陇右之军将士在绵竹城中开怀痛饮之际,师纂却在成都的益州刺史府的大堂上喝着闷酒。他独自坐在堂上,面对着满案丰盛的佳肴,自斟自饮,边喝着酒还边长吁短叹,似乎有满腹的心事。
陇右之军进入了成都以后,邓艾便以师纂领益州刺史,协助他处理一些日常公务。在陇右之军所有的将领之中,师纂成了最受邓艾重用的人。然而,师纂虽在打仗时能冲能杀,不失为一员英勇善斗的战将,可因其性情比较急躁,且又缺乏办理政事的经验,所以在处理公务时往往是捉襟见肘,有时甚至对邓艾不仅无所帮助,反而接二连三地捅出了一些漏子,添了不少麻烦。这不能不令邓艾大失所望,只好事无巨细都亲自去处理,而把师纂抛在了一边。为此,引起了师纂的忧虑和不满,以为邓艾目中无人,独断专行。此次邓艾率军重返绵竹,去庆功犒军,邓忠、王颀、牵弘、杨欣等陇右诸将皆随军前往,甚至连降将马邈和一些蜀国的旧臣也都一同前去,但邓艾却命师纂率领本部兵马留守成都。尽管邓艾如此安排是因为师纂是益州刺史,留守成都是其职责,并非厚此薄彼,别有用心。可却引起了师纂的猜疑和怨恨,认为邓艾是故意冷落他,让他难堪。这一连串的事情凑到了一块,使师纂产生出满腹的牢骚和心事,只好长吁短叹,借酒浇愁。
师纂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闷酒,不知不觉中已经到了微醺的程度。就在这时,他忽听到有人轻声地说:“刺史大人真是好口福、好自在!”
师纂吃了一惊,抬头一看,见田续不知何时溜到了大堂之上,正怪模怪样地瞧着他。
田续在江油关时因违犯了军规,被邓艾打了二十脊杖,并削去了其兵权,把他统领的兵马交给师纂率领。从那以后,田续就成了一个既无职也无权的闲散将军。到了成都以后,邓艾也没有再重新起用他;这次大军重返绵竹去庆功犒军,邓艾也没让田续一同前往。对此,田续虽表面上不声不吭,每天在成都满城乱逛,可心里却对邓艾恨之入骨,每天都在挖空心思地寻找着报复邓艾的办法。
师纂苦笑了一下,向田续招招手,瓮声瓮气地说:“田将军不妨也来与我共饮几杯,以消愁解闷。”
“多谢刺史大人还没有忘记往日之情分,续不胜感激!”田续正巴不得如此,连忙在师纂下首坐了下来,斟上了一杯酒,双手捧到了师纂的面前,阴阳怪气地说,“刺史大人福星高照,官运亨通,请饮了此杯酒。愿刺史大人青云直上,不断升官晋爵!”
师纂把那杯酒一饮而尽,心事重重地说:“我等同军为将多年,同生死共患难,汝何必开口刺史”闭口刺史“倒显得十分生疏。”
“此一时彼一时也。”田续哀叹了一声,自斟自饮了一杯,悲伤地说,“我与刺史虽曾同军为将,患难与共,但如今却有天瓘之别……”
“我这个刺史是有名无实!”师纂闷闷不乐地说,“邓太尉大权独揽,事必躬亲,使我这个益州刺史形同虚设,无事可做,在其位而难谋其政!”
“如此岂不更好!倒落个逍遥自在,何乐而不为?”田续偷偷地打量着师纂,投石问路地说,“只有一事我百思而不得其解:若论官职,刺史在成都仅次于邓太尉与卫军司,而高于其余诸将;若论功劳,绵竹之战能大获全胜,与刺史拼死而战密不可分,首功非刺史莫属,其余诸将望尘莫及。然而奇怪者是:此次全军重返绵竹庆功犒军,官低功小之诸将,甚至连降将马邈,均一同前往,而刺史这位官高功大者却不得前去,着实令人深感遗憾与困惑!”
田续的话正好捅到了师纂的疼处,揭了他的伤疤。他像吃了苦瓜似的,咧了咧嘴,忿忿不平地说:“我生性耿直,不善阿谀奉承,故而难得邓太尉之宠信,此等风光荣耀之事,当然也就与我无缘。”
“噢——原来如此!”田续装出恍然大悟的样子,连连点头,再次给师纂的杯中斟满了酒,半劝慰半挑拨地说,“武皇帝有言:‘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刺史不必为此事而烦恼,且饮酒取乐。刺史虽不得邓太尉之宠信,但与我相比,已是不幸中之大幸也。我戎马半生,多有战功,然因偶尔有悖邓太尉之意,竟然险些丢了性命;后虽侥幸保住了小命,可却要遭受皮肉之苦,至今身上伤痕累累。每思念至此,我痛不欲生……”说罢,唏嘘不止,泪流满面。
“田将军不必悲伤,且自珍重。”师纂又把杯中之酒喝了个净光,醉眼蒙咙地说,“盈则亏,满则溢,物极而必反,邓太尉之专横跋扈,相国已经有所觉察,并让卫军司传谕于他,要他凡事须报,不宜辄行。我等暂且忍耐数日,以待后图。”
田续停住唏嘘,揩去泪水,引而不发地说:“我倒无妨,待回师以后,解甲归田,自食其力,做一个农牧小民。倒是刺史要格外小心,免得落个身败名裂之下场。”
“呃——”师纂一愣,惊奇地问:“田将军此话何意?”
田续见师纂已经上钩,心中暗自高兴,半含半露地说:“刺史莫非忘记黄皓之事乎?”
“黄皓之事……”师纂心中不禁一惊,怔怔地瞅着田续,不知如何是好。
原来,邓艾率军进入成都以后,闻知黄皓奸佞阴险,弄权误国,残害忠良,排斥异己,欲把其斩首示众,以平息民众之愤与蜀国旧臣之怨。谁知黄皓对此早有防备,先用重金和珍宝贿赂师纂。师纂被黄皓买通,再三劝阻邓艾:黄皓虽祸国殃民,但却对我国极为有利;若不是黄皓从中作梗,打乱了姜维之部署,我军何以能如此迅速地灭掉蜀国;如果斩了黄皓,只怕蜀国旧臣心怀疑惧,于平定巴蜀不利……邓艾听从了师纂的劝告,没有斩黄皓,只是把其逐出了皇宫。
师纂原以为此事只有他与黄皓知道,没想到如今竟然连田续也已经晓得!此事非同小可,若是被邓艾得知,绝不会善罢甘休!到那时,他不仅保不住现在的这个官职,恐怕连性命也岌岌可危!想到了这里,他不由得心惊肉跳起来,连那浓浓的醉意也被吓飞了一大半。
田续见击中了师纂的软肋,心中大为兴奋。然而,他却表面上故作严肃,忧心忡忡地说:“刺史放心,我绝不会把此事泄漏于任何人!只是……据我所知,邓太尉对此事亦已有所觉察,正在暗中进行查证。若是被其查明真相,后果将不堪设想!请刺史早作防备,以消除后患。”
“这……”师纂惊慌失措地瞧着田续,惶恐地说,“以田将军之见,我该如何是好?”
“这……”田续翻了几下白眼珠,迟疑地说,“斩草应先除根。此祸之根源乃黄皓。刺史何不趁邓太尉不在成都之际,派人把黄皓暗中杀掉。只要黄皓一死,便是死无对证,邓太尉也对刺史无可奈何!”
“实不相瞒,我亦早有此意,可黄皓自被逐出皇宫以后,便已销声匿迹,不知躲藏在何处。我派人暗中搜寻了数日,始终寻找不见其踪影。”师纂焦躁不安地说,“除此之外,不知田将军还有他法乎?”
“这……”田续眨巴了几下眼皮,有些卖关子地说,“办法倒是有一个,只怕刺史不敢去干……”
“事情已经迫在眉睫,我必须孤注一掷。请田将军看在我二人多年同舟共济之情分上,助我一臂之力!”师纂真是有点急了,恳求着田续。
“我如不愿助刺史一臂之力,今日便不会至此!只是此事非同儿戏,需冒险而行,望刺史审慎行事……”田续附在师纂的耳边,小声地嘀咕了一阵。
师纂初时大惊失色,继而紧锁眉头,后来又面色阴沉,最终还是破釜沉舟地说:田将军所言甚是!我若不铤而走险,就只能坐以待毙!事已至此,也只有依田将军之计!只是……
“法不传六耳。此事只有天知地知,汝知我知!”田续心领神会地说。
师纂把两只空杯斟满了酒,感激地说:“多谢田将军为我指点迷津,事成以后,定当重谢!”
“我只求为人排忧解难,而不求投桃报李!”田续端起酒杯,抑制不住内心激动地说,“干杯!”
姜维率领蜀军主力归降,不仅把钟会从愧疚、尴尬之中解脱了出来,令他焦躁的情绪大为缓解;而且使他未动一刀一枪,就得到了大批精锐兵马和大量急需的粮草,消除了他的后顾之忧。更为重要的是:他因此而被封为司徒,赐爵县侯,增加食邑万户。姜维也因此而得到了钟会的信任和厚待,不仅让他仍旧统领原蜀军兵马,而且与他交情甚密,出则同车,坐则同席。
为了进一步取悦于钟会,也为了暗中聚集力量,姜维又传令汉城守将蒋斌、乐城守将王含,让他们率军来到涪城,归降了钟会。姜维的这一招收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既使钟会对他深信不疑,又把蜀军的精锐兵马统统集中到了自己的身边,随时都可以采取大的军事行动……
对于姜维的意图,钟会并没有察觉出来。他只知道自己手下已经有了十几万精兵强将和可供全军用一个多月的粮草,而邓艾只不过是占据了兵力空虚的成都、统率着两万兵马,其军事实力根本无法与他相比。本来,邓艾为征西将军,他为镇西将军,邓艾在军中的位次高于他;而现在,邓艾为太尉,他为司徒,二人同列“三公”之位,已是平起平坐,并无高低之别。如此一来,他对邓艾又有何惧哉!所以,邓艾遣使邀他前往绵竹参加庆功宴,他就不予理睬,只是派遣胡烈前去应付。一则想借此机会打探一下邓艾的虚实,以决定下一步的行动;二则欲故意冷落一下邓艾,以观其有何反应。
这一日,钟会闲暇无事,正在大堂上翻阅着《左传》。姜维只身来到了他的面前,笑吟吟地说:“维久闻司徒博览群书,过目不忘,《春秋》、《左传》倒背如流,今日何故又如此耶?”
“聊以解闷耳。”钟会抬起头,笑眯眯地说,“伯约已有两日未曾至此,使我深感寂寞。不知伯约这两日忙于何事?”
“维这两日闭门思过,未曾来给司徒请安,请司徒海涵!”姜维抱歉地说。
钟会奇怪地问:“伯约何过之有,需长时闭门深思?”
姜维在钟会的对面坐了下来,煞有介事地说:“维经再三反省,始如梦初醒,发觉司徒与维皆上了邓艾之当、中了邓艾之计也!”
“噢——”钟会惊愕地打量着姜维,有些意外地说:“伯约何出此言,令我困惑不解!”
“司徒待维,情同手足。维敢不如实相告!”姜维郑重其事地说,“邓艾老奸巨猾,历经三朝,貌似淡泊名利,实则利欲熏心。此次征伐蜀国,相国意欲让司徒创建不世之功,只使邓艾作为偏师,绊维于沓中,以策应司徒。然而,邓艾欲独占灭蜀之大功,而大耍阴谋诡计:他先是对相国之部署阳奉阴违,采用打草惊蛇之计,把维赶出沓中;继而他却躲在阴平,坐山观虎斗,让司徒与维在剑门关鹬蚌相争;后来他又趁司徒与维打得难分难解、无暇后顾之机,乘虚而人,抢夺灭蜀之大功。如此看来,司徒与维岂不是皆上了邓艾之当、中了邓艾之计也!维若是事先识破邓艾之阴谋,宁肯在沓中与其同归于尽,亦不退守剑门关,让争斗了多年之冤家对头得此渔翁之利!痛哉!惜哉!如今悔之已晚矣!”
姜维的这番话真是说到了钟会的心坎上,使他对邓艾的怨恨之情又加深了许多。为了能够找到更多的证据,以便将来更好地对付邓艾,把被其抢夺去的灭蜀之大功重新抢夺回来,他故作镇静,不动声色地问道:“伯约之言似有道理,然而口说无凭,何以为据?”
“维经这两日闭门深思,觉得邓艾虽是老谋深算,但最终还是露出了其马脚。”姜维停顿了一下,头头是道地说,“维在率军撤离沓中时,随军携带着大量粮草辎重,队伍绵延十余里,行动异常迟缓,首尾难顾,可用于作战之兵马不足两万;而邓艾却有三万精锐兵马,且轻装简骑,无有拖累,行动灵活迅疾,若他真欲把维绊于沓中,并非难事!但他却只是故作声势,雷声大雨点小,仅仅是尾随着维之兵马而动,即使接战,也是少战辄止。故而才使维率军顺利穿过了孔函谷。此乃一据也。维撤离沓中以后,邓艾明知驻守阴平桥之诸葛绪与雍州军难以阻截维之兵马,但他却按兵不动,隔岸观火,坐视诸葛绪被维击败而不救,让维再次得以脱身。若他立即挥兵进行追击,维将腹背受敌,何以能过阴平桥,退守剑门关?此乃二据也。维率军退守剑门关后,邓艾已经无仗可打,但他却既不退兵狄道,也不进军大剑山,协助司徒攻打剑门关,而是西进阴平,躲在那个偏僻角落里,瞒着司徒秘密策划入蜀之事。此乃三据也。邓艾率军翻越摩天岭、奇袭江油关、夺取了涪城之后,本应率军奔赴剑门关,从背后攻打此关;或固守涪城,卡断维率军回救成都之路,与司徒共同夹击维之兵马,然后合兵一处进军成都。维正因惧怕此举,才不敢经涪城回兵成都,而是舍近求远,绕道郪县。无论邓艾奔赴剑门关或固守涪城,均会把维之兵马置于绝境。若维之兵马不存,巴蜀就可一举平定。但邓艾为抢占灭蜀之功,竟然置司徒与主力大军于不顾,独自进军成都。此乃四据也……”
姜维有根有据的分析,使钟会不由得暗暗佩服,深有感触地说:“伯约之言犹如醍醐灌顶,使我茅塞顿开!然而,事已至此,又如之奈何?”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姜维冷冷一笑,深思熟虑地说,“司徒不必担忧。以维之见,邓艾虽名噪一时,但必难持久,最终将因成而败,因福得祸。”
“因成而败,因福得祸?”钟会急切地问,“何以见得?”
姜维不慌不忙地说:“从古至今,败不馁者不乏其人,而胜不骄者又有几人?人在失意之时,皆头脑比较清醒,尚可自制;而在得意之时,则会利令智昏,难以自控。韩信因功而骄,因骄而遭致杀身之祸。据维观之,邓艾不久也将步韩信之后尘,蹈韩信之覆辙!”
姜维此言,犹如一阵春雷在钟会的头上滚过,使他既感到震惊,又为之振奋。他睁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姜维,迫不及待地说:“此话何意?请伯约讲明!”
姜维不紧不慢地说:“邓艾入主成都以后,居功自傲,独断专行,擅自拜维之旧主为行骠骑将军、太子为奉车都尉、诸王为驸马都尉,蜀国之旧臣也各随高下,拜为王官。由此可见,邓艾不仅专横跋扈,目无王法,而且招降纳叛,笼络人心,其不轨之心已显露了出来。此事如被相国得知,岂能容他?故而,维以为,邓艾不久将变成另一韩信。”
“伯约果然眼力非凡,看人观事入木三分!”钟会被姜维说得心悦诚服,向姜维拱拱手,求教地问,“当今之际,我该如何是好,方可不负相国之重托?”
“这……”姜维欲扬先抑,故作为难地说,“维乃一员降将,又是邓艾冤家对头,瓜李之嫌不可不避。故而,维不便多言,请司徒自作主张。”
“伯约何出此言?”钟会焦急的心情溢于言表,恳切地说,“自与伯约相遇之后,我视伯约如兄长,言听计从,深信不疑。伯约何故如此多虑,不肯尽力助我?”
“维虽愚昧,但尚知‘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何况司徒待维如此深厚,维岂能不尽心竭力以报此恩德!只是……”姜维犹豫了片刻,才毅然决然地说,“为报司徒知遇之恩,维只好不避嫌疑,冒昧直言矣。维以为,司徒应立即把邓艾在成都之所作所为报于相国,使相国知其骄横自专之行、悖逆不轨之状,早作戒备,以防不测。十余日后,司徒应率大军移师雒县,陈兵于成都附近,严密监视邓艾之动向,以防其突然之举。只有如此,司徒方可不负相国之重托!请司徒审时度势,三思而行。”
“妙哉!有幸得遇伯约,真乃天助我也!”钟会喜形于色,兴奋地说,“事若得成,会定禀明相国,重重封赐伯约!”
“此事万万不可!”姜维连忙推辞,“维之所以献计献策,是为报司徒厚待之恩,绝非欲邀取功名利禄!维已老矣,形同槁木,心如死灰。若蒙司徒垂怜,让维重归故里,守在先妣坟前,弥补先前未能尽孝之过,维便心满意足,感激不尽也!”
钟会赞赏地瞧着姜维,翘起大拇指,不胜感慨地说:“伯约真乃孝义之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