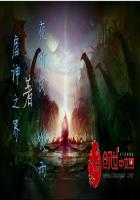即使蝉的生命在外界只有七天,但夏天从未因为停止了某只蝉的存在失色,自然和顺序的循环,让耳朵总是插不进它们歌声戛然丧失,又匆忙拼接起来的缝隙里。所以,一整个夏天都是处于音乐的平整和光滑的状态中,感觉不到死亡的惋惜和新生的喜悦。
也就是在悄然飘叶的时候,能感到那支彩笔猛然换去了一种颜色,走着走着,就是漫天的金色包围了,蝉死,乐曲最后一只颤音也很美妙。记得曾经多次自己用嘴巴啄开笼子的鹦鹉,在有限的空间内找飞的感觉,被我们捉住再次关进笼中去,在一个月后的台风中,作为一只会飞的鸟儿与木笼一起被摔死,最后一次的,在小院的绿化带里得到空间上的自由,说不出它是该悲伤还是快乐。外公也因此决定了从此不养任何鸟儿。尊重生命,也包括尊重它们选择生存和死亡的权利,以为拼命却劣质地挽留下来才是善良,存在就是某种希望,而不在乎本真的感受,这是许多人一贯的定理。从踩死第一只蚂蚁的童年开始,因为听不见喊疼的声音,只有我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快乐,并没有罪恶感。也是唯一一次,外公和我一起去院子里找鹦鹉和它们的木笼,不是日常给鸟儿晒太阳的安排。
喜爱的,深爱的,不舍的,怜爱的,它们的生命,我们无一例外地想要拼命保留,而不管它们自己是否想要留在我们身边。也许正是这种缝隙密不透风的占有欲,剥夺了它们的许多第一次,并不会再有此生的下一次。小时候,只要想拥有任何一种小动物都会轻易得到,所以,当我指着卖蛐蛐的人身上披满的鸣叫,大人确实不好拒绝我的。这样我就得到了它,暑假也因此有了乐趣和可供研究的对象。掐一段最鲜嫩的小葱,对我来说,并不是重大的事,这是维持鸣叫的唯一方法。那么唱歌给我听吧,这是它得到小葱的必须交易。整个夏天,双耳都沾满了这种单一的音符,因为它吃的食物也是那么一种。隔着竹子编织的家,也许并没有看我,而是在专心地吃葱吧,而我想说的是,它是应该一直这么健康地活着直到自然死亡。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这种做法,是对它们最好的解释了。有一天,它被提着送到我的面前,从竹笼的洞眼里露出我晚上喂给它的小葱,没有那种很小的缺口,也没有一丝声音透出。我亲自把它送去花园里,让声音从本来就属于自然,最终安静也属于它们。
“明年夏天,还唱歌给我吧……”墙壁上的爬墙虎更繁密了,没有人的喜爱包围的它们反而活得更舒畅一些,没有谁说:你必须活下来。或者也没有人说:你不该长在这里。所以,每次去的那个小院,多年来唯一没变的就是你们。有一点我不敢否认,那就是在它们绿的快乐下我埋下了许多用“爱”编织过的生命,它们的囚笼。离开反而更自由。
它纤细地穿梭在身边,而有时的某些时间,又确实是美的。当他们说,让我静一静吧,那就是想要彻底的安静。关上窗,放一杯热的茶在桌上,不久以后,就会有新鲜的鸟鸣和风泡进去这杯茶。在蛐蛐之后,谁这样说:来满足自己喜爱的爱心不是一种善良,而是对它们的残忍。我说:小虫,那时我把你放在花园的原因就在这里,这是离我最近的自然,也是你的自由了。最后一次,而对我是第一次,没有遮盖释然的笑。
选择一定有这样的刺伤,我清楚地记得一些画面,虽然没有出现在我的生活中,一方祈求舒适地离开,但亲人之爱,友谊之爱,出于本能拒绝了他们。一旦松开手,双方的美感都多一些。不是在每种时间内都会有这样的思考,在夏天尤为集中些。其实,秋天的最初依然是挂满蝉鸣的,只不过很少清楚的在听。我想的更多的是,在这七天内,它们是如何将内心和歌声做的一样滴水不漏,只渗出夏的喜悦和活力。一直排斥那些尽力在蜡烛和蚕生命期限中放大悲伤的作品,过于感性的思维只是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一定是痛苦的”,而并非“也许在它们看来,这才是最好的方式”,思想的强加比行动的强迫给予更令人恐惧,以至于一提起春蚕,我首先想到的是某些诗早已证明好的,“丝方尽”吧,该难过的到底是你还是我们呢?而你又是如何得到结论,这些微小的生命没有你过得幸福,不是该一遍遍地感怀它们的伟大与不幸,那么,坐享这些丝绸的人们又是如何理解的?
它们有自己的法则,和人类世界的不同,这是我唯一能做解释的。面带慈悲的叹惋,有时就是一种丑陋。最后一次,你不知道,对于自己还有几次的歌声,也许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但对这歌声的主人而言,毕竟只有一次,也就是以“一”为单位的“最后一次”,放过它们的喜怒哀乐,让它们露出自己舒畅的方式,那微笑也是很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