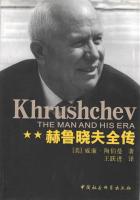每次长时间的比赛后,我都会筋疲力尽,而对于我来说,每一场比赛都是漫长的。我的发球并不是很出色,不能通过发球轻松得分,因此每一个对手都要跟我打上整整12个回合。我应对比赛的技巧和知识正在不断地提高,但是我的身体却垮掉了。我几乎只剩下皮包骨了,而且身体非常虚弱。比赛时,打一会儿就两腿发软,随后我的神经也不受控制了。我告诉尼克,以我现在的状态,根本无法和世界上最优秀的选手竞争。他也很赞同我的说法。“比赛中双腿就是一切。”他说。
我在拉斯韦加斯找了一个教练来训练我的体能,他叫雷尼,退伍前曾是军队的上校。雷尼是一个像粗麻布一样粗鲁的人,骂起人来像水手,走起路来像海盗。在很久以前的一场战争中,他曾经中过弹,那是他不愿提及的经历。和雷尼待上一个小时后,我宁愿有人一枪毙了我—他似乎以谩骂侮辱我为乐。
1987年12月,沙漠不合时宜地冷了下来。赌场21点的发牌员戴着圣诞帽,棕榈树上挂满了亮闪闪的彩灯,甚至长街上的妓女们也在耳朵上戴上了圣诞挂饰。我告诉佩里我不想等到明年了,我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强壮了。我开始有了掌控网球的感觉。
我在孟菲斯参加了自己在1988赛季的首项赛事,并赢得了冠军。那场比赛我打得得心应手,球离开我的球拍后充满了活力。我的正手逐渐加强,击出的球简直可以将对手打穿。每一位对手都以不可置信的表情看着我,仿佛在说你这些球究竟是怎么打过来的。
我也从球迷的脸上注意到了一些变化。他们崇拜地看着我、要我为他们签名的样子,当我走进赛场时他们疯狂尖叫的样子,让我感觉稍微有些不适应,但是却也满足了我内心深处所向往的一些东西。这些渴望藏得如此之深,甚至连我自己都不曾发觉。我很害羞,但是我却喜欢得到别人的关注。当球迷们开始模仿我的穿着时,我有些憎恶,但也会暗暗窃喜。
1988年,模仿我的穿着就意味着穿牛仔短裤。牛仔短裤就像我的标志一样,总是同我一起出现,有关我的文章和简介必然会提及牛仔短裤。但奇怪的是,事实上并不是我选择了它们,而是它们选择了我。那是1987年我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参加耐克全球挑战赛的时候,耐克的品牌代表邀请我去一个酒店套房看看最新的衣服样品。麦肯罗也在那里,当然他得到了最先挑选的机会。他拿着一条牛仔短裤说:“这他妈的是什么东西呀?”
我睁大了眼睛,舔了舔嘴唇想:哇,这件裤子很酷啊。麦肯罗,如果你不想要的话,那我可就要了。
当麦肯罗把它扔到一边后,我就迅速把它抢到了手。现在每场比赛我都穿着牛仔短裤,很多球迷们也模仿我穿了起来。体育评论员却在这点上大做文章,认为我是想要出风头,但事实上,就像我的发型一样,我是在尽力保持低调;他们说我是在努力改变这项运动,但事实上,我却是一直在试图阻止这项运动改变我;他们称我是一个叛逆者,但事实上我并没有兴趣当什么叛逆者,我不过是像所有的青少年一样经历着叛逆期。这二者区别很模糊,但是却很重要。心底里,我只不过是想做我自己而已,但是因为我并不完全了解我自己,我想要弄清楚我是谁的尝试是盲目而笨拙的,而且必然也是矛盾的。我现在所做的和我在波利泰尼网球学校所做的事并没有什么不同—挑战权威,寻求自己的位置,向父亲传达某种信号,为得到机会而奋斗。我做的一切都没有改变,只是现在的我站在了一个更大的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