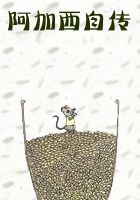我看看坐在看台上的父亲,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赛场,忧心忡忡—不是愤怒,是忧心忡忡。我也很担心,但是同时也非常愤怒,心中充斥着自我厌恶感。我真希望我是帕克斯先生戒指里那只身体僵直的蚂蚁。
在我将东西装到网球包里时,我狠狠地咒骂着自己,这时不知从哪里钻出一个男孩,打断了我的自我讨伐。
“嗨,”他说,“别再为这事恼火了,你今天没有发挥出最佳状态。”
我抬起头。这个男孩年纪比我稍微大一点儿,但是比我高出了一头,正做出一副我不喜欢的表情。他的脸有些与众不同,他的鼻子和嘴巴太过突出,与整个脸根本就不协调。而且,最令人讨厌的是,他竟然穿着一件怪里怪气的衬衫,衬衫上面的那个小人是在打马球吗?我一点儿都不喜欢他。
“你他妈的又是谁?”
“佩里?罗杰斯。”
我转过身继续收拾我的包。
他无视我的暗示,不停地嘀咕我没有发挥好,我比罗迪不知要强多少,以及下次我将如何打败罗迪。都是些废话。我猜,他的确是想向我示好,但是他以一种自以为无所不知的姿态对我“谆谆教诲”,仿佛自己是少年版的博格,因此我站起来,毫不留情地用我的后背对着他。我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别人为了安慰我而与我进行的谈话,这比一个安慰奖杯更没有意义,更何况该谈话还是来自一个穿着一件胸前印着人玩马球图案的衬衫的孩子。把网球包背在肩上后,我对他说:“关于网球你他妈的知道些什么啊?”
之后我感觉很糟糕,我本不应该这么刻薄。后来我发现那个小孩也是一个网球手,他也参加了那项赛事。我还听说他疯狂地爱上了我姐姐塔米,这无疑是他为什么和我搭话的原因—为了接近塔米。
但是如果我感到内疚的话,佩里则大为恼火。在拉斯韦加斯青少年中,盛传着这样的消息:“小心啊,佩里正找机会叫你好看。佩里见人就说你对他很无礼,下次再遇到你,他一定会好好教训你一顿。”
几周后,塔米说大家都要去看一场恐怖电影,所有大一点儿的孩子都去,然后问我去不去。
“那个叫佩里的去吗?”
“也许吧。”
“好的,我去。”
我喜欢恐怖电影,而且我有我的打算。
妈妈提前开车把我们送到了电影院,这样我们可以买些爆米花和甘草糖并找到满意的座位—中排中间的座位。我总是坐在中排中间的座位—电影院里最好的位置。我让塔米坐在我的左侧,然后让我右侧的座位空着。果然,打扮得像预科学校学生的佩里来了。我站起来向他招手:“嗨,佩里,到这边来。”
他转过身,眯起眼睛。我能看出他对我突如其来的友善行为尚存疑虑,他正试图分析此刻的形势,从而合理应对。然后他笑了起来,之前的怒气也烟消云散。他慢慢地穿过过道,走到我们那排,然后一屁股坐在了我旁边的座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