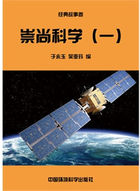周有光生平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祖籍为江苏宜兴,1906年生于江苏常州。经济学教授,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的曾祖父是清朝的官员,同时也在常州经营棉纺、织布、当铺等产业。清朝咸丰年间,太平军攻打常州,他的曾祖父全力支持清军守城,以家产供守城清军军饷,后常州城被攻破,曾祖父投水自尽,周家的雄厚家财尽失,从此家道开始衰败。
周有光生于江苏省常州市,后来迁居苏州。1923年开始就学上海圣约翰大学;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随同全体同学和华籍教授离校,改读离校师生创办的光华大学,1927年毕业。1928年至1949年,任教光华大学、江苏和浙江教育学院;后任职新华银行,由银行派驻美国纽约。1949年上海解放后回国,担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
1955年10月,周有光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提出方案的三原则,方案在1958年公布。
此后,主持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制订,提出正词法的基本规则和内在矛盾,基本规则在1988年公布。
1979至1982年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文献技术会议,该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参加制订聋人教育用的汉语手指字母方案(1963年公布)和汉语手指音节设计。
1958年开始在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开讲汉字改革课程,讲义《汉字改革概论》1961年出版第1版,1979年第3版,1985年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
1980年开始,担任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中国方面三委员之一。出版《新语文的建设》(1992)、《新时代的新语文》(1999),阐述语言生活的历史进程、人类的双语言生活、国家共同语和国际共同语的形成和发展。并出版《中国语文纵横谈》(1992),提出汉字效用递减率、汉字声旁的有效表音率,阐述整理汉字的四定原则(定形、定音、定序、定量)。
1980年,周有光发表《现代汉字学发凡》,1983年发表《汉语内在规律和中文输入技术》,阐述按词定字的原理和拼音变换汉字的原理,提倡以语词、词组和语段为单位的双打全拼法,使拼音变换汉字技术代替字形编码,1983年制成软件。2000年出版《汉字和文化问题》,倡导研究现代汉字学;上海师大、华东师大、北京大学先后开设现代汉字学课程。1998年出版《比较文字学初探》,提倡比较文字学的研究,在世界文字发展史中理解汉字的历史地位;提出六书有普遍适用性、文字三相分类法;对人类文字的发展规律进行新的探索;清华大学等校采用作为教材。
1989年,周有光在83岁时离休,继续在家中研究和著述。2000年出版《现代文化的冲击波》,阐述世界四种传统化的历史比较和华夏文化的光环和阴影。2001年选取90岁后发表的部分文章编成《周有光髦耋文存》,提倡华夏文化百尺竿头更上一步,适应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周有光先后共出版书籍20多种,发表论文300多篇。退休后,著述不断,2005年亦有《周有光百岁新稿》一书出版。曾任第四、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从《西游记》到《资本论》
周有光的祖上在江苏常州是望族,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书香门第,藏有很多书,“不过全是文言的。”
作为出生在晚清的周有光,小时候接触的依然是《三字经》之类的书,“那时我们家的书很多,随便我看,但书都是文言,我都看不懂,小时候我对《三字经》也不感兴趣,”给周有光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西游记》。
“我们那一代人,小孩子认得几个字以后,都喜欢看《西游记》,不像现在可以看的东西多了,我们以前没什么好看的,”不过,周有光却自言自己看《西游记》是看了两遍才看懂的,“读书是件很好玩的事,第一遍看不懂,不要放弃,看第二遍,也许就能看懂了,”就是通过这样的阅读,周有光认为自己的“阅读能力也就提高了。”
1923年,周有光进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那是教会学校,图书馆随便去看,那时我不仅看中文书,也看英文书,”那时的周有光受到左倾思潮影响,由此便决心阅读《资本论》,“对我们来说,《资本论》很重要,但是那时没有中文的,我埋头苦干阅读英文版,结果看不懂,不是文字看不懂,而是内容看不懂。”由此,阅读的乐趣往往就跳跃在第一遍的不懂到第二遍的懂之间。
书橱兼做菜橱,菜有书香
1956年,周有光从上海调来北京,住沙滩原北京大学内,那是民国初年为德国专家造的一所小洋房,周有光占其中两间半房间。“一间我母亲和姐姐住,另一间是老伴和我带小孙女住,半间做我的书房、客室、吃饭间。”而周有光也只能将书放在半间书橱内,“另一半留着放菜碗,由此我在《新陋室铭》中写道:卧室就是厨室,饮食方便,书橱兼做菜橱,菜有书香,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
书橱与菜橱功能合一的境遇只有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才有好转。当时,周有光所在的单位建造新简易楼,分得两大两小四居室。其中一小间,9平方米,也就功能独一地做了他的书房兼客室,“我的书桌很小,只有90厘米长,55厘米宽,一半放书稿,一半放电子打字机。书桌又破又小,一次我玩扑克牌,突然一张不见了,原来从桌面裂缝漏到下面抽屉里了。”
书桌虽小,书橱却很大。在这个9平米的空间内,除了在窗口放小书桌,入口放个沙发,其余之地全是周有光的书架。周有光嫌这个书房小,进而,四个房间全都被布置成以书架为主,书成了这个家的主角,“我家里没有什么家具,因为放了家具就不能放书了。”
尽管四间房子全被用来藏书,但周有光还是认为自己是有书无斋,“我国外亲戚朋友,做教授的,都住的小洋房,他们都有书房。什么叫书房呢,不仅有看书、写文章的地方,还有一个藏书的地方,等于是个小图书馆。我这是破房子,是有书而无斋。”
沈从文叫他“周百科”
从小时候开始,就读了很多书,喜欢看《西游记》是周有光还记得起的,至于其他的书,则因为“太多了,说不上来了。”不过,周有光还清楚地记得对自己终身受益的书,那就是《不列颠百科全书》。在周有光的书房中,《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是占据了一定的地位。
周有光专门有一书架摆满了《不列颠百科全书》,共三排,从上至下分别是中文版、英文版、日文版。
事实上,周有光还有“周百科”的外号,那是拜连襟沈从文所赐。而在大学时,周有光与百科全书的情缘就结下了。
当时,大学老师指定《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一些篇章作为周有光及其同学必须阅读的课外读物,“比如说世界历史,就告诉我们下课到《不列颠百科全书》看哪些条目。”
“这部书非常好。一个题目,简简单单给你讲,而如果去看书,一个小问题就是一本书,看百科全书反而可以节约时间,”周有光自认《百科全书》的作用非常大,“对我非常有用,其实对每个人也有用。百科全书是没有围墙的大学,你可以先了解大致情况,然而再查看其他比较专业的书。”
到了后来更有趣,改革开放时期,中美两国要搞文化合作工作,当中有一项就是要翻译美国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周有光竟然做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三位编委之一,其他两位编委是刘尊棋和钱伟长。“其实,《不列颠百科全书》本来是英国的,因为二战期间英国的很多企业都卖给了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是如此。我们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不过由于当时国内购买力很差,就压缩成10本,称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由此,大家更有理由叫周有光为“周百科”。
语言学家的“前世今生”
周有光最初是搞经济学的,对金融特别熟悉,解放初期还写过《新中国的金融问题》、《资本的原始积累》一类著作。不过,在周有光家里却很少可见经济方面的书籍。
周有光解释,自己所住的隔壁就是办公楼,有一个小房间全都放着他的经济学书籍。不过,离休后,他把这些书全部捐给单位图书馆了,“我已经改行了,不搞经济学了,而搞语言文字学了。”由此,在周有光的书架上所列的大都是语言学、文字学的书:《语言文字学术论文集》、《外来语词典》、《常用构词字典》,甚至小到一个国家语言研究的书籍,都在其内。
“经济学当中最重要的亚当·斯密斯和凯恩斯,可以说经济学都是外国的,但是文字学中国古代就有,”周有光认为文字学是中国最早的,就必须看古代的东西,由此在他的书架中《说文解字》是不可少的,“作为一个中国人,要研究语言文字学,一定要研究中国古代到现在文字学的发展。中国古代没有语言学,文字学中包括了很多语言学的知识。”
“事实上,我的学术研究在离休以后就结束了,”为了查阅书籍,此前周有光要到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去,“我年纪大了,在家都可以自理,但出去不方便,站不住了,不能去图书馆了。”
离休后,周有光开始随便看书,主要看世界历史、各地研究文化问题的,这成了他研究的另一个兴趣点。书架上也多了历史、文化方面的书籍:《全球通史》、《世界文明史》、《神光沐浴下的文化再生》、《文明的狂飙疾进时代》。“全球通史》、《世界文明史》很重要,之前的历史不是全球化的,这两本书却有全球化的眼光。”
人与书,俱不老
尽管周有光认为自己的书房很破旧,但书却很时髦,往往引领潮流。这也难怪,周有光书架中书的来源很多都是漂洋过海的。
“现在做学问,你不看外国书是不行的。”由此,周有光在国外的亲戚朋友经常给他从国外书店买书、寄书。直到现在英文版的《年鉴》是周有光每年必买的书之一,“我每年都从外国买《年鉴》,因为要查阅资料。”
也正因为有着国外书籍的补充,周有光书架上的书颇为时髦。三年前,《世界是平的》就已经摆进了他的书架中。那是本英文版的,在《世界是平的》被译成中文版前,周有光就已经接触了弗里德曼关于“世界是平”的思想。
周有光书架中时髦书籍还有《张氏四姐妹》,英文版的。周有光的妻子是张氏四姐妹中的老二张允和。前不久《合肥四姐妹》中文版出版。而周有光是在几年前就已经看了这本与其有着密切关系的书,“这种书在外国人看看还是好的,中国人看就不够味了。因为外国人写中国的东西,常常不地道,这不能怪他们,文化是有差异的。”
尽管周有光基本上是足不出户,不过对于新的文化现象他一点都不陌生。在他的书架中就有于丹的书,甚至连批驳于丹的书也一并俱全。
“于丹论《论语》的书我也看,包括批评她的书我也看,于丹做了个通俗化的工作,做得很好,我们需要这个工作,”周有光还专门写了文章,“现在许多人都骂于丹,如果从学术水平来看,于丹并不是最高的。但于丹做的不是学术工作,是科普工作,把孔老二的学问给大众,这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