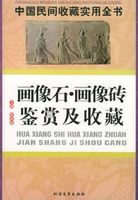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山西饶材、竹、、卢、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出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盐铁论·本议篇》中也有一段类似的文字。由此可见,随着商业转运贸易的发展,许多地方土特产已在全国范围内成为富贵之家的“奉生送死之具”。商业的发展,必然促进商业城市的兴起和市场的繁荣。四川汉代画像砖对当时的市井作了细致的描绘。
不论是古代还是当代,商业市场都不是随意发展起来的,它必有一定的依托。在汉代,置市必须在县以上的治所,这一制度到唐代仍然遵循。市井画像砖上,商店林立,人物众多,市肆门垣、市楼、市隧齐备,可以肯定是昙以上治所的固定商业市场,而不是乡间草市,其中新繁和成都出土的市井画像砖上,市楼矗立于市井中央,列肆与(chán,民居房,市房)排列众多,制度完备,很可能是成都的市貌。
固定的商业市场不仅要设在城里,而且必须在固定的区域,以垣墙环绕,与里坊相隔,设市门,定时出入,也就是说市场是封闭式的。市井画像砖上,市肆门垣整齐排列,广汉县和新繁县出土的市井画像砖上,还有隶书题记“东市门”文字,彭县出土的市井画像砖上有“南市门”、“北市门”的文字,与制相合。《三辅黄图》中说,长安的市“各方二百六十步”、“四里为一市”,也就是说,汉代的市井为方形。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宁城图上的“宁市”正是方形,印证了记载的真实性。成都等地出土的方形市井画像砖表明,当时四川的城市与西汉京城长安以及国内其他市制是相同的,由此可见政治统一的巨大力量。
汉代各地市肆都有政府派的市令、长或丞进行管理,他们一般住在市楼里;同时还派市啬夫(古代官名)巡行市场,以纠违法。市楼是市肆中最高大显著的建筑。张衡在《西京赋》中说:“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市楼上可以观察并监视市内各隧的活动。市楼上悬鼓,击之以开闭市门。楼下坐着市署官吏。广汉县周村出土的市井画像砖上有一座二层市楼,有榜题明示,二楼悬鼓一面,楼顶饰以单凤,一楼二市吏对坐交谈。
市肆管理有一定的规定,凡进入市内的商品,必须分类摆列在列肆中交易。肆即为商肆,因市中有商肆,故称市肆。又因各肆是排列成行的,故又称为列肆、市列、行市。肆店里有店,崔豹《古今注》中说:“肆店,肆所以陈货鬻之物也,店所以置货鬻之物也。”也就是说,肆是摆设商品用以买卖的,店是放置商品(货物)之处。成都出土的市井画像砖上市列分明,列肆后面(靠市墙处)还有房屋建筑,隐约可见屋内有堆积之物,可能就是放置货物的店,或称“邸舍”、“廛”。肆店里的货物交易,有肆长监督,重要的商品成交,要立书契券约。市列之间有供行人来往走动的人行道,即隧。成都出土的市井画像砖中间就是十字形的隧。
不论从文献记载还是从画像砖图像上,我们都可以看出,尽管汉代政府对商品交换进行了抑制,对商品市场实行严格的控制和管理,但这并未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买卖仍然活跃,市井之内的热闹景象,有如班固《西都赋》描述的长安市:“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左思《蜀都赋》也说,成都市上“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靓妆。买贸鬻,舛错纵横。异物堀诡,奇于八方。”四川汉墓出土的市井画像砖反映的正是当时市场交易的热闹景象,让我们来看两个实例。
新都县出土的市井画像砖展现了一个较小的市井全景。左右两侧上部分别题有“北市门”、“南市门”字样。画面上共有二十多个人物,或坐或立,正在相对交易。有的正提着货物,有的坐地行贩,有的置桌交易,有的设帐为市。
成都市郊出土的市井画像砖平面略呈方形,有市墙围绕,三方设门,每座门有三个门洞。左边市内隶书题记“东市门”、北边市内隶书题记“北市门”,市中置重檐市楼一座,上悬一鼓,楼下正中开门。进市门的十字路(隧)上有人物数起。东隧五人,或相对而语,交流市场信息,或行走于市,尽快赶到目的地;西隧有七人活动,服饰各异,神态活泼;南隧也有七人,或坐或立,似在讨价还价;北隧四人,分两行沿隧边靠列肆而坐,面前放着售卖的商品;隧的中央有类似小亭的建筑,南北隧边坐着商贩,隧的两侧为列肆,如长廊式建筑,共分四个交易区,每区的肆有三至四列。西北、西南和东南的三个贸易区的列肆之处,靠近市墙,又有纵横交错的市宅,一方靠近市壁,三方为列肆,形成如长方形的宅区,中间另立店房(邸舍)。靠北面市墙内两区的市店内,可以看到堆积的货物,以及顾客、商人的活动。
市井画像内容丰富,但看不清交易何物,新都出土的沽酒图则十分明确,店主正在为门外顾客盛酒,左上方还有二人正向酒店走来,左下方一人手推辇车边向外走,边和店主话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