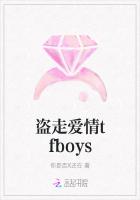宗教,就其与社会的关系而论,—无论是一般的关系,还是特殊的关系,一也可以分为两种,即人类的宗教与公民的宗教。前一种宗教没有庙宇、没有祭坛、没有仪式,只限于对至高无上的仁帝发自纯粹内心的祟拜,以及对于道德的永恒义务;它是纯粹而又朴素的福音书宗教,是真正的有神论,我们可以称它为自然的神圣权利。后一种宗教是写在某一个国家的典册之内的,它规定了这个国家自己的神、这个国家特有的守护者。它有自己的教条、自己的教仪、自己法定的崇拜表现。除了这个惟一遵奉这种宗教的国家而外,其余一切国家在它看来全都是不敬神的、化外的、野蛮的;它把人类的权利和义务仅仅伸张到和它的神坛一样远。一切原始民族的宗教便是如此,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公民的或积极的神圣权利。
《社会契约论》
如果我们希望孩子们掌握一些东西,就不应对他们谈论宗教。
《忏悔录》
我想谁都知道,一个儿童,甚至一个成年人,其有所信仰,无非是生在哪个宗教里就信仰哪个宗教,这是显然的。这种信仰有时会减弱,但很少有所增强;信仰教义是教育的结果。
《忏悔录》
基督教是一种纯精神的宗教,一心只关怀天上的事物;基督徒的祖国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的确,基督徒在尽自己的责任,然而他是以一种深沉的、决不计较自己的成败得失的心情在尽自己的责任。只要他自己问心无愧,无论世上的一切是好是坏对他来说都无足轻重。如果国家繁荣,他也几乎不敢分享公共的幸福,他怕自己会因国家的光荣而骄傲起来;如果国家衰微,他也要祝福上帝的手在对自己的人民进行惩罚。
《社会契约论》
基督教只宣扬奴役与服从。它的精神是太有利于暴君制了,以致暴君制不能不是经常从中得到好处的。真正的基督徒被造就出来就是作奴隶的;他们知道这一点,可是对此却几乎无动于衷;这短促的一生在他们的心目之中是太没有价值了。
《社会契约论》
可是,每个公民都应该有一个宗教,宗教可以使他们热爱自己的责任,这件事对国家有很重要的关系。但这种宗教的教条,却惟有当其涉及到道德与责任—而这种道德与责任又是宣扬这种宗教的人自己也须对别人履行的—的时候,才与国家及其成员有关。此外,每个人都可以有他自己所喜欢的意见,而主权者对于这些意见是不能过问的。因为既然主权者对另一个世界是根本无能为力的,所以只要臣民们今生是好公民,则无论他们来世的命运如何,就都不是主权者的事情了。
因此,就要有一篇纯属公民信仰的宣言,这篇宜言的条款应该由主权者规定;这些条款并非严格地作为宗教的教条,而只是作为社会性的感情,没有这种感情一个人既不可能是良好的公民,也不可能是忠实的臣民。它虽然不能强迫任何人信仰它们,但是它可以把任何不信仰它们的人驱逐出境;它可以驱逐这种人,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敬神,而是因为他们的反社会性,因为他们不可能真诚地爱法律、爱正义,也不可能在必要时为尽自己的义务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但如果有人公开承认了这些教条,而他的行为却和他不信仰这些教条一样,那就应该把他处以死刑;因为他犯了最大的罪行即在法律面前说了谎。
《社会契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