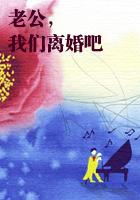在胡适的认识中,《墨子·非攻》上篇是基于道德性的正义感而主张“非攻”,而中、下篇是基于如Jeremy Bentham所说的“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的逻辑上来叙述“非攻”主张的。胡适评价《非攻》上、中、下篇的差异时,指出“《非攻》上只说得攻国得‘不义’,《非攻》中、下只说得攻国得‘不利’。因为不利,所以不义”(参见其《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胡适对于《非攻》上、中、下篇,在学问上没有做出明确的区分,但在评价时,指出“尤其是三篇里的《非攻上》实在是最合乎逻辑的反战名著”,把《非攻》上篇和中、下篇分开来叙述。比如说在现代的研究中,对墨家的看法一般倾向于“义即利,利即义”的见解,作为对《墨子·非攻》篇整体的认识,胡适虽然也认同这个见解,但胡适还是意识到了《非攻》上篇与中、下篇的差异。就《非攻》篇整体来说,其关键字句是功利主义,但最初篇的《非攻上》并不是论功利主义的,当然,把《非攻》三篇汇总起来看,就使人不易懂了。其实正如李承律前面所说,上篇“虽然也说利,但这个利不是功利主义的利;《非攻》中、下篇的利是功利主义的利,此利与义相同”。
墨子也好,胡适也好,对于战争,最初都是纯粹地或原理性地以义或不义为问题中心。但到了后来,一旦自己要实际面临战争了,就有如从《非攻》上篇到《非攻》中、下篇转换一样,胡适由主和变为彻底抗战,转变了自己的主张。胡适主张的转变,正好与《墨子·非攻》篇是同样的流向。尽管胡适年轻时(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是和平主义者,但最终却积极推动了抗日战争。墨子在原理上也是和平主义者,而实际却以“诛”的名义,容许了战争。如此,胡适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主张、想法、行动,实际上正好像采取了《墨子·非攻》上、中、下篇这样的阶段性的主张、想法、行动。虽然这并不是胡适有意识性地去按《非攻》上、中、下篇所做,但最终却殊途同归。对于如何来处置暴力战争,即使是和平主义者的胡适,最终也还是容许了战争。墨子按《非攻》上、中、下篇的顺序展开讨论的过程,与胡适由作主和努力到彻底抗战的这个观点转变的经过,可以认为是同样的。同样是和平主义者的两人,尽管主张反对战争或者主张议和,但最终却容许了战争这样的过程,可以看出其中有某种矛盾的存在。两者结果都不能避开战争,不仅容许了战争,抗战思想一旦觉醒了,两者都成了战争的专家。墨子呢,想出防卫术,以集团为单位进行战争行为。而另一方面,胡适设想了周密的作战方针,引导政府的首脑部门,自己也在外交上,在美国这个最重要的国际舞台上作出实绩,发挥了其战略智慧。
作为“极端和平主义者”的胡适,而自己最后却成了“人类理智上最矛盾,最无理性,最违反逻辑的好战的人性”的人了。也就是说,自己也成了被拘束于人性中某种矛盾的人了。在当代,地球上依然持续着杀戮行为。我们人类对于战争的拒绝感,应该比以前更强烈了,但尽管如此,还有战争在进行着。人类的矛盾,至今也没有消失。胡适到了晚年,在自己经历了战争等所有人生体验之后,还指出“《非攻上》实在是最合乎逻辑的反战名著”,对《非攻》上篇作了很高的评价。这并不是年轻人常有的理想论,而是对当代正在进行着战争、或打算进行战争的人,提出的来自经验者的重要转言。战争结束之后,胡适还对《非攻》上篇作出如此高的评价,这其中包含着启发人类本性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