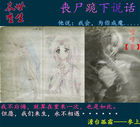李丹从小时没做过这种劳动,他只是在河边上用杠杆车过水,觉的比这个省力得多。他拐到那里,从畦背上走过去,才吞见香菊隐在一排几棵又高又密的鬼子戔后面。
这是特意栽培的鬼子姜,它饫起来,可以遮蔽太阳。一说小胡芦攀延上去,开了一朵雪白的小花,在四外酷旱的田野堅,只有它还带着淸总的露水。香菊抬头看见李丹来了,就停下来,喘着气!可以你来干什么,这么晒天。
李丹看见香菊的衣裳螯个湿透了,贴萑身上,头上的汗水,随着水斗子的漏水,丁当滴落到井里去。就说;这!活太累我来邦邦你吧?
香菊笑了一笑,訧又把水斗子哗啦啦放下去了,她说,你不行,好好养你的伤吧!
李丹站在香菊对茴,把拐支稳,低下头一看:那是一眼大井,从砖缝里蓬蓬生长着特别翠绍的荜,井水震菡的很厉害,可是稍一平静,他就看见水里而轻微的浮动着晴朗的天空,香菊的和鬼子姜的影子,还有那朵巍巍的小朵胡芦花。
李丹很喜爱这个地方,也着实心痛那淺园流汗的人,他又幼香菊,很累了,休息一下吧。
香菊说。
不能休息。奸容易才把垅沟潢满,断了流又X知道要费多么大旳力接着她堅一望西北上说广你看看那里起来的是不枭云采?
李丹转身一望说:那不是云采,那是山。
下场雨就好了,香菊喘着气说,我在辋梦里都听若雷响,我们盼望庄稼饺好,多打粮食,就象你盼望多打胜仗一样:~李丹顺着坭沟走过去,地是那么干燥,李丹想:耍吸收多少水,才能止住这庄稼的饥渴?要流多少汗,才能換来几斗粗粮,供给我们吃用?他深深的感觉到自己战斗流血的意义,对香菊的辛苦劳动,无比的尊敬起来。回头望望吾菊,香菊低着头浇园,水越浅,井越深,绳越长,她浇着越吃力了。
等到天晚,风吹着香菊那服红流汗的脸。
我们回去吧!她说着又浇上一斗,放倒在水池子上,水滴丁丁当当落到井里。她叉步过来,在水池子黾洗了冼脚,就登上了放在一边的鞋。她问李丹:你想吃计么菜?
李丹说:我想吃辣茭:不。你的伤还没好利落,我给你摘几个茄子带叨去。香菊抖着湿透了的辫了走到菜畦里去,拨着卟子,找着那大个的茄子,摘了几个。等她卸下辘辘回家的时候,天色已经裉晚了。她说:从这里道上冋去吧。
她背若辘辘,走在前面,经过一块棒子地,她拔了一颗,咬了晈,回头交给李丹,李丹问:甜不甜?
香菊回过头去,说广你尝尝呀,不甜就给你广李丹嚼着甜棒,呑菊慢慢在前面走,头也不回,只是听着李丹的拐响,不把他拉的远了。
天空只有新出来的、弯弯下垂的月亮,和在它上面的那一颗大星,活象在那旷漠的疆扬,有人刚刚弯弓射出了一粒弹丸。
1943年于
一九四七年六月间,我当记者,跟随树人同志从某县县城出发,到四区去检査大生产工作。树人同志事变以前在这一带做过很松时期的党的秘密工作。
树人同忐骑马,我骑车子在前面。天气热,又是白沙土道,很是难走,到了一个村边,我把车子靠在一棵大柳树下而,歇着凉等他。
树人同志到了,他说:到村里休怠吧,我带你去看铝一个老同志,我们有十几年不见面了:我推着车子,他拉着马,慢慢走进宁来。走不远,往北拐进一个破旧梢口,媒西边有一个小白门,锁着哩。树人同志说:喂,这老头儿哪诅去了?你来把马遛一違,我去找他。
我把车子靠好,拉箸马在门口慢慢遛着,树人同志跑到宁上去了。我看出这梢门里,原是一家大宅院,后来分做几户,房子有的拆了,有的叫故人烧毁了,有的还完全,却很陈旧。从庭院中那些树木、房屋、门窗的形式看,这该是个大破落户家庭。
过了一会,树人同志搀扶着一个老久儿间来了,那老头几一边笑一边说:树人,你不要搀扶我,我闫己的家门,道路熟若哩!
老人的双目失明,艿朵好象也有些他短小胖壮,花白胡子,头上半禿,却留着头发,好象事变以前的一个髙级小学的校长。
到了门口,他从怀摸出钥匙,一下就捅幵了锁,让我们进去。
我拉着牲门进院,老人恻着耳朵听丫听说:有牲口吗?我去找个人来冷饮!
院里是三间北屋,是拆了楼的坐子,门前两棵髙火的香椿树,树皮斑驳,枝叶希少,看来在五十年以上了。对面三间南屋,门锁着。西边是一段破墙头,那边象是一个里院,有三间赀南房,院里种着菜。老人趴着墙喊一声;秋格,那边南星里,有一个女孩子答应一声,就跑出来,问:干什么呀?老爷!
咱们来了客,你牵着性口到井上饮饮!
女孩子有十八岁,身体结实,从破墙上通的一声跳过来,从我手里接过性口去。
树人同志贴着老人的耳朵问:这是准呀?
老人说:你不认识她?这是凤儿的大孩子,
啊,这么火了!树人同志高兴的说,你母亲哩了母亲看姑姑去了,女孩子笑着说,母亲常和我:门堤念大叔,我说叫她明天去,她非今儿个去不行!
老人又说:从她父亲牺牲了,她们就搬到这村来住。家里穷,又是烈属,村里把那房子给了她们。她还有一个兄弟和一个妹妹哩!
快去叫他们来,树人同忘说。
那不是他们,就在那边屋子里广女孩子说。
我们往西院里一晋,可不是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子,正扶着门榧看我们。树人同志跳过墙去,拉着她的手问长问短,到屋里去了。
大女孩子牵出牲口去,老人从北屋里搬出一条板発来,放在南房凉里。树人同志回来,才把我介绍了。老人很荥热的握着我的手,叫我在他耳朵旁边,恨告自己的姓名,我大声报了名字,他很喜欢,说:我记住了你的声竒。你什么时候走到这里,你一说话,我就知道若朋友来了。
我们坐下。女孩子牵着牲口回来,手逛还提了一大涌水,说:在井上它喝的不多,叫它歇一歇再喝吧!
她把牲口拴在香樁树上。
老人问:牲口饮好了?
女孩子大声说:饮好了!
好:老人说,秋格,听我说:你去弄点面来:我们客來了,擀凉而吃。
女孩子答应着过墙去了。
这些景象,谈话,对我因为生疏也就觉得平常,在树人同志的心里好象引起很多波澜。老人也好象在那迅思想什么,不断用手摸着那花胡子。过了一会,树人同志抬头告诉我说:事变前那些年,我在这一带做秘密工怍,这院子就是我那时候的机关,老人是个高小教员,他倾家荡产来邦助革命。我们在这屋里办过列宁小学,专招收那些穷人家的孩子来上夜校,那些孩子们后来就成了这一带革命的根基,现在革命开花结果了,很多人在地方上负重要的责任。那女孩子的母亲叫凤儿,跟着父亲念书,富家子弟来求婚,老人说,那是我们的敌人,都拒绝了,许给了他最喜爱的一个穷学生,我们的同志,叫马信涛。老人说,在将来,穷人才有出息,有作为。老人后来被捕下狱,受酷刑,双目失明,耳朵受伤,差一点死在狱里。听说信涛在事变以后,参加部队,当团政委,五一那年,在平汉路一次战斗里牺牲了。……树人同志还没说完,老人说:树人,最近有什么好消总?
树人同志报告了些老同忘们的消息,又从皮钽里拿出中央二月指示,笑着说:这里贫中央的一个文件,叫他给你念念!
老人很高兴,他庄严静穆的倾耳听着。我和他并肩坐着,大卢朗诵中央的二月指示:那主要是分析爱国自卫战争的形势和指示进一涉实行土地改革的。足足念了有吃一顿饭的工夫。
我念完了这个文件,从心里觉得做了一件最高兴的事。有一股热热的倩感鼓荡着我,竟一时想起以后有多少工作要我去做,要去拼命完成!
老人听完了,沉默转。树人同志笑着对我说:他在思考、研究问题哩!
拉了一会,老人问:在这半年里面,我们一共消灭蒋介石多少军队我告诉他消灭了五十九个旅。
老人又问:尽是哪几次大的战役?每一次战役消灭多少?我们部署的约略情形又是怎样,我一时说不详细,就敷衍了草了几句,老人有些不满,他说:你应该记的洁楚,材料确实详细,才能分析研究。这样含胡其辞,使我这没眼的人难以捉摸呀!毛主席还在陕北吗?他的身体怎样?
我说:还在陕北,他的身体很好。
好。这就是天大的胜利和好消息。老人说,我们的电台为什么不常报告些毛主席的消息,他们不明白有多少人关心毛主席的身体,比关心一个省城,甚至一个京城还重要。
人同志叫我去邦那女孩子做饭,我跳过玻墙,到那边南屋里去。那是两间房子,屋里放着些织布纺线的家具,整齐干净。
屋里并没有叫秋倍的那姑娘,一个小姑娘正坐布地上学汸线。另釘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坐在里间炕上,肌着窗台,拿铅笔描画什么,听见我进去,回过头来笑了一笑。这孩子浓眉大眼,昨常神气,我说:你同树人叔在一块工作:我说:嗯。你叫什么。
我叫承志。那孩子说,接着腼腆的一笑。你两和树人权说说,叫他带我出去工作!
我说:你没有上学广他说:我想去当泡兵。
我才宥见,他描画的是一本新近战场上使用的各种泡的图样。我正要问他为什么要当炮兵,看见秋格推完了碾子,满头大汗端着半簸箕面回来了。一进门就问:还没点火。
小姑娘手忙脚乱,赶紧放下纺车往锅里添水,打火烧柴。秋格用手背擦着额角上的汗,笑着说:同志,你看我们这日子,一个这么小不顶事,一个大些了,什么也不愿意干,整天回那个!我觉得我这工作,比你们千的活重要广男孩子不服气的望着我说广你叫这位同志说说,穷人怎样才叫彻底翻身?
穷人的饭,怎样才能吃的长远?
那得生产女孩子沾手合着面说。
你叫我说,光推碾子捣磨不行,还是先打败老蒋要紧!男孩子说。
你想当兵,想成了疯魔,女孩子说广你可别吃饭呀,人家做熟了,你比谁也吃得多。
我问村里给了他们多少地,怎样种法,女孩子说:我们分了十四亩地,我种耕耩锄耪你全会吗?
喂!同志,男孩子笑着说,你别认识不清了,人家年上当选了劳动英雄哩!
用着你了!女孩子瞪了兄弟一眼,接着说,学哩:今年我种了三亩棉花,二亩花生,再过来,吃花生吧!
做熟了饭,我们就在这屋里吃。老人安排我们坐好,一个劲叫秋格给我添皈菜,秋格笑着喊;他们都满着碗哩!
起了晌。我们告辞要走,说过些日子回来看他们。老人同三个孩子一直送我们到村外,树人同志拍着老人的肩头说:好好保重,我们完全胜利的日子不远了!
老人安稳沉静的说:那是自然。不然我们苦干了那些年,又苦千了这些年,为的是什么呀!
我们走出很远,孩子才抉了老人问去。天气还是很热,在那样毒热的太阳下面,树人同志信马由缰,慢慢走若,很明显,他在回想过去那些经历。他对我说:老人还有个二女儿叫翔的,一九三三年在北平被捕牺牲了。她同我感倩很好,老人原主张我们结婚的。今天,我没敢提起她来,老人也不提她,这一年秋后,我随军攻打津浦线。
这是冀中平原的东北部,池势很洼很平,命落很希。我们的军队从南北并列的一带村庄,分成无数路向车坫进发。天气很睹朗,车站的水塔看的很清楚,田野里的庄稼全收割了,只有槔子玷、绿豆蔓一铺一团的放在地里。
部队拉开距离,走的很慢。我往两迫一看,立时觉得,在碧兰的天空下面,在阳光照射的、布满谷楂秋草的大池上,四面八方全是我们的队伍在行逬。只有在天地相接连的那里,才是肖肖的风云,低垂的烟雾。这时还有人在秋草地上牧羊,羊群是那样的洁爱和安静人们丝毫没有惊扰。
那里是云梯,一架又一架!那里是电线,一捆又一梱丨那里是重炮、重机枪。背负这些东西的,都是年轻野战的英雄们,从他们那磨破的裤子,拖带着泥块的鞋子,知道他们连续作战好哩日月了。
突然有一只野兔奔跑过来,有几个幼小的炮兵连声呼喊起来,我看见其中一个,恰恰就是在老人家迂见的那个男孩子承志!
到了冲锋的地点,那个紧邻车站的小村庄。古运粮河从村中间蜿蜓流过,这条河两岸是红色的胶泥,削平直立,河水很浑很深,流的很慢。两岸都是日子,白菜畦葡萄架接连不断几条乌黑的电浅已经爬在白菜上,挂到前面去了,战士扪全紧张起来,我听到了战场上进攻的信号、清脆有力的枪声,冲锋开始了。我听见命令:过河,就看见那个小小的炮手一一马承志,首先跳进水里,登上了对岸。
这孩子跃身一跳的姿式,永远印在我的心里,这是标志我们革命进展的无数画幅里的一幅。在这以前,有他那年老失明的外祖父、在平汉线作战牺牲的马信涛、芻谨生产的姊姊马秋格;从它后面展开的就是我们现在铺天盖地的大进军,和那时时刻刻在冲过天空、吱吱作响、轰然爆炸的、我们的攻占性的炮声。
1948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