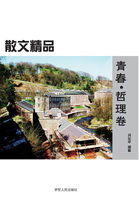关于知识分子主题的发展脉络曲折复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通过狂人这一叛逆者的疯言疯语,使我们感同身受一个“独战庸众”的个人所承受的巨大压力,有所发现的紧张以及最终不得不向现实妥协的苍凉心境;《在酒楼上》通过吕纬甫与“我”的邂逅,吐露“蝇子式的绕圆圈”的生活苦闷,表现了现代知识者的孤独、颓唐、失落、妥协和觉醒之后找不到出路的绝望感。是鲁迅先生开启了知识分子自我审视、自我启蒙和真诚忏悔的先河。在钱钟书的《围城》里,方鸿渐是个充满自我矛盾的人物,他既正直又虚假,既真诚又油滑。在几十年后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里,倪吾诚上演了另一出文化性格的悲剧,他向往西方文化,却无时不在传统文化的包围之中,被几个乖戾的女性折腾欲死,受虐而又虐人,忍受着无可解脱的痛苦。我们记得《激流三部曲》中,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遭到无情的摧残,觉慧的反抗和出走,曾带来了怎样的曙光和气息,而新时期巴金的《随想录》,既是作家在自己身上发现觉新品性,触摸到知识分子人格中的奴隶根性,也是对鲁迅先生知识分子自审主题的接通,我们由之引起深深的历史感慨。郁达夫在《沉沦》等作品中写到知识者由于性的苦闷和生的苦闷而导致的沉沦,在贾平凹笔下的庄之蝶身上似乎也能发现,而郁达夫等人的“自叙传”小说体式,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张贤亮的创作中又一次得到印证,然而历史却经历了何等的沧桑巨变。叶圣陶笔下的灰色小人物,茅盾的《蚀》三部曲,巴金的《憩园》、《寒夜》,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十七年”时期的《红豆》、《青春之歌》,新时期王蒙、李国文、王小波等人的小说,都为我们奉献了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形象,足以构成一个深长的人物画廊。
女性形象体系同样摇曳多姿。“五四”文学对于女性的发现和第一代女作家灿若群星的集体亮相自不必说,第二个十年中莎菲女士的出现是重要征象。她的身上,理想与现实、灵与肉的冲突达于极致,个性自由浪潮冲击下的她,有摆不脱的孤独。她是中国式出走的娜拉,没有独立,只有苦闷。直到七十年后,一些年轻的女性主义写作者,仍然在回应丁玲的声音,现代当代的莎菲们依然活着。曹七巧、郭素娥、李香香、萧萧、虎妞、繁漪、田小娥、黑氏、陆文婷、冯晴岚、司绮纹、王琦瑶、吴为、玉米所有这些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著名女性都在某些方面存在基因和血缘的联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历史地发展着的人性决定,“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决不是单一地静止地,它是一条动态的不断发展、不断延伸的主线,从不自觉到自觉,从对国民性的发现到对现代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深沉思考,从较狭窄的视角走向宏阔的文化视野,它将伴随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而不断深化下去。
四、游离与回归——文学思潮的演变轨迹
从现代到当代,文学的口号之争、主义之争、流派之争、方法之争,不可胜数,从未间断过,它们都与其所处的特定时期思想文化背景的变幻,政治斗争和社会思潮的起伏密切相关。比如,人性与阶级性之争,就是一个贯穿题目,前有鲁迅与梁实秋之争,中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巴人的人性论的批判,上世纪八十年代则有人性与异化问题的大争论。再如,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也是贯穿始终的问题,早期有“左翼”与自由主义文学之争,上世纪四十年代《讲话》发表似乎廓清了是非,但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仍有隐蔽的争论,到七十年代末拨乱反正时有了对“工具论”的批判,八十年代观念革命时有“回到文学本身”的吁求,一直未曾停息。其他如主体论之争,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争,“大众化”与“化大众”之争等等。应该看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政治化思维起着决定作用,争论双方都过于重视对方的政治态度和立场,对于争论本身的文学性内涵和思潮性指向,却往往忽略。在今天,既然要以贯通的眼光来看,就应该突出文学思潮的激荡、演变和连续性,突出文学的规律性,不宜过多纠缠“左与右”、“敌与友”之类的是非——在时间的冲刷下,后者显然越来越缺乏吸引力了。
关于现代文学思潮,有学者指出,“五四”时期,“在当时发生重大影响的外来思潮都有一个‘中国化’的‘变形’过程。就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而言,现实主义特别是俄国现实主义影响最大,后来成为中国新文学主流;浪漫主义也有较大影响,但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而属于现代主义范围的各种思潮也曾吸引了许多作家,做了多种试验。”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第1页。事实上,西方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新起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并存于此一时期。当我们联系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太阳社、新月派等的相继出现,对此将有更深感触。当时,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兴盛,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略晚于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出现,但也辉煌一时,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则初露端倪。一些学者在描述三大文学思潮的演变轨迹时认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随着政治和文化氛围的变化,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出现了文学观的倾斜,导致了“拉普派”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误导,后经“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引进和对“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匡正,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潮;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由于“左”的文学观念的纷扰和社会关注重心的转向而趋于衰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这一时期一度鼎盛,在文学实绩上表现为新感觉派小说和现代诗派。
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现实主义文学依然是主潮,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进一步衰微,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则在悄然行进。其中,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中出现了抗战文学思潮的发展路径。刘增杰、赵福生、杜运通:《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关于当代文学思潮,一般认为,“十七年”时期,文学创作主要是沿着“左翼”文学的方向发展,带着从延安时期就大力倡导的“大众化”和“民族化”色彩;“文革”时期,“左”的倾向推到极致,出现了“文学激进思潮”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第181页、第158页。;新时期,文学思潮的演进次序分别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朦胧诗潮”、“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女性文学”等等。也有一些论著对当代文学思潮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梳理,把当代文艺思潮归纳为:本体论的、主体论的、生产论的、价值论的、人本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自然主义的、现代主义的、形式主义的、非理性主义的、新历史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文艺思潮等。陆贵山主编:《中国当代文艺思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这种梳理虽不无道理,但偏重横的排列,相对忽视了现当代文学思潮之间的内在连续性。
当我们强调回到文学本体,扣紧现当代文学思潮的内在关联性时,便可对现当代文学思潮的发展轨迹作如下描述:“五四”时期,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共同受制于有时代特色的社会思潮——启蒙主义和个性主义。启蒙主义主要强调对现实的正视与反映,个性主义主要强调张扬个性与主观精神,因此,这一时期可以简明地归结为启蒙主义和个性主义文学思潮。随着社会思潮的潮起潮落,文学思潮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发生变化,形成了三十年代新的文学格局与思潮:“左翼”文学思潮与“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并存。从1923年“革命文学”口号的提倡,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形成,到1930年“左联”的成立,标志着一种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为主导的文学思潮的出现和形成。由“五四”提倡个性解放到强调阶级意识,由重视个体意识到强调民族群体利益,由文学反映现实、表现情感到将文学纳入实际革命运动,“五四”开始的“文学革命”演变为“革命文学”即“左翼”文学思潮。对于“左翼”文学思潮,简单的肯定或否定或许容易,却有悖于历史主义的治史原则。
我们更愿意将它还原到当时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去重加认识,认为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中,在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中,在文学体现中国人的现代精神及其变化方面,“左翼”文学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毋庸讳言,“左翼”文学思潮在文学观念上强调实用目的性和社会功利性,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文学性的毁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思潮曾受到质疑与冲击,冲击来自于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产生、演变,持续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一种思潮。自由主义概念含有政治、思想、经济等不同层次上的含义,文学史上的“自由主义”主要体现为几个文学派别及其代表性人物的理论、创作的持续与演变,如现代评论派、新月派、论语派、“京派”、理论上的“自由人”、“第三种人”等,代表人物有胡适、周作人、梁实秋、朱光潜、沈从文等。从文学观看,他们强调文学表现人性与文学的个人性。他们的主张无疑具有合理性,但不可否认,在以救亡、革命、政治为中心意识的时代,必会遭受来自各方的压力和诟病。
纵观现当代文学,我们会发现,它经历了一个审美传统不断被打断,又不断被续接的过程,也即一个游离与回归不断交织的过程。我们之所以强调现、当代文学的一体性、贯通性,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有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为代表的几十位著名作家由“现代”跨进了“当代”,为延续自己的创作做出了近乎悲剧性的努力,这就奠定了现、当代贯通的生命基础,其中有丰富的教训值得总结。近有学者专门研究了处身当代的“郭沫若:中国歌德之道路”、“茅盾、老舍:‘现实主义’之困境”、“巴金和曹禺:激情主义之阻力”,研究他们何以放弃了“五四”以来长期形成的个人话语,而接受了流行的公众话语,作为“自由知识者”的精神日益弱化,何以在历史惯性的“同化”和“探索精神”终结的双重作用下,陷入了精神生活和文学创作的危机,从而提出“走进当代”的鲁郭茅巴老曹现象不单是文学现象,还是一个文化现象程光炜:《文化的转轨——“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现在看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近三十年间,文学被进一步规范化和观念化,于是出现了“政治意识形态化文学思潮”。这一文学思潮显然是“左翼文学思潮”在新的时代环境下的延伸和强化。在这一文学思潮的影响下,文学整体上失去了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把握,大量作品变成观念与政策的图解,导致作家创作个性的丧失和文学人文关怀的弱化。当然,每当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钳制有所松动时,文学创作又会短暂地繁荣。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是一个文学的大繁荣和文学价值重现的时期,可以称之为“文学的第二次解放”。这一时期“现实主义的回归”成为标志。“回归”是指文学回归到感性的、形象的、情感的审美本性上来。这一思潮带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分别包括伤痕——反思——改革等不同的文学倾向。从20世纪80年代初萌芽,在80年代中期之后蔚成风潮的是“文学向自身回归”思潮。这一思潮强调文学的规律性和艺术性,寻求文学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带有探索性和先锋姿态,表现于朦胧诗、实验话剧和先锋小说的实践。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以来,“世俗化、大众化文学思潮”成为醒目的现象。“世俗化”有意识地对过去奉为神圣的某些价值准则和盲目的准宗教式的情感进行消解,“大众化”解构文学创作上的先锋意识,强调文学对日常性、世俗化的生活的肯定和书写,对实用的大众文化的认同。
对现当代文学思潮史上脱离审美和回归审美的交替倾向,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曾就某一时段作过精当概括。即以当代文学来说,我们不妨绘出这样一幅波浪形的图式:1955年到1957年间,回到艺术;1958年到1960年间出现悖离;1961年到1963年间,再次回归;1964年到1977年间,出现了更大更长久的悖离;1978年到1982年间,完成本来意义上“革命现实主义”的回归;1983年到1989年间,大幅度回到审美,空前繁荣;1989年到1992年间,又出现短暂的脱离倾向;1993年以来,回归审美,旋即全面进入了市场化时代。
五、文体:在“西化”与“本土化”的碰撞中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