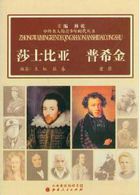“慢!”朱元璋又把侍从喊回来。“拣起来。”
侍从把奏章从地上拣起来,递到皇上的手上,朱元璋从头细细看了下李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欲说自图不轨,还犹可说。今说他欲佐胡惟腐,则令人难解。人之常情,爱自己的儿子,必过于兄弟之子。安享万全之富贵,必不侥幸取万一之富贵。李善长与胡惟席,不过是侄婧之亲,而与陛下,则是子女之亲。倘使李善长辅佐胡惟靡成功,不过是勋臣第一:太师、国公、封王而已,娶公主做岳翁而已,能过于今日之尊荣?况且,李善长岂不知天下不可侥幸而得,当元朝末年,欲为此者何限十百,哪个不是身为粉灰、宗祀绝灭,能保住脑袋的又有凡几?这都为李善长所亲见,何苦到了垂暮之年,去干那种蠢事?大凡奋而蹈险者,必有深仇大恨,万不得已,死里求生,以求脱祸于万一。今李善长之子,乃陛下骨肉之亲,无丝毫之嫌猜,何苦冒死而为此?功如李善长尚且如此,天下人难免不侧目,遂至人心解体!今李善长已死,言之无益,但愿陛下戒鉴于将来耳。
奏章讲得顺情入理,无可挑剔。朱元璋越发觉得,对李善长一家下手毒了些,愧对于同患难的良吏老友。但他立时又提醒自己不能上当。自古迄今,有雄才大略的帝王,有几个是妇人之仁?凡是开国君主,哪个容得下一同起事的弟兄比肩而立?而权倾朝野的大臣,哪个不是把国事搞得糜烂不堪?想到这里,他对自己的大刀阔斧,果断杀戮,不但心安理得,而且迁怒于王国用。这孽竖,竟想拿自己的耿忠,换取朝廷上下的礼赞,而把污水泼到朕躬头上,实在是可恨之极!他想立即下令逮捕王国用,但转念一想,该杀的早已杀掉,的已经达到,何不将纳谏容物的美名留给自己?于是,朱元璋不追究也不批驳,王国用逃脱了杀头之祸。
朱元璋当时没有料到的是,他这样做,实际上等于默认李善长有冤情。
胡惟庸,汪广洋,李善长,一个个从炙手可热的当朝一品宝座上滚下来,跟随着去了丰都城。在朱元璋的心目中,有一个人的形象越发高大灼目。这个人就是自己同样容不下的刘伯温。
初,对于中书省内部的鸡争狗斗,刘伯温心知肚明。他早就当面提醒过朱元璋,胡惟庸是一头会把车弄翻的“辕牛”。但朱元璋相信,自己有着足够的能力驾驭那头辕牛,并没有认真对待刘伯温的警告。等到威胁逼到头上,开始大抓胡党,才深深体会到老军师的先见之明。在这一点上,胡惟庸比他聪明,率先向刘伯温伸出魔掌。像揭发李善长,暴露了两人非同寻常的关系一样,胡惟庸对刘伯温的仇恨,暴露了自己的勃勃野心。牵连众多的胡党案,止是从追查刘基被害开始的。可见,大力张扬刘基的预见,不仅是惩治胡党的有力佐证,而且是争取舆论、安慰自己的妙招。
用之则取,用罢则舍,是朱元璋的一贯作风。他意识到,有必要再一次把胸怀坦荡、料事如神的老军师抬出来,为自己张目。
洪武二十年冬天,朱元璋传旨召见刘基次子刘璟。同时接见的,还有章溢的儿子章允载,叶琛的儿子叶永道,胡深的儿子胡伯机。
刘基、章溢、叶琛、宋濂,初来投靠时,被朱元璋尊为“四先生并专门建造“礼贤馆”隆重安置。那是何等的尊荣,何等的受到器重。如今,物是人非。三请方才出山的刘伯温早已被毒死,被李善长劝说出山的宋濂,蒙冤路上自缢身死。章溢、叶琛和胡深,原来都是地方武装的领兵元帅,带著全部人马投靠了朱元璋。胡深在进攻陈友定时被俘遇害。章溢患病而死,得到了善终。叶琛已老病缠身,气息奄奄,朝不虑夕。所以,朱元璋想用对耿忠文臣的优渥,来映照李善长、宋濂等“胡党”分子的忘恩负义、罪有应得。于是,他把隆盛的皇恩,施加到他们的儿子身上。他对四个垂手侍立的年轻人亲切地说道:
“你们的父亲,都是好秀才,好官儿。他们不但都没有受胡惟庸的蛊惑,刘伯温还早早看清了那厮脑后的反骨。可惜,他没能看到胡党殄灭。朕十分思念他们呀!”朱元球两眼殷红,一副伤感的样子。“尔后,你们每年冬天来京城朝见,都留下来过年,过完了年再回去。”
第二年,刘璟、章允载、胡伯机等来朝时,朱元璋再次当面谴责胡党。他愤慨地说道:
“刘伯温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有他一个人洁身自好,谁也不从。结果,吃他们蛊了。他的大儿子刘琏,那小子也厉害,始终不从奸党,也吃他们害了!如今,这群反臣,都被我除掉了,坟墓挖掘了,为你的父兄报了仇。”
“皇上的厚恩,微臣感激不尽!”倔犟的刘璟被感动得伏地痛哭。
洪武二十三年正月初,在京城过了年的刘璟等人,被召到奉天殿左暖房,再次受到皇帝的亲切接见。朱元璋不厌其烦地说:
“你们的老子,都是君子人。章溢是善善良良一个老儿,回家去好好的病死了。刘伯温父子两人,都被那歹臣胡惟庸害了。起初,我只道他是老病,原来是吃蛊了。提起那般奸党,朕的心头就疼,恨不得再杀他们几回!”
这年夏天,胡惟庸案再掀高峰,李善长被杀,牵进去近万人々朱元璋想用恢复刘家爵位,以证明圣明英睿的皇上,赏罚分明,不忘有功之臣。等到年末,刘璟进京朝贺万寿节时,朱元璋深情地对他说:
“当年我去婺州时,得了处州。那里东边有方国珍,南边有陈友谅,西边有张士诚。刘伯温挺身而出,来随着我。他的天文高明得很,别人只用秀才的理来断,他强于他们百倍。鄱阳湖里四处厮杀,他都有大功。后来,胡氏结党,他自洁不从,吃他下了蛊。有一天,他来和我说:‘陛下,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担谅着不好。’我着人送他回去,到家便死了。朕宣召刘琏来问,他说:‘父亲的肚子胀得紧紧的,后来又泻得瘪瘪的,就那样死了。’这正是着了蛊的症候。你大哥刘琏在江西做官,也吃他药杀了。
如今朕让你袭了你老子的爵——诚意伯,每年与你五百石俸禄。”
刘璟急忙跪到地上磕头说:“陛下皇恩浩荡。但万不可赏赐小人。”“哦,这是为什么?”
“小人的哥哥有儿子,应由臣的侄儿刘荐袭封诚意伯。”
朱元璋不由肃然起敬,一拍龙案说道:“咳!终究是秀才人家的孩儿,知孝悌,懂礼数,这么大的爵禄,竟让与哥哥的儿子。好呵!那就叫你的侄儿刘荐袭爵位吧。”朱元璋咧着大嘴笑了。“朕也与你个小职位儿,给朝廷办些事。你留在朕的身边,作随侍御驾阁门使。你也不要回青田去了,着家人捎封书子回去,向家里报喜就是。”
“谢陛下。”刘璟虽然极不情愿,也只得磕头谢恩。
皇帝一句话,刘家叔侄脱下布衣,摇身一变,成了官家人。明眼人都看得出,刘氏一门荣耀,与其说是皇上不忘旧臣生前的勋劳,不如说是为了映衬李善长、宋濂等人的罪不可恕。
李善长谋反案,是在胡惟庸通倭、通虏的背景下,罗织进去的。所涉及的既有文臣,也有武将。眼下,最为危险的文臣都被淸除掉,该腾出手来收拾那些出生入死打天下的武夫了。
“皇上呦!你当众说过:‘俺揣着一升麦子跟了你,南征北战,功勋卓著。’难道你把这些话都忘光啦?你还说,俺是最早跟了你的手足心腹,不忍心治俺的罪。这话你是当众说的,难道也忘了?俺可是从来忠于皇上,决没有跟着胡惟庸谋反那回事呀!俺咋就成了胡党、犯了大罪呢?你倒是再替俺说几句公道话呀!啊,啊,啊……”
撕肝裂肺般的哭喊声,从阴暗潮湿的大牢中传出来。犯人自从戌时开始哭喊,一个多时辰过去了,仍然一声高,一声低,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
这个哭喊的人,就是不久前朱元璋亲口为之辩护的吉安侯陆仲亨。他是今天傍晚,镣铐加身被押进大牢的。此刻,正跪伏在地上,满面涕泪,大哭大叫。
“皇上呀,你不替俺说话,俺死不瞑目呀!”
“不许喊叫!再不住口,当心拿大棒子敲你的狗嘴!”狱卒大声呵斥。
“你小子休得狗仗人势!俺是皇上亲口保过的人,你敢斥骂老子,当心你的狗头!你告诉那些歹毐的王八蛋,俺姓陆的是大功臣,大忠臣,他们抓错了人!”
“哼!死到临头还敢耍鸟威风,没有人听兔子叫!”狱卒不理不睬。
“他娘的,你敢骂皇上的心腹爱将,当心老了跟你算账。”陆仲亨已经控制不住自己。
犯官哭喊不止,狱头只得如实汇报上去。朱元璋一听,冷笑道:“告诉那恶棍,仅凭他进了大牢所说的话,也够死上几回的!”
果然,陆仲亨的哭天喊地、大叫冤屈,不但没有感动皇帝,还加速了自己的死亡。两天后,便被悄悄砍了头。
陆仲亨之死,为整肃勋臣武将这出闹剧,拉开了序幕。凡是与李善长、胡惟庸,以及两人的亲戚故旧,有过来往的将帅,相继成了“胡党”或者“胡党的羽翼”。短短几个月内,被处死的有功武将,就有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河南侯陆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已经死去但仍然被追成“胡党”的,有淮安侯华云龙,宣德侯金朝兴,济宁侯顾时,靖海侯吴祯,永城侯薛显,临江侯陈德,巩昌侯郭兴,六安侯王志,汝南侯梅思祖,营阳侯杨璟,南安侯余通源,申国公邓镇(大将邓愈之子),以及大将毛骧,李伯昇,耿忠,于显,丁玉,于琥父子等近三十余人。
特别引起朝野惊诧的是,被处死的陆仲亨、唐胜宗、吴祯、陈德、顾时、华云龙、郑遇春、郭兴、费聚等九位封侯的武将,不仅是朱元璋的同乡,而且是朱元璋南略定远时,二十四员骨干中的铁杆弟兄。其余被杀的,也绝大部分都是渡江以前的老部下。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这句流传许久的古语,不只是对功成杀勋惨象的谴责,也是对开国君臣关系的准确概括。自春秋战国以来,时光推移数千年,无数朝代更替,尽管形式与程度有差异,但几乎代代如此。这不单单是个道德良心问题,而是关系到皇权巩固的百年大计。至高无上的皇帝,岂能允许他人分享自己的权力?而功高势大的权相、勋臣,甚至后妃、外戚、身边的太监,都是觊觎皇权的罪恶势力。这怎能不使皇帝枕席难安、忧思萦怀?历史知识已经很丰富的朱元璋,更懂得权臣的能量与危险。难怪,早在立国之初,他就制定了禁止后妃、太监干政的条规。他曾当面阐述过这样做的理由:
“治天下者,修身为本,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使预政事,至于嫔嫱之厲,不过备执事,侍巾栉,若宠之太过,则骄恣犯分,上下失序。观历代宫阃,政由内出,鲜有不为祸乱者也。”
说罢,他命在座的老儒朱升,纂述一部《女诫》,诫谕宫阃,严防后妃干政。
洪武二年八月,又制定了内官(宦官)编制规则。《规则》明确写道:“自古以来,此辈求其善良者,千百中不见一二。若用以为耳目,即耳目蔽矣;以为腹心,则腹心病矣。驭之之道,但常诫敕。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则骄恣,畏法则检束,检束则不敢为非也。”
发布《规则》之外,朱元璋还命令在宮门口树立铁牌,上书“太监不准干政”,以达到时刻警诫的目的。
后妃、太监,都是皇帝家族成员,恩宠太过,他们便有了擅权干政的本钱。因此,需要严立章法,予以约束和震慑,让他们乖乖地就范。而对勋臣武将却不是这么简单。他们既是新王朝的开拓者,又是新皇帝的支撑者、保卫者和拥戴者。兔死狗烹,削而弱之,虽然是皇权的极端霈要,但不能操之过急,不能下一道饬令,统统罢黜甚至杀掉。暂时留谁,先烹哪个,不但要根据需要,还得找到名正言顺的口实。瞒大过海,只能遮人耳目,找到名正言顺的口实,才能消除良心的谴责。万一弄巧成拙,不仅有损于神聪颖锐真龙天子的光辉形象,还怕激起变故。胡惟庸专权跋扈,人所共知。杀其头,甚而烹其肉,无人敢于腹诽。某些武将勋臣,腐化贪暴,有案可稽,进行严厉的惩治,也无人敢于置喙。而像宋濂、汪广洋、陆仲亨、唐胜宗、华云龙、郑遇春等文臣武将,一向耿忠谨慎,没有辫子可抓,除了加上“奸党”的罪名,就只有向“谋反”、“通寇”等罪名求救。总之,只要他们的名声太响亮,身上的权势欲有所膨胀,对皇上的威名、皇家的权力构成威胁,就是陷人了罪恶的渊薮,就等于犯罪!
这就是朱皇帝的逻辑。他绝不能听任那些手握重兵的枭雄们,对阜。权虎视眈眈!
朱元璋生平最为赞赏的,就是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不流一滴血,便达到了目的。干得多么高明漂亮。他曾打算把功臣武将统统安置到他的老家凤阳,使他们远离权力中心。转念一想不妥。那么多的淮西勋旧、赳赳武夫聚在一起,不是同样十分危险吗?
看来,罗织罪名、大兴冤狱才是惟一妥当的法子。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自己已经拥有、而为他人所觊觎的一切!
战争可以分割权力与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