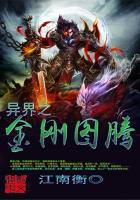这种来自“下层”的“新人”对“旧文化人”的“嫉恨”,代表了一个受压迫的阶级或阶层对统治阶级的思想情绪。这种“嫉恨”的情绪必然传染给与这个阶层和阶级有着同样境遇的人们,并在他们思想中引起广泛共鸣。如果没有高瞻远瞩的伟大领袖人物的博大胸怀和气度,没有分辨秋毫的敏锐洞察力,是不可能克服这种情绪,也不可能充分认识其危害性的。实际上,这是把对整个统治阶级及其一小撮“妄自尊大”、“趾高气扬”,总是想“侮辱、欺负和压迫别人”的人的怨恨情绪,迁怒到了“文化人”身上,并且由迁怒“文化人”进而迁怒于以他们为载体的文化;下面在谈到民粹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反文化倾向”时,我们将会看到这种情况。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来自“下层”的“新人”,即平民出身的民粹派知识分子有这种思想情绪;下层的广大民众因其文化低下,受欺凌压榨之深,更有甚于这些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在他们身上不可避免会更强烈地表现出这种思想情绪来。他们也必然会把这种思想情绪传达给来自下层的政治的和文化的代表,这些代表把民粹派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的这种思想情绪加以汇聚和集中,就会变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由思潮再转化为某种政策而加诸“文化人”身上。所以,在文化落后的农民国家,特别在农民革命过程中,一般总处理不好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其最深根源即在于此。
二、反对文化崇拜,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文化同民粹主义对待“旧文化人”的态度相联系,民粹派对待一般文化也表现出了某种偏激情绪,即对文化持过多否定或全盘否定的虚无主义态度。在民粹主义产生初期和它出现以后的相当时期,俄国并不存在“民粹主义”这一用语。最初被称为“虚无主义者”的人,就指的是民粹主义者。我们最早见到这样称呼民粹主义者的,是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父与子》(1861年)。作品的主人公,一个下级军医的儿子巴折洛夫,就被他的朋友和追随者阿尔卡季称作“虚无主义者”。阿尔卡季在向他的伯父帕维尔·彼得罗维奇,一个自由主义贵族的代表人物,介绍自己朋友并解释“虚无主义者”时说,虚无主义者就是“一个用批评的观点对待一切的人”,也是“不向任何权威折腰的人,他不把任何原则当作信仰,不管这些原则怎样受到广泛的尊敬”。屠格涅夫著,张铁夫等译:《父与子》,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24页。在解释“虚无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时,小说还通过这个自由主义贵族的口说道,这种人“以前是黑格尔主义者,而现在却是虚无主义者”。以前苏联和我国学术界在评论《父与子》的主人公巴折洛夫时,大多认为屠格涅夫是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歪曲了这个平民知识分子,就是说,歪曲了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民粹主义刚刚产生时期的这个民粹主义知识分子的形象。当然,严格地说,由于阶级立场和思想的局限,作家屠格涅夫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这个问题的;但屠格涅夫作为一个冷静的、严格的、天才的现实主义作家,对这个民粹主义知识分子形象的刻画是相当真实的。说其刻画真实,原因有二:一是屠格涅夫熟悉这个类型的知识分子,他同他们有过相当接触,了解他们,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同情他们的;二是,从上述我们提到的拉甫罗夫对具有批判思维的知识分子的评述中,也可看到这类所谓“虚无主义者”所具有的“用批评的观点对待一切”的思想特征,这同现实主义作家屠格涅夫笔下的巴折洛夫的思想性格是相符合的。
另外,我们可以把巴折洛夫仅肯定具体的自然科学,否定哲学、艺术、音乐、绘画等等屠格涅夫著,张铁夫等译:《父与子》,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28—57页。,同民粹主义的文件《革命者基本信条》中所说的一段话——“革命者鄙视任何学理空谈,在给未来几代人提供知识时,……他只知道一种学问,就是破坏的科学。为此也仅仅为此,他现在研究机械学、物理学、化学,还应有医学”《苦役与流放》杂志1931年第4期(77),第56—57页。——加以对照;也可以再同俄国哲学家和思想史学者别尔嘉耶夫、弗兰克提供的民粹主义者对待科学和艺术、哲学的态度加以对比,都可以看出,这三者提供的情况基本相符。况且,一部民粹主义思想的历史也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皮萨列夫式的人物,他作为虚无主义的代表,也认同可以从屠格涅夫塑造的巴折洛夫身上看出他们一代人的“容貌”;Л。普洛特金著,高惠群译:《皮萨列夫》,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75页。这也给我们提供了具体的历史证据。所以,我们认为,说民粹主义的特定派别对文化艺术持虚无主义态度,是基本符合历史真实的。
民粹主义对文化艺术持虚无主义态度,反对文化崇拜,其动机一方面犹如上面所述,是由于文化本身是靠着人民的血汗和苦难,靠着对人民的剥削而获得的,这样,掌握文化就似乎同剥削、同罪孽联系到了一块儿。所以在民粹派看来,文化本身仿佛也沾染上了剥削和罪孽的味道。因此,民粹主义思想经常对文化报以轻蔑甚至敌视态度,“在任何条件下都会起来反对文化崇拜”。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第58页。另一方面,这也同他们对文化的极端功利主义态度有关,这一点在下面将会谈到。
民粹派反对文化崇拜,其重要表现之一,是瞧不起甚至鄙视传统的大学。他们因为大学“同外界隔绝、脱离人民生活”而对它加以批判。至于对大学教授,则认为人民因他们“从事抽象理论”而对其不加信任。民粹派在某种意义上把知识分子同官吏划上等号,认为“大部分教授是官吏”,因而对他们加以排斥。民粹派主张“把大学教育思想灌输到民间去”,在他们看来,“星期日学校大都是培养大学生的苗圃”。阿·普·夏波夫:《村社》,摘自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第32—33页。
否定大学教育是民粹主义,特别是无政府主义的一个突出特征。彼·阿·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都曾抱有这样的思想。克鲁泡特金甚至说,“必须关闭一切大学、学院和其他高等学校”,“我们不需要为少数人建立的大学、技术学校和海军学院”;“我们需要”的,只是“医院、工厂、化学企业、船只、生产作坊和工人学校,工人学校一旦成为不可或缺的东西,便将以难以想象的速度超过现有的大学和学院的水平”。彼·阿·克鲁泡特金:《我们是否应该研究未来制度的理想》,摘自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第272、273页。
巴枯宁宣称实际斗争就是“科学”,他也号召青年“抛弃这些大学、学院和学校”,说什么,这些学校“总是力图使你们脱离人民”;号召青年“不要在科学上煞费苦心了”;“到民间去吧!你们的战场,你们的生活和你们的科学就在那里”。巴枯宁:《告俄国青年兄弟的几句话》,摘自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第52页。
我们知道。无政府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潮流中的一个重要派别;而这个思想流派在俄国民粹主义各个流派中以巴枯宁为代表,又在相当时期内占据着主导地位,具有压倒性的影响力。所以,无政府主义对待教育和科学的这种态度,对于俄国民粹主义来说,是相当典型的。
三、以道德主义为评价精神文化的最高标准
别尔嘉耶夫认为,俄罗斯知识分子具有一种所谓“一切从属于政治的世界观”;又说,“俄罗斯民粹派的心灵是道德化的,它对世间的一切都采用特殊的道德评价”。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页。他和弗兰克都认为,民粹派遵循的是“道德主义”;这种道德主义“要求个人的严格的自我牺牲和私人利益(虽然是最高的和最纯粹的)对社会事业的绝对服从”。同上;亦见弗兰克著,徐凤林译:《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第56页。
这里实际上指出的是,民粹主义奉行的是道德—政治价值至上,而让科学真理和文化价值服从于他们的道德—政治价值。
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似乎任何阶级、任何政党在处理政治与科学、政治与文化的关系时,实行的都是政治—道德标准第一,科学和文化价值标准第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科学真理是客观的,一般来说纯粹的文化价值也是客观的,比如莎士比亚悲剧引起的艺术美感,无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都能加以欣赏,这就表明它是客观的,不能因为各个阶级、政党的政治—道德标准不同而对此加以否定。但民粹主义正是从极端革命主义出发,以其纯主观的政治—道德标准否定科学和文化标准。
实际上,对于尊重科学真理和纯文化价值的科学中立主义者或不问政治的文化中立主义者,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应该允许他们存在的,因为科学和文化的最高价值标准之一,是不能发生继承性中断,这就要求承认其生存承续和发展的合理性。极而言之,像气象的测量,在什么时候也不应中断,否则,事过境迁以后,是无论如何也弥补不上去的。而如果按照民粹主义的说法,“当社会现有的全部力量都必须用来解决各种迫切的实际问题时”,“社会上任何一个对这些问题不关心的成员都是社会的敌人”;而只要对“迫切的现实问题”采取“冷淡主义”,“逃避参加解决这些问题”的的,就被认为“将是一种反动因素”,彼·拉·拉甫罗夫:《历史信札·第九封信》,摘自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第116页。这种不允许科学文化界有中立主义存在的做法,无疑将造成科学和文化的中断,妨害它们的发展。其实,民粹主义在其《革命者基本信条》中宣布的——对革命者来说,“凡能促使革命胜利的一切,都是道德的。凡妨碍革命取得胜利的一切,都是不道德的和罪恶的”《苦役与流放》杂志1931年第4期(77),第56—57页。——正是这种极端主义的东西。在这里,科学文化的中立主义实际上已被他们宣布为“妨碍革命”,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和罪恶的”。
按照民粹主义的原则,一切科学建制,包括一切科学家和文化人,所有专家和学者,都必须“把自己的才能、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精力用来解决迫切的现实问题”,而将自己的研究“摆在次要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几何学新领域的开拓者蒙日就会整天在作坊中度日,啃干面包,给工人书写指示。在这种情况下,参加创立化学科学的贝多莱和富尔克鲁就会献身于硝石的采掘和对农人出身的矿工的训练。在这种情况下,比较语言学的首创者威廉洪波尔特就会把自己的全部智慧用于普鲁士的复兴。”天文学家、细胞学家,总之,一切科学家、文化人都应该投身政治,否则,他们“著作的全部科学价值就不能使它逃脱历史的必然的宣判:……将是一种反动因素,而不是进步因素”。彼·拉·拉甫罗夫:《历史信札·第九封信》,摘自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第116页。
由于受到这种政治—道德价值至上论的影响,到苏俄时期,托洛茨基在《文化与革命》一书中就文化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提出了实质上是“政治标准第一,文化标准第二”的口号。托洛茨基著,刘文飞等译:《文学与革命》,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6页。也正是受这种影响,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宁愿相信李森科“春化小麦实验”的伪科学,也不愿相信生物遗传学的科学真理。所有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受民粹主义文化观影响的结果。
四、对科学和文化的极端功利主义态度
有关民粹主义在科学和文化上的极端功利主义,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通过巴折洛夫同自由主义贵族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的一段辩论,作了通俗易懂而又集中的概括。巴折洛夫在辩论中说:“我们行动的根据就是我们认为有益的那些东西”——“在目前情况下最有益的就是否定——于是我们便否定。”
自由主义贵族巴维尔问:“‘否定一切吗?’”
巴折洛夫坚定地回答:“‘否定一切。’”屠格涅夫著,张铁夫等译:《父与子》,第56—57页。
这段对话异常精练集中地把民粹派的功利主义和虚无主义及其相互关系,作了概括的阐明。民粹主义的行动准则就是对事业“有益”二字,既对实现革命的近期任务“有益”,也对解决目前迫切的现实问题“有益”。
应该说任何阶级、阶层、政党和社会集团都有其一定的功利主义,因此,不能不作分析地一概否定功利主义。但功利主义不能编狭,不能走向极端。只顾对眼前“有益”,而不从长远需要考虑;一味追求急功近利,而不管全体人民、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利益和福祉,就是狭隘的极端的功利主义。而民粹主义奉行的就是这种急功近利的极端的功利主义。
出于对目前迫切的现实问题“有益”的考虑,彼·阿·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都一致认为,不需要“为少数人建立的”、“脱离人民”的大学。克鲁泡特金认为,需要的是“用社会资金普遍开设学校—工场,这种学校—工场很快就能包括现在大学的教学,当然也一定能发展到现在大学的水平,并且能超过它们”。彼·阿·克鲁泡特金:《我们是否应该研究未来制度的理想》,摘自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第272、273页。
因为从只对实际生活“有益”的角度考虑、并且仅仅出于实用目的,民粹派“主要对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学感兴趣”。别尔嘉耶夫著,邱运华、吴学金译:《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第129—130页。60年代著名的虚无主义者皮萨列夫,主张“能思维的现实主义者”,即指民粹派,应“崇尚务实、劳动”。因此,他“只承认自然科学,鄙视人文科学”。同上,第52页。正基于此,民粹主义革命急进派在其纲领性文件《革命者基本信条》中规定:革命者“只知道一种学问,就是破坏的科学。为此也仅仅为此,他们现在研究机械学、物理学、化学,还应有医学。为此,他们夜以继日地研究人世间的活学问,日夜钻研当前社会制度所有可能层面上的特点、形势和条件。但目的是一个,就是最快地、最坚决地破坏这个可恶的制度”。《苦役与流放》杂志1931年第4期(77),第56—57页。
民粹主义在科学和文化上的极端功利主义,是同他们文化观的虚无主义和道德主义(或者说政治—道德价值至上)联系在一块的。出于对科学和文化艺术的极端功利主义,他们宣称只需要实用的东西,而对抽象的学理性之类的学问(如哲学、美学等),纯艺术性的高雅的作品,如莎士比亚、普希金等,都一概予以否定。实用的具体的自然科学,和立竿见影的工艺性的技术,被他们看作是“有益的”,而哲学、艺术、美学之类,则被视为“贵族式的”奢侈品,这种对待文化的态度,必然导致文化虚无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