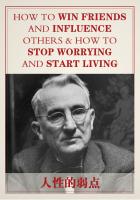张小凤
父亲给了我一台旧相机,因为订报送了一台新的相机,所以旧的就给我拍着玩,这个相机原来是用来拍摄外伤伤口的。记得有一天的中午,午餐是大块的烤肉。“嘟……”对讲机响,“叶青你下来一下。”我抹了抹嘴边的油腻,到楼下的诊所。
是外伤,一个穿蓝色工作服的男子,侧躺在缝合台上,手臂上一道深深的切伤,两边的肉都已绽开,父亲已准备好要缝合了,一旁和我年纪相仿的小护士,对我微微地笑着:“相机拿好,对伤口拍一张相。”爸爸很平常地说着,弯弯的缝针已穿过分离的两片肉,小护士还是微微地笑着,一边递出止血的棉片。我慢慢地对准伤口,突然想到中午的烤肉,两片裂开的肉倒像一个张得大大的嘴,深不见底,我仿佛看见这个伤口真的笑了,嘴巴张得好大,而血就从这里汩汩流出。
我还记得伤口的主人脸上尴尬的表情,这是那天的情形,对我而言像是触动了童年的记忆。宽阔的大地从来就不是儿时的嬉戏场,如同血腥战场的急诊室,却是我饱尝窥视快感的乐园,记忆中咸咸湿湿的气味,孩童因疼痛所发出的尖锐哭叫已深深烙在嗅觉与听觉印象里。我站在父亲的身后看到别人椎心的疼痛。在这充满封闭与禁忌的场所里,我度过大部分的童年。惟一未入眼帘的是手术室里更露骨的战斗,微黄的玻璃背后是永远的秘密,也是刺激偷窥欲望的原动力,那道门里,始终藏着更大的秘密,我却怎么也无法逾越。
在一次激烈呕吐后,我结束了我童年的“观血经历”,最近读到傅科(Michel Foucault)的传记,其中有一段是描述傅科小时候由做外科医生的父亲领着,观看一次截肢手术,为的是培养他的阳刚之气。小时候的观血经历,有没有培养我的阳刚之气,我不得而知,只是对伤口的深刻感触,影响了我对许多事物的看法。
尖锐的环境,复杂的人事,在人与人摩肩接踵之际,总历历地留下伤口,流血不止,痛彻心肺。在复原的过程中,伤口若真能微笑,就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释然与宽恕吧,在椎心的疼痛后,学习愈合,学习成长。在每一次微笑的伤口中,累积生命的智慧,历练生命的坚韧。小贩抬头看了看我,有点歪斜的脸上露出自傲的神情,那一刻,我看到了“人”的骨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