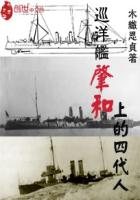只有提出人的所谓“高级生活”和人类进化问题时,与以手段为中心的科学家的冲突才开始出现。如果你是在研究狗和猴子的行为,或是在做学习、条件作用和激发行为的实验,现有的手段论工具对我就很适用了。这些实验能适当地设计出来并加以控制,论据也可以很精确,而且很有效。
只有对研究者开始提出新的问题时,提出不能有效处理的问题时,或是关于含糊不清而难以把握的课题提出疑问时,我们才陷入真正的困境。毫无疑问,许多科学家这时会轻视他们不能对付的、不能有效解决的问题。
马斯洛曾说出这样一句警语:“不值得做的事情是不值得做好的。”现在还可以附加一句:“需要做的事情是值得做的,即使不能做得很好。”
的确,研究一个新问题的初步尝试大都是粗糙的、不精密的、低级的、不成熟的。从这些初步的尝试中你通常能学会下一次该怎样做才能做得更好。
当然,要跳过这个初步是不可能的。记得有一个孩子,当他听说列车事故中大多是最后一节车厢遭殃时,为了减少事故,他竟建议把最后的车厢摘除!
显然,开端是不能被摘掉的,甚至这样想和这样要求本身也是对科学精神的一种否定。动手打开新的领域当然是更令人兴奋、更有价值的,也是更有益于社会的。“你应该热爱问题本身。”莱尔克说。科学的突击部队当然比科学的宪兵更为科学所需要。前者即使很容易弄得更龌龊,并要承担更高的伤亡率,但仍然比后者重要。
二次大战期间,比尔·毛尔丁的漫画对于前线战斗的士兵和后方梯队仪容整洁的军官之间的价值冲突是很精彩的写照。在一定的特殊情况下,必须有一个人首先穿过精神坑道领域。
当马斯洛的精神病理学工作引导他探索非病理学时,也就是研究心理健康的人时,他遇见了过去从来没有的难题,例如,价值和标准的问题。实际上,健康本身就是一个规范词。
于是,马斯洛开始理解为什么在这方面一直很少作为。就“正规”研究的正规准则而论,这不是一种好的研究。实际上他并不称之为一种研究,而是一种探索。它很容易受到批评,马斯洛也曾批评过它。
马斯洛怀疑自己的价值观念是否会闯入他所选择的研究对象中。当然,有一组裁判员会更好些。我们目前已有的一些测验比任何过去独自做出的判断都更客观而无偏袒,但在1935年这样的测验是不存在的,那时不独自做就根本别做。如果你选择了“做”,你将会学到很多东西。不过,还有很多人选择了“做”,当然也学到了很多。
通过对这些相对健康的人和他们的特征的研究,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科学家,都使我打开了眼界——看到了成打的新问题,不再满足于我过去认为理所当然的旧答案、旧方法和旧概念。这些人引起的新问题有:什么是正常、健康、善良、创造性和爱?什么是高级需要、美、好奇、完成?什么是人中豪杰和神圣的品质?什么是利他主义和合作、爱护的弱、同情和不自私和仁慈?什么是伟大、超越的经验、高级的价值?
当马斯洛注意到这些他一直在进行有关研究的问题,他认为有可能对于回答这些问题做出某些贡献。它们并不是不能验证的,更不可能是“不科学的”问题。
人的“高级”心理过程不会那么适度而又安然地嵌入机器的运转,从而产生可靠的知识。这部机器原来很象厨房里曾被称之为“万能器”的东西,但它并不能真正对付所有的原料,而只能有几项用途。
或者换一个马斯洛说过的例子:“我看见过一部精巧而复杂的自动洗车机,能把汽车刷洗得很干净。但它只能做这样一件事,任何别的东西进入它的掌握都只能象一部汽车那样接受洗刷。我设想,假如你所有的唯一工具是锤子,那就会诱使你把每一件东西都作为钉子来对待。”
简而言之,你如果不想放弃你的问题,就只有想出新的方法解答这些问题。许多心理学家选择了这条路,他们宁愿竭尽自己的所能去研究重要的问题——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限制自己只做那些他们能够以现有技术漂亮完成的事——以手段为中心。马斯洛也是如此。
假如你把“科学”定义为有能力去做的事,暂时没有能力去做的事就变成“非科学”的了。很显然,这项假设是完全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