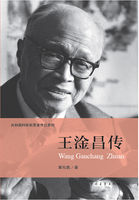重耳正在沐浴,曹共公领着他的幸臣、爱妾、侍女一群人,闯进浴室,要看重耳的骈胁,把个重耳羞得无地自容。
宋襄公见重耳执意要去,以马车、美姬相赠。然那美姬,早已有了心上人儿,且又偷吃了禁果。
楚文王打败仗归来,管城门的官儿硬是不让他入城,他不止忍了,还掉转马头,向敌阵冲去。
重耳怪狐偃用计劫他,夺魏犫之戈以刺偃,偃闪身避过。重耳举戈又刺,偃慌忙逃之,重耳持戈追之。赵衰、先轸、介子推等一齐上前劝阻:“公子,狐偃此为,真的是为您好?”
重耳投戈于地,恨恨不已。
狐偃上前叩首请罪曰:“杀偃以成公子,偃死愈于生矣!”
重耳曰:“此行有成则已,如无所成,吾必食舅氏之肉!”
狐偃笑而答曰:“事若不成,偃不知死在何处,焉得与子食之?如若有成,子当列鼎而食,偃肉腥臊,何足食?”
赵衰趋前两步说道:“吾等以公子负大有为之志,故舍骨肉,弃乡里,奔走道途,相随不舍,亦望垂功名于竹帛耳。今夷吾无道,国人孰不愿拥戴公子为君?公子自不求入,谁走齐国而迎公子者?今日之事,实出吾等公议,非偃一人之谋,公子要杀,索性连吾等一齐杀了吧!”
魏犫亦厉声曰:“大丈夫当努力成名,声播后世。奈何恋恋儿女目前之乐,而不思终身之计耶?况且,要恋目前之乐,吾等在齐,谁没有妻室?”众雄初入齐时,齐桓公为安定众心,为他们各娶一房妻室,内中最贤者当推赵衰之妻——赵姬,且为赵衰育有三个儿子。
经他二人这么一嚷,重耳犹如醍醐灌顶,幡然醒悟。忙改容说道:“吾吃多了酒,说话颠三倒四,请尔等见谅!”说毕,深深作了一揖。
这一揖,把众难的一腔怨气,满腹忧愁,尽行逐去,异口同声道:“这才是吾等的主人!”
狐毛见重耳消了气,忙道:“该早朝矣。”一边说一边取出干饭以献,介子推亦捧水以进。
重耳曰:“奔波了一夜,一定很饥了,要吃,大家一块儿吃吧。”
众雄应了一声,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壹叔不能吃,他还要割草喂马。不能吃的不止壹叔。此番出走,已不比在翟,有备而出,随从一大帮,足有三十余人,或刷车、或割草、或喂马。
待壹叔等人用过早餐,众雄便催赶车马上路,晓行夜宿,不一日来到曹国。
曹国国君曹共公,特好游戏,不理朝政,亲小人,远君子,以谀佞之人为心腹,视爵位如粪土,某一日朝会,一下子封士二百余人,皆是里巷市井之徒,胁肩谄笑之辈。有此等之人把持朝政,还有豪杰贤者立足的地方吗?
重耳不只是贤者,还是大贤者,不说狐偃这一帮子豪杰了。俗话说得好,“薰莸不同器。”这一帮子奸佞小人,得知重耳一行到了曹国,唯恐久留不去,纷纷去见曹共公,不只说重耳的坏话,还拿晋惠公来威胁曹共公,说什么晋惠公说了,谁敢收留重耳,谁就是寡人的仇人!寡人将兵戎与之相见。
唯有大夫僖负羁,站出来为重耳说话:“主公,别听他们瞎嚷嚷。晋、曹同姓,公子穷困而过我,宜厚礼之。”
曹公共曰:“不是寡人不愿接待重耳,寡人有寡人的苦衷。”
负羁曰:“苦衷者何?”
曹共公曰:“曹,小国也。不只小,而且穷,又居列国之中,子弟往来,何国无之?若一一待之以礼,则国微费重,何以支撑?”
负羁曰:“晋公子贤德闻于天下,且重瞳骈胁,大贵之征,不可以寻常子弟视也。”
曹共公曰:“好,依卿之见,咱不以寻常子弟视重耳。然,晋惠公有言,谁纳重耳,他将兵戎相见,咱何苦来呢!”
负羁曰:“晋惠公即位以来,晋国无有宁岁,他自顾尚且不暇,何力顾及他人?况且,齐纳重耳七年,未见他片言相责,更不说兵戎相见的话了!”
曹共公良久无语——负羁还以为他答应了呢——突然迸出一句话来:“卿说重耳重瞳骈胁,重瞳寡人知之,未知骈胁如何?”
负羁对曰:“骈者,双也。胁者,肋骨也。肋骨连在一块,称为骈胁。”
曹共公笑曰:“人的肋骨都是一根一根的,卿骗谁呀?”
负羁曰:“世人都这么说,主公不信,臣也没有办法。”
曹共公曰:“有道是,‘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一个人,若是肋骨真的连在一起,挺好玩的,可将他暂迎馆中,俟其沐浴之时,寡人要一睹真假。”
负羁曰:“不行,不行。这是人的隐私,看了不好。”
曹共公不想和他纠缠,佯装应道:“好,寡人不看了,寡人这就遣使迎重耳入馆。”
曹共公果真遣使将重耳迎进驿馆。古礼,凡列国子弟往来于某一国家,某国便要有所馈赠,大到牲畜、小到布帛,还要设宴相款。曹共公不这么干,仅以粗饭相待,气得重耳将筷子摔到地上,经狐偃、赵衰反复劝说,勉强吃了半碗。
古时的旅店,不同今日之旅店,只供一张蓆,被褥之类,是客人自带,根本没有沐浴——也叫洗澡的设施。驿馆有,驿馆就相当于现在的国宾馆。
自齐到曹,少说也有七八天的路程,七八天没有洗澡,又是一路风尘,用过晚餐,当务之急便是洗澡。
重耳正洗着,曹共公领着幸臣、爱妾、侍女一群人,闯进浴室,要看重耳的骈胁,把个重耳羞得无地自容,赶忙抓了一件衣服,捂住私处。
一爱妾笑嘻嘻地说道:“亏汝还是一个男人呢,看一眼能把汝吃了不成?”
幸臣强行摸了摸重耳的肋骨大声叫道:“那肋骨确实是连在一起的。”
爱妾笑道:“俺不信。”
幸臣道:“不信汝可以摸呀。”
爱妾果真朝重耳肋骨摸去,重耳急闪,另一侍女乘机摸了一下重耳肋骨,惊叫一声道:“果真是连在一起的!”
重耳恼羞成怒,大声嚷道:“尔等如此无理,小心吾去曹共公那里告尔!”
爱妾一边指着曹共公,一边格格娇笑道:“汝睁大眼睛看一看他是何人?”
重耳举目望去,见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壮汉,宽面大耳,心中暗自思道:“难道他就是曹共公?”正要开口询问,狐偃、赵衰等人赶了过来。他们也不认识曹共公,大声责问道:“尔等这是干什么?”
幸臣回道:“吾等不想干什么,吾等只想看一看重耳是不是骈胁。”
狐偃强压怒火道:“尔等此为,能是待客之道?”
一爱妾嘴一撇道:“小样儿,不让看算了,俺们走。”
曹共公将手一挥道:“走!”
待曹共公离去,狐偃向一守馆之人问道:“刚才那一帮子都是何人?”
馆人道:“是吾国国君和他的爱妾、幸臣,还有侍女。”
重耳右手成拳,朝左掌心狠狠砸了一下说道:“欺人太甚!吾若是……”
狐偃抢前一步,将他的嘴巴捂住。
重耳虽说将下半截的话咽回肚去,心中恨恨不已。
负羁也在暗自生气,归到家中,其妻吕氏迎之,见其面有愠色,问之曰:“朝中出了什么事儿?”
负羁道:“朝中没有出什么事儿。”
吕氏道:“朝中没有出事,汝为何面有愠色?”
负羁道:“吾恨共公耳!”
吕氏道:“共公为汝君,何恨之有?”
负羁道:“晋公子重耳过曹,主公不以为礼,吾劝之口头从之,然又率爱妾、幸臣、侍女,观重耳沐浴,堂堂一国之君,做出此等之事,吾深以为耻!”
吕氏道:“君说的是晋公子重耳吧?”
负羁道:“正是。”
吕氏道:“那可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负羁道:“汝认识重耳?”
吕氏道:“不认识。”
负羁道:“既然不认识,汝怎知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吕氏道:“今下午,妾在郊外采桑,正值晋公子车骑从此路过,妾暗自窥之,但见晋公子仪表堂堂。从行之人,一个个豪气冲天,皆非凡人。吾闻‘有其君,必有其臣;有其臣者,必有其君。’以从行诸子观之,晋公子必能光复晋国。今受其辱,一旦光复晋国,必要兴兵伐曹,玉石俱焚,悔之无及。曹君既不听子之忠言,子当私自结纳可也。妾已备下美酒一坛,细食五盒,并藏白璧于食盒之中,以为贽见之礼。结交在未遇之先,子宜速往。”
负羁由衷赞道:“夫人之智不让须眉,吾这就去拜访重耳。”言毕,微服轻车,来到驿馆,向阍者说明来意,阍者又告重耳。重耳晚饭没有吃好,饥肠辘辘,又受曹共公奚弄,含怒而坐,闻曹大夫负羁求见馈食,忙道:“有请。”
负羁见了重耳,一揖到地:“臣之主公生性诙谐,不拘小节,待公子不当之处,责在小臣,请公子谅之。”说毕,又是三揖。
重耳故作大度道:“小事一桩,吾早已忘到九霄云外了。”
负羁将话锋一转说道:“公子名显列国,世人无不以一睹公子尊容为快,公子屈驾曹国,乃曹人之幸,外臣特备美酒一坛,细食五盒,以飨公子,请公子勿辞为盼!”
不只说得好,又有美酒佳肴,重耳如何不喜?叹曰:“不意曹国,竟有此等贤臣!亡人幸而返国,当以千倍相报。”
说毕,揭开食盒,乃是红烧大肠。一连夹了五块,方又揭了一盒,乃是鲜炖鲫鱼汤,忙又喝了几羹。揭到第五盒的时候,食盒下边置了一块白璧,其璧洁白无瑕,质地细腻,温润光滑,真宝玉也。
重耳将白璧扫了一眼说道:“大夫惠顾亡人,使不饥饿足矣,何敢受如此之厚礼?”
负羁道:“此外臣一点孝心,公子切勿推辞!”
重耳再三推辞,终不肯收,负羁退而叹曰:“晋公子穷困如此,而不贪吾璧,其志不可量也!”
次日,重耳即行,负羁又负美酒两坛,细食十盒相送。
出城三十里,狐偃忽然说道:“吾等这次去楚,必由宋过,宋、楚仇深似海,吾等且不可说去楚。”
重耳道:“那吾等说去什么地方?”
狐偃道:“就说投宋。”
重耳道:“宋若留住不让吾等去呢?”
狐偃道:“宋襄公果真挽留吾等,必定会帮公子复国,这也不是坏事呀!”
重耳道:“怕他没有这个力量。”
狐偃道:“咱也知道宋没有这个力量,咱说投宋,只不过哄哄宋襄公罢了,该去楚,还去楚。”
重耳道:“那就这么办吧。”
狐偃道:“吾和宋之大司马公孙固相善,吾想先行一步,为公子前驱,可乎?”
重耳道:“可。”
于是乎,狐偃驱车先行,受到了公孙固的热情款待。宴间,公孙固问曰:“公子一行,是投宋还是过宋?”
狐偃诳曰:“乃投宋尔。”
公孙固曰:“为复国之事乎?”
狐偃曰:“正是。”
公孙固摇头曰:“这事宋办不到。”
狐偃曰:“宋既能助齐孝公复国,缘何不能助晋公子复国?”
公孙固曰:“今昔不同。”
狐偃曰:“有何不同?”
公孙固曰:“寡君不自量力,与楚争霸,兵败伤股,至今病不能起。”
狐偃曰:“依将军之见,吾等只有另投他国了?”
公孙固轻轻点了点头。
狐偃曰:“贵国不能助晋公子复国,留之一宿当不为难乎?”
公孙固曰:“看子把话说到哪里去了?晋公子之名,向慕久矣,莫说留之一宿,就是留之十载,吾国亦乐为之。吾这就遣人扫除馆舍,以候车驾。”
狐偃起身谢曰:“多谢大司马,依弟估算,晋公子该到城外了,弟想去迎一迎他,这酒待会儿再喝吧。”
公孙固曰:“也好。然晋公子乃大贤之人,今从吾境路过,吾不能不禀告一声国君。”
狐偃道:“兄言甚是,弟就在这里坐等了。”
公孙固乘车入宫,面见宋襄公,以重耳过境相告。宋襄公正恨楚国,日夜求贤人相助,闻听重耳到来,忙道:“把他留下。”
公孙固曰:“臣非不留也。晋公子志在复国,非仇楚也。况主公贵体欠恙,伐楚又非朝夕之事,还是放他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