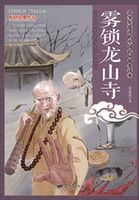二苗,擦完了没有,快些准备明天割麦用的镰刀,家里传出二苗母亲的喊声。李二虎咽了口唾沫,猫着腰蹑手蹑脚地出了小院。那一晚,他在村口的山坡上坐了许久身子才凉快下来。那一晚,他决定非二苗不娶。他只是弄不明白,以前和他一块儿上学的那个瘦丫头啥时候变成这样?女人真是会七十二变的。后来,二苗的父母要价三万,就是要价四万,他也要娶二苗的。他第一个月开了工资,给爹买了条捂腿的皮裤,给二苗买了条牛仔裤,腰身上还有一圈碎花呢!二苗说了,即使那个乡干部派媒人来提亲,她也不答应,她就等二虎。
有了二苗这句话,李二虎算是吃了定心丸。只是爹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让他多少有些不放心。
他每晚在县城的街上逛,不仅是为了乘凉,其实还有一个任务。
夏天的晚上,隔三差五,就有哪家出丧事,便会在巷口搭个灵棚,请一班响器在灵棚下红红火火地吹打,吹上党梆子《大祭桩》、《灵堂祭》,还有年轻姑娘小伙子唱流行歌曲,他最喜欢听《老鼠爱大米》。他想自己是老鼠,二苗肯定是大米。不过,自己才是真正的老鼠,整天窝在几百米的地层下呢!他不由咧嘴笑了笑。看到高兴处,他也会随着唱歌的人轻轻哼唱。人群中有好多他这种类型的人,他一下就能感觉到。那些人是外地的民工,操着他听不懂的口音。那时,他会用一种俯视的眼光看他们,自己是本地人嘛,他们是来打工的外地人。不过,灵棚下的乐队免费丰富了他们这些人的夜生活。
演出结束,他会找到响器班的头,索要一张名片。名片上面有联系电话,有班头的姓名。他工房的那个小木头箱子里面已攒了十几张这类民间乐团的名片。听得多了,他便能听出好歹。他相中两家,班头都说价钱好商量,现在这一行难做,竞争激烈呢!到时你打个电话,老哥肯定为你操办好,让你成为村里的大孝子,谁也不敢小看你。李二虎想着村人看他时眼里肯定全是佩服的眼神,一时便觉得自己高大威猛起来。
他愈发决定爹老了以后他必须要从城里请最好的响器班,给爹红棚,让爹高高兴兴上路,这才是孝顺。百善孝为先,这件事几乎比娶二苗还重要。
这样想着的时候,穿着一件白色衬衣的李二虎,在街上行走,像一尾游动在车流中的鱼。他不怕那些车辆,那些车辆都得乖乖给他让行,尽管有时会听到司机愤怒的粗口。有时,隔着车窗玻璃,还能看到一张扭曲的脸。但李二虎毫不介意,他每天要听到无数次骂声,看到无数次白眼。他知道那些城里人看不起他,说他们乡下人素质低,可他在心里不这样认为,城里人就素质都高吗?他有一次在超市发现一个中年女人,悄悄将一柄精致的小刀塞进她的白色手袋里。每次看到城里人那些卫生球眼睛,他会莫名其妙的在心里偷笑。
李二虎今晚的心情,只有一个字,那就是烦。烦吧还找不到出气的。
原来,他经常和村上的那个介绍他来挖煤的同乡一块儿逛街。可今天,那个同乡告诉他,说是乡里一个干部托人到二苗家提亲,出价出到五万元,二苗的父母答应了,二苗也答应了,男方说只要订了婚,就将二苗安排到乡政府的食堂上班。
李二虎不相信二苗会这样做,可也不相信自己。他手里现在连一万块钱都没攒够,也没本事给二苗安排工作。他将满腔疑惑放在心里,一个人出来透风。
在城里最繁花的庙街的拐弯处,有一家人正在红棚。灵棚下三盏100瓦的大灯泡,亮如白昼,周围挤满了人。典型的八音会,唢呐、二胡、锣、鼓、棒槌、笙全用上了,叽叽哪哪,吱吱唔唔,锣一声,鼓一声,好不热闹。一支唢呐正在吹上党梆子《皮秀英打虎》,那唢呐声就像一个女声正在如泣如诉,围观的人不时爆发一阵掌声。有那入迷的,别人的掌声已经停止,他一个人仍在啪啪鼓掌,引得大家哄笑起来,把一个穿孝衫的人也引得咧嘴笑了一下。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李二虎听着灵棚下传来一阵甜甜的女音,正是他最喜欢的歌曲。他在车流中,一边东张西望一边大步穿行。忽然,对面一辆车急驶而来,煞白的车灯一时晃得他睁不开眼。
这时,他忽然有些心慌,脑子里在瞬间一片空白。一声刺耳的刹车声响过后,他感到自己轻飘飘地飞了出去。
他离地面愈来愈远。他站在城市的上空,看着这座流光溢彩的城市。
他脚上那双回力牌球鞋,有一只已经掉了,他有些着急,明天下煤窑时穿什么呢?
他的身体愈来愈轻,觉得前所未有的轻松。他在空中看得清楚,灯光通明的街头围了好多人。那辆白色轿车的主人,吓瘫在车外,站不起来。带着大盖儿帽的交警正在驱赶围观的人群。街上的车辆一眨眼便排了长长的一溜,司机们从车窗探出头来张望。李二虎看着一辆红桑塔纳轿车里,一个女人正将头歪在手握方向盘的男人的肩上,男人正扭头吻着女人的头发。李二虎不仅叹了口气,他与二苗在一个村上呆了二十年,也仅仅握过二苗的手,二苗的手白皙,但粗糙,手掌上还有硬硬的茧子。
到现在,二苗也不知道他偷窥过她擦身子,见过她那白白的胸脯。不知道,二苗那白白的胸脯最终谁会享用。
就让街上那堆人忙乱吧。他感到累了。他想回家。尽管那个家很简陋,尽管那个家只有他和爹两个人,想到爹,他一时有些心酸,他还等着爹老了以后好好操办一番,请城里最好的响器班去红棚,让爹高兴,也让村上人高兴一次。村子太偏僻,一年也难得听到几次锣鼓响。村子里只要有响器班来,不是有人老了,就是村上的姑娘往山外嫁呢!那是让村上的小伙子们伤心的声音。
其实,如果不是为了娶二苗,他不会离开村子。这个城市不属于他。
那个没有高楼大厦,只有翠绿的山,甜甜的山泉和阵阵松涛的地方,才是属于他的老家。现在,他只想自己变成一只鹰,以箭一样的速度飞回家乡。只是不知村上的乡亲们会不会让他进村。
家乡的风俗,年轻人死去,正值壮年,属于凶事,在外面死去的不能进村,只能停在村外,草草处理,更别说给他红棚。飘在半空的李二虎一时有些忧郁。
一个人的旅行
休假
正是上午十点钟,办公室明晃的像挂了满屋100瓦的灯泡。那一刻,许茹云都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就像枚爆炸的炸弹一样,炸得四面开花。
领导在瞬间有些反应跟不上,只是看着对面的许茹云脸色煞白,嘴像机关枪一样一通猛扫:“动不动就是扣奖金,能不能来点新鲜的,把我爆炒算了,行不行?行不行!”
那一刻,许茹云脑子里一片混沌,她的大脑已经管不住自己的嘴巴。
她就像一只鼓鼓的气球,要不将这股气放出去,整个人就会爆掉。家里家外的事,她已经受够了。
昨晚忙完公司的事,回到家已是晚上九点钟,心里就带着几分歉意。
推开门,秦刚正跷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听到门响,他连头都没转一下,好像她是无色无味的空气。此时,肚子里咕咕噜噜一阵猛响,想到整整一个下午自己忍着肚痛,笑脸陪着客户,好话说了两车皮,那个像怒目金刚的男人,才算有了笑模样。回到自己家,莫非还要看这个054男人的脸色不成?火气呼地一下窜上心头,她手下脚下的动作便带出巨大的响动,就盼着秦刚接茬,那样她就有机会闹个不亦乐乎。她不在乎破坏自己的形象。够了,累了。她努力做一个优秀的员工,努力做一个贤惠的好妻子,可好像从没有人考虑过她的感受,秦刚这个离她最近的人都认为她是铁打的,多大的压力都能自己承受。她不要做宰相,她就想做一个不高兴就哭哭啼啼,高兴了就哈哈大笑的女人。
叮叮当当一阵响,高跟皮鞋老老实实缩在墙角,手机也悄声静气地躺在茶几上。秦刚两只耳朵里像塞了棉花团,无动于衷。许茹云心里涌上一阵绝望,泪水忽地一下涌上眼眶。那就哭吧,痛痛快快哭出声吧!
许茹云已准备像泼妇那样一把鼻涕一把泪,狠狠地宣泄一场。就在她甩头发的工夫,泪水却奇怪地消失了。她眨了眨眼,眼睛甚至有些发涩,连眼睛都与自己作对!
许茹云像破了洞的气球,软软地陷在沙发上。小腹有些隐隐作痛,两个鬓角也在嘣嘣跳着痛,似乎有一股气在顺着脊梁骨窜上窜下。她四肢弯曲缩在沙发上,那姿势就像在母腹中的样子。她告诉自己,挺住,不要让秦刚笑话,少了这个男人的问候,就不活了吗?那天晚上,她没吃饭就上床休息了。她是弯腰搂着肚子进卧室的。好多女人在结婚前有痛经的毛病,结婚后却不治而愈。她偏偏是个例外。做姑娘时,每个月的例假准时得就像单位里的杂工老刘,几乎是在踩着点上班。结婚后,尤其是这几年,例假就像一个叛逆的中学生,不迟到就早退,说来就来说走就走。那天晚上她做了好多梦,一幕一幕的场景就像演电视剧,梦中一直有个男人笑望着她,是一张熟悉的面孔,可她想不起来是谁。
睡梦中,她突然醒了:“迟到了,迟到了。”等醒过神来,满屋流淌的却是白白的月光。窗户没有上纱帘,隔着玻璃,能清晰地看到夜空中那一弯新月,静静的,像一只明亮的眼睛俯望着她。她侧了侧头,看到秦刚睡得正香,一条胳膊伸在被外,不时还有一阵轻微的鼾声。他一定能活个大寿数,他脑子里从来不考虑没有边际的事。
许茹云想起刚结婚的那段日子,两个人谁也离不了谁,如影随形。
她到娘家住两天,头天走,秦刚第二天就奔过去,一天不见对方心里就没着没落。
那时候,他们住着十六平方米的小屋,既是客厅又是卧室还兼着厨房。许茹云在那一方小天地乐此不疲的忙碌。在对着门口的一堵墙上装了一面大镜子,让小屋一下宽敞明亮了许多。地板中央一张驳了漆的小桌,铺着一块白色镂花的桌布,一个咖啡色的高颈花瓶骄傲地站在那里,里面插着一束怒放的百合。白色的双人床上是一床黄色碎花床罩,上面放着烫着童花头穿着粉裙子的洋娃娃、一只毛茸茸的小狗,墙角还放着两个白色的衣柜。水泥抹的地板,被许茹云每天不辞劳苦地拖过来拖过去,发出喜滋滋的光泽,衣柜的左侧还挤着一只小小地白色书柜,上面放着许茹云喜欢读的书。一个宝石花录音机喜气洋洋地坐在书柜凸出来的面上,里面经常会回响着伍思凯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那时候秦刚激情澎湃,经常会随着歌声舞之蹈之。一块小天地,被许茹云收拾成温馨的天堂,秦刚的朋友们不止一次羡慕地说:“秦刚,你老婆的手会变魔术,什么东西到了她手里都能变废为宝,摆出一番样子,真奇怪!”
秦刚沾沾自喜,一点都不谦虚:“那当然,我老婆是什么人呀?”
就是那样小的家,秦刚还经常邀好友到家里相聚,几个男人边喝边聊,许茹云系着漂亮的花围裙,在刚进门的铁皮火炉上,手忙脚乱地做油炸花生米,做西红柿炒鸡蛋,做糖醋丸子。几样菜装盘放在桌上,她要卷起帘子透好半天风,才能将屋里的油烟散尽。她将铁皮火炉用一块猪皮擦得油亮,地板打扫干净,火炉上蹾着一把铝茶壶,不多时便快乐地吱吱叫起来。许茹云给每个人茶杯里加上足够的水,就坐在火炉旁捧着一本书读,火炉冒着红红的火苗,她的脸也红彤彤的,心也是。听着秦刚豪气冲天的吆喝声,她会偷偷抿着嘴笑。那时候多好,他们无忧无虑。
工资不高,两个人合起来每个月工资不到六百来块钱,可他们居然够花,还要隔三差五下馆子吃小吃。两个人在单位都是小职员,不担事,整天算计的是怎样让对方高兴,从来没有算计过钱的事。
晚上吃过饭,他俩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秦刚将频道让出来,她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看的节目。要不就谈点单位呀社会上一些新闻。两个人谈得热火朝天,好像屋里有几十号人似的。从什么时候开始,两个人觉得忽然无话可说?许茹云记不起来。她只知道,随着秦刚在单位担任了个职务,承担了科室的负责工作,孩子上了初中,她一下子忙得昏天黑地。昨天上午学校开家长会,她正在单位开会,走不开。她打电话让秦刚去参加,秦刚只是闷闷一句话“我有事,正开会,”便挂掉电话。许茹云顿时觉得胸口像堵了块儿破布,闷得难受,孩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的,秦刚你凭什么当甩手掌柜?
许茹云柔着声和领导请假时,领导满脸不高兴,几乎将窗户玻璃看出洞来,嘴里才吐出一句话:“去吧,快去快回,今天的会议很重要,业绩是和奖金挂在一起的。”许茹云惴惴不安地走出公司。她不明白,她开个家长会和业绩、奖金也会挂钩吗?一年不就是开两次家长会吗?
学校的教室,已坐满胖的瘦的、黑的白的成年人。许茹云坐在靠窗的位置上,阳光照得她有些昏昏欲睡。恍惚中,她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少年时代。她是班长,脖子上系着红领巾,正精神抖擞地给同学发作业本;正站在讲台上打着拍子,领着同学们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那时的学生很单纯,不像现在的孩子们叛逆,都吵吵嚷嚷着要张扬个性,让家长轻不得又重不得。许茹云的思绪信马由缰,没提防老师在讲台上一连喊了她几遍,“牛小马的家长来了没有?”
许茹云嘴里应着“来了”,忙举了举手。
“你是小马的妈妈?怎么做家长的?你的孩子在学校表现怎么样,你知道不知道?你还负不负做母亲的责任?已是初三了,小马整天泡在网吧,还在身上纹身,你知道不知道?从来没见你和我们沟通过,不要以为把孩子交给学校就没事了。”老师像批评小马一样批评了许茹云一通,许茹云红着脸几乎要将头缩进胸腔。
从学校出来,许茹云沮丧到了极点,她做女人怎么这样失败?她虽然不是女人中的极品,但她也不是那种拿不上台面的女人,为什么家里外面一团糟?她一个人漫无目的地乱走,不知不觉就上了学校对面的灵云寺。
正是下午四点来钟,山门外静静悄悄的。她的心也忽然静下来。
山门外那块空旷的场地有三面都围着白色的栏杆。她走过去,双手扶在栏杆上。秋天的阳光照在身上有些发热,风吹过来,却带了几分凉意,放眼看去,远处层峦叠翠,村庄隐约其中。看着看着,自己就变成了一点绿也融入其中,一转眼,又化成一只苍鹰,在碧空盘旋。她站了许久,直到天色逐渐暗下来,一个穿着灰色道袍的僧人站在她面前,才将她惊醒:“施主,这里风高,要不要到寺中小坐?”想来这悲天悯人的僧人已观察她许久。许茹云急忙回答:“谢谢,不用了,我准备下山。”“阿弥陀佛”,高个僧人转身欲走。许茹云看到僧人耳后的那道疤痕,又想到平日里人们的传说,不由张口道:“师傅,你不是暴云山吗?”“阿弥陀佛,这里没有暴云山,只有觉远。施主,告辞了。”僧人双手合十,快速走开,一会就顺着高高的石阶隐入了山门。
一种莫名的绝望忽然像网一样将她罩着,这个暴云山曾是市里的首富,就在他的事业如日中天时,他却突然遁入空门,入了当地的灵云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