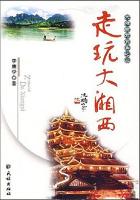来,和我一起陪咱爹喝一杯。我看了她一眼。
女人身子往后一缩,甘村长你怎么能这样呢,一杯又一杯的,这可不行。
进了门就得听我的,不喝就甭想……拿钱。我有点不高兴了。
女人眉毛一挑,怎么能这样呢,喝也行,你得加钱。
钱钱钱的,你让她赶紧走。我爹忽然指着门出了声。
这时候,我听得我的手机唧唧唧地响了,接起来一听,是鼓匠班的头儿马乐打来的,说他们来了,让我出去接应一下。我看了那个女人一眼,不喝就不喝,走,跟我去接待人。女人从她的小皮包里掏出张纸,抹了抹嘴,噔噔噔地跟着我出门。出了院门,风把她身上的味道吹了开来,我使劲吸了一口,忍不住停下来,说,我有点多了,你扶我一把。她说,你可不敢乱想啊。我摆了摆手,快点扶住我,不看我喝多了吗?她迟疑了一下,还是揽住了我的胳膊。我感到我的身体哆嗦了一下,走着走着,我忍不住伸出手摸了一下她的屁股。她尖叫了一声,火烫似的弹到了一边。
太流氓了你,再这样,我就不陪你了。她一惊一乍地说。
小皮突然叫起来。
我觉得有点酒醒了,心说是不能这样,她不过是陪我演演戏,哪能当成自己的女人呢。
我就一瘸一拐地往前走。
她落在后面慢慢走,离着我至少有几步远,好像我随时都可能扑向她。我回过头看了她一眼,你走快点嘛。
到了村委会门前,我看到鼓匠班的车早停在那儿了,一辆搭了篷的东风130货车,七八个演员都在呢。车就是戏台,一会儿他们就在车上表演,根本就不用搭台。鼓匠班子如今都这样,说走就走,车走到哪儿,戏就唱到哪儿。马乐见我过来,伸出一只白白净净的手握了我的黑手,笑眯眯地把我介绍给了他的同行,说这就是甘家洼的甘村长。又把他的演员介绍给我,这是谢美美,这是关哥,这是喜红妹,这两位是刘家兄弟。我学着镇长的样子跟他们一一握了手。马乐看了我身边的女人一眼,这是谁,好像哪里见过,不会是你老婆吧?
偏偏她还真是我老婆呢。我没假思索地说。
马乐含糊一笑,你老婆不错嘛,年轻,漂亮。
女人也是含糊地一笑。
我说老马你先把喇叭放开唱,听到声音,人们就出来了。马乐就指挥人开始忙活。他们从我的办公室往外拉电线时,我发现外面的人还没一个回来,村子里的人也没一个出来。后来我看到我爹来了,他抱来一大摞塑料凳子,他把它们一个一个摆开,嘴里念叨着啥,好像是说这个该谁坐,那个该谁坐。他又抱来几块木板,用砖头把它们架起来,我看出什么阵势了,一块木板就是一个能坐好几人的长条凳。马乐他们接好线放开了喇叭,外面的人还是没一个回来,马乐就问我,怎么还没人?
我摇了摇头,只管唱你们的,把声音开大。
马乐就跳到车上放了一个曲子——《祖国你好》。
我的小驴小羊蹦跳着出来了。我妈慢慢腾腾地出来了。月桂、三铁匠、老张头、富仁的老娘、老葵和他的哑巴侄子出来了。这些人一出来,我就知道全村的人差不多都出来了。可是那些在外面打工的人呢,他们怎么没一个回来?我看了月桂一眼,我说你家天成咋不回来?月桂摇摇头,他说还没放假,老板不让回。我又问三铁匠,你家小雪小凤咋不回来?三铁匠说,我刚才还给她俩打电话了,她们说还得几天。我没去问富仁的老娘,我知道富仁这家伙不会回来了。我摆了摆手,说都坐吧,坐下好好看。我发现他们坐下后,都盯着我身边的女人看。可是呢,我身边的女人根本就不怕他们看,手里捏着一袋瓜子,瓜子皮从她嘴里吐出来飞得好远。
马乐探过脸问我,村长,现在可以开始了吗?
我说再等等,镇长还没来呢。
马乐就又放了个曲子——《今天是个好日子》。他当然不舍得用自己的嗓子唱了,他们这些人啥德性我太知道了,怕唱多了唱坏了嗓子,嗓子唱坏了以后就没有挣钱的本钱了。我听着喇叭里放的曲子,心里问自己,今天是个好日子吗?我又低下头问小皮,今天是个好日子吗?小皮不吭声,它只会摇尾巴,没一点想说话的意思。我接着问我身边的女人,今天是个好日子吗?女人噗地吐出一颗瓜子皮,当然好了,唱大戏能不是好日子吗?
马乐放了半天曲子,又问我,开始吗?
我知道不可能有人回来了,镇长肯定也不会来了,他肯定忙得把我们村唱戏的事忘了。我就摆了摆手,开始吧。
马乐说,不等镇长了?
我木木地说,镇长有事,怕是过不来了。
马乐哦了一声,那我们就开始了?
我顿了顿,等等,好歹我也得讲几句。
我从马乐手里要过话筒上了戏台。我听得我的喂喂声从话筒里传出来,传得很远很远。我郑重地给台下的人们鞠了一躬。我说,今天是个好日子,好多年我们村没唱过一台像样的戏了。这都是我的过错,我这当村长的不能给大家唱一台像样的戏。今天我给你们请来了县城最好的戏班子,都是响当当的演员哪,马乐,着名的北路梆子演员,三铁匠你听过他的戏吧?谢美美,着名的歌唱演员,还有喜红妹和关哥,着名的二人台演员,还有刘氏二兄弟,都听过他们说的快板书吧?能把他们请来,我高兴啊,我这个村长没白当。我给大家唱这台戏也不是因为我有钱,我就想花钱给大家找个热闹。我们村过去多热闹啊,我就是想给你们找回从前的热闹。好啦,开戏吧。
我等着他们鼓掌,我觉得我讲得很好,好多年没讲话了我觉得我还是讲得很好。甭看我没念过几天书,从前我大会小会讲得可多呢,放电影前我要讲几句,戏开前我要讲几句,没戏唱没电影可放时我在办公室对着麦克风也要讲几句,我的声音通过街头的大喇叭响在村庄的每个角落,听了的人都我夸口才好。可是现在,他们听了我的讲话竟没一点反应。
你们的手都哪去了?也不鼓个掌?我脸一沉说。
“我的女人”和那几个演员就鼓起了掌,可是我们村的人却没一个伸手。
我摆摆手,算了算了,开戏吧。
喜红妹和关哥先登了台,到底是着名演员啊,二人台唱的那叫个好。
喜红妹长得也那叫个好,我盯着她,我的眼睛一直盯着她,我从她脸上看到了另一个女人的脸。我从她身姿里看到了另一个女人的身姿。我从她声音里听到了另一个女人的声音。那是我的女人啊,是那个撇下我爷仨跟野男人跑了的女人。她这会儿在哪里?我又看了看我身边的女人,她的眼睛一直没离开过喜红妹,她一边嗑瓜子一边听戏,脚下早落了层乱七八糟的瓜子皮了。她就坐在这一地瓜子皮里听戏,看都不看我一眼,好像她就不是我租来的女人,好像跟我一点瓜葛都没有。
我看到马乐登了台,他先是唱了一段《算粮登殿》,接着是《四郎探母》,再就是《空城计》啦。我知道他《空城计》唱得好,他就是凭这段戏出了名的,我看到他手摇芭蕉扇站在城头上唱: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泛影,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这家伙唱得就是好,有板有眼,看得我爹眼睛珠都不转啦,两只手还跟着打拍子,脑袋一晃一晃的。马乐唱过了这段,我爹鼓起了掌,我妈也鼓起了掌,我爹忍不住站起来,说再来一遍,把这段再来一遍。三铁匠也说,对对对,再来一遍。马乐还真就重唱: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泛影,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
镇长就在这时进了村。
镇长坐着一辆我叫出不名的小车来了,车身明晃晃的,车屁股也明晃晃的。车是他自个开的,他跳下车,腆着个啤酒肚朝戏台这边走过来。我赶紧伸出手捅了一下我身边的女人,甭嗑了,镇长来了。我身边的女人懒洋洋地站起来,老大不情愿地跟着我迎上去,我说,镇长您来了,等了您老半天呢。我身边的女人也出了声,镇长您来了。镇长看了她一眼,又把目光转向我,这是谁?我压低了声音,借的,是我借的女人。镇长瞪了我一眼,真是瞎胡闹。我就有些结巴了,不是您让我借的吗?镇长点着我的鼻子说,你真是个一根筋,不知道那是跟你开玩笑吗,酒话你还能当真?我不知该怎么说了。镇长摇摇头,目光从我身上又移到车上,又从车上移到台下,老半天出了声,你这不是耍我吗,怎么就这几个人?我硬着头皮说,镇长您上台给大家讲几句吧。您好久没来我们村讲讲了,您给我们讲讲吧。
镇长脸一沉,少给我打岔,你不是说你们村的人都能回来吗,怎么就这几个?你这不是给我唱空城计吗?
镇长说着朝他的小车走去。
我哭丧着脸说,镇长您不看戏就走?
镇长摆摆手,镇里还有好多事等着我处理呢,我得回去。老甘啊老甘,你这家伙藏得就是深,你总跟我哭穷,说你们村穷得都揭不开锅盖了,揭不开锅盖你花这么多钱唱戏?揭不开锅盖你能租个女人?
镇长拉开车门,本来是要钻进去了,忽然记起了什么,又回过头对我说,对了,买这车我落下不少饥荒,你得给我想想办法。
甩下这话,镇长砰地关了车门,走了。
我看着镇长的车驶出村口,渐渐消失在了老火山背后。日头眼看就要落山了。我又坐到了我爹身边。我租来的女人还立在那里,我指了指身边,坐下,你也坐下。她老大不情愿地坐到了我身边,坐下了却一点都不安稳,一眼一眼地看手腕上的表,嘴张得能吃几颗鸡蛋似的打哈欠。我的小驴小羊没了影,也不知他们疯到哪里去了。小皮倒是安静,卧在我爹腿边,耳朵一竖一竖的,听得认真着呢。马乐不知什么时候下了台,把那张唱空城计的嘴贴到我耳边,村长,你看这戏还要不要唱下去?我让他给问得愣住了,他说啥?这戏还要不要唱下去?我身边的女人捅了我一下,悄声对我说,算了吧,也没多少人看,这会儿打住,能跟他们按多半场算。我知道马乐什么心思,我也知道这个女人什么心思,他们都急着回去了。
我咬牙切齿地说,唱,唱,给我唱到底。
马乐摇摇头,懒洋洋地往台上走,筋骨好像给谁抽了,没一点气力了。
我身边的女人一眼一眼地看我,一颗瓜子皮苍蝇似的砰地撞到我脸上,又一颗瓜子皮嗡嗡嗡飞过来。
我心里狠狠骂了一句,腾地站起身,冲着台上的马乐挥了挥手,算了,不唱就不唱了。马乐直愣愣地看着我,老半天说,真的不唱了?我点点头,不唱了,散了吧。马乐又说,真的不唱了?我说,不唱了不唱了。马乐脸上立刻开了朵花。我就给他们结钱,我一分都没少给他们,一千五就一千五呗。我对点钱的马乐说,你给我记好了,明年的今天,甘家洼还要唱戏,我还要订你的班子。马乐好像没听见,收了钱一扭身就上了台,去指挥他的同行收拾东西了。我看着他们整理好东西,看着他们说说笑笑上了车,看着他们喇叭一鸣屁股一冒烟走了。他们一走,日头就一闭眼睛栽到老火山背后去了。我爹他们也站起了身,往家里走了。富仁的老娘走得颤颤巍巍的,好像一阵风就能把她吹倒。我盯着她的背影,心里说,富仁啊富仁,你怎么就不能回来呢,这么好看的戏,你就不懂得陪着你的老娘看一眼?挣钱就那么要紧?
都走了,除了小皮,除了我的小皮他们都走了。
不,我身边还有一个人,她站在我身边却不看我,嘻嘻哈哈给谁打电话呢。
没多久,来了辆大红的出租车,我身边的女人眼一亮,跑过去说了句什么,然后又回到我身边,伸出一只手说,真不好意思,您付费吧,我还得回去跟我们经理结账呢。我看着她那只绵软的手,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给揪了一下,但我还是掏出钱给了她。她一张一张点了钱,揽了一下我的胳膊,谢谢,谢谢您了,希望我们下次还有合作的机会。说完,她就钻进了出租车,好像是记起了什么,她又打开车窗,冲我摆了摆那只绵软好看的手,然后,屁股一冒烟去了。
散了,一台戏就这么散了。
我站在刚才的热闹处,不提防喉咙里冒出了几句唱词:到此就该把城进,却为何在城外犹豫不定?进退两难为的是何情……你不要胡思乱想心不定,你就来来来,进得城来听我抚琴……
唱得好,唱得好。我听得有人啪啪啪在我背后鼓起了掌。
我扭过头一看,却原来是收破烂的大老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