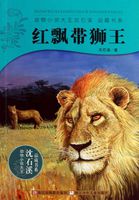第一部分
一九九六年七月五日,我女儿疯了。那年她才十五岁。她这一疯,我俩的人生顿时风云变色。"我觉得好像要到好远好远的地方去,再也回不来了。"有时她突然清醒过来,没头没脑说出这段话,说着说着又迅速离我远去。她究竟去了哪里,我猜也猜不到,梦也梦不着,只知道我必须一把抓住她,拉她回来。太迟了。我和她之间的联系瞬间消失,真不敢相信。想当初她牙牙学语时,教她说话的是我,第一个念故事给她听的人也是我。这些无法抹灭的记忆,却在一夕之间,全都化为乌有。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责怪自己。没错,我从头细数自己犯下的每一个错误,扪心自问到底少给了她什么,但终究还是无法解释我眼前的事实。真的是无语问苍天啊!我一度把希望寄托在医生身上,后来发现医生所知有限,医生只知道我女儿病情的临床表现。若真正要谈起她的情况,恐怕医生也比我高明不了多少。后来我还发现,当今人们对精神疾病的了解和以往差不多,都是如同瞎子摸象。这些虽然表明要治好我女儿的病,机会微乎其微,但同时也意味着,精神疾病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方面。
在当代社会里,"精神病"三个字会冒犯人的,正确的说法是"脑部疾病"。就某方面而言,这确实是一种脑部疾病,但有时候我和女儿相处,却觉得自己面对的是暴风雪或洪水等罕见的自然景象,它狂暴到可以摧毁一切,狂暴到叫我忧心、又叫我吃惊的地步。
七月五日。我在公寓里醒来。我们住在纽约格林威治村西区银行街一栋廉价公寓的顶楼,周围的建筑相当气派。我身旁的床空空荡荡,帕特一早就出门到她在富尔顿街开设的舞蹈教室结账。我们结婚两年了,各自带着以往的包袱进入这段婚姻,两人的真正世界只能在缝隙里寻找。
而我带来的最大一个包袱,就是我那正值青春期的女儿萨莉。我有点讶异萨莉居然已不在。还不到八点,屋里就已经又热又闷,太阳把涂了柏油的屋顶烤得发烫,女儿睡的上铺离天花板不到三英尺,自然是暑气蒸腾,加上昨晚我们的冷气烧坏了家里最后一根保险丝。她铁定是逃出去呼吸新鲜空气了。
客厅地板上杂物满地,都是她昨晚挑灯夜战的痕迹: 一台坏掉的随身听,用胶带紧紧捆着;半杯冷掉的咖啡;一本布面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过去这几个星期以来,她一直在钻研这本诗集,而且越读越有兴致。我随手翻开诗集,里面交织着各种符号、密密麻麻的批注、圈起来的单字,看上去实在令人眼花缭乱。尤其是第十三首,在页边空白处写满了评语,原诗差点淹没在茫茫的手写字海当中,看起来好像是犹太教经书《塔木德》里的一页,从头到尾密密麻麻写满批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