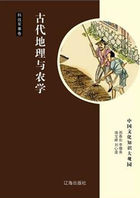村里,高三金长得贼眉鼠眼,个头小,是白龙村有名的盗贼。曾因盗卖耕牛在牢房里坐了一年零九个月。出狱后,偷技更为高超。既能掏腰包,又能翻墙入室。他在镇上偷,在县城偷,若不是已娶妻生子,他一定会偷到大城市去。但是自从村里建了化工厂,高三金就再没出过门。他跟妻子吹嘘说,你随便去城里看看,哪家大工厂周围没养肥大批大批的贼?钢厂旁边的叫“钢耗子”,油厂边上叫“油耗子”。耗子多着呢,大工厂牙缝里稍稍漏下一点,就够耗子们啃的啦。高三金单打独干,从没停止过偷盗化工厂。厂里以前的围墙对他形同虚设,他一翻就过去了。加固增高后对他也不起作用。他每次都只偷很少的量,从不多偷。日子长着呢,他把化工厂当成了自家的自留地,随需随取。这种日子对高三金来说很让他满足。够了,游手好闲,有地方有东西可偷,而且从不会失手,还要怎样呢?化工厂家大业大,或许他们根本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高三金过得油光水滑,滋润惬意。
厂里的围墙做得坚固,里边砌着红砖,表层还被抹上了一层水泥。在一僻静处,高三金从墙上方方正正地凿下了一块。那是完整的一整块,卸下它,围墙上会显露出一个方洞。再装上去,围墙重又变得严丝合缝。那方形的接缝,看着隐约就像墙壁的裂纹。它是高三金给自己悄悄安装的侧门,四周长着些灌木丛。他轻松着呢,进进出出都是穿门而过,毫不费力。就像是那墙壁里暗设着机关。他摸索着墙壁,摸着摸着就会从上面掉下一块来,洞口打开。
他背着只蛇皮袋子,里边装的物件并不多,但很沉。很难把那样的重量和高三金的个头连在一块。他几乎不是背,而是吃力地从墙里推出来。搂着,往上提,再推,一看就是在推某个重物。背着,是指从墙根这儿,到高三金的家,一路上他要歇上好几回。现在是深夜,漆黑一团。高三金返身堵上墙洞。他有些疲惫,更是欣喜。一屁股坐在蛇皮袋子上抽支烟,袋子里的东西怎么也坐不坏。他坐在上面,也不嫌硌人。没一点声音,草和灌木的枝条也没有丝毫晃动。高三金烟抽到一半还是觉得不对劲,他站起来,试探着往前走了几步。某种尖锐的硬物猛一下顶在他腰眼上。高三金一哆嗦,滑稽地举起双手。
嗬嗬,这么快就举手,很容易叛变啊你。原来是王大根。他在部队上呆过,说话总还带有部队里的尾音,听着特讨厌。
顶在腰眼上的是根木棍,高三金把它拂开了。你没事半夜里跑来顶我干什么?在家顶你媳妇不好吗?顶我,我还以为是刀呢,或是电棒?你又不是不知道,化工厂保卫科的那些人都配着电棒呢。他们穿着制服和派出所差不多,手上握着电棒好像随时准备着要顶人。
不是还没顶过你吗?
那是,顶我?哼!
你像只老鼠,会钻营啊。围墙上,王大根用手指了一下,像这样的门你还开了几扇?
你问门干什么?高三金对此保持着足够的警惕,王大根打听这些事不是好兆头。他以前从来都是正眼也不会瞧一下高三金,更别说跟他打听事。在村里,高三金连一条狗都不如。当然喽,他们谁也不会对贼有好眼色。
问你,你就说。王大根把高三金手上的半截烟夺过去吸了两口,又呸地一下吐掉。
问我,我就说?你以为你是谁啊?你是村长吗?或者你是保卫科的人?你和我一样,什么也不是。高三金从口袋里掏出烟来,那盒里还有十好几根。他叼一根在嘴上,剩下的全给了王大根。你拿去吧,他说,我家里还有。
王大根接过烟,本来想要扔掉,但他舍不得,还是顺手塞进衣兜了。
直说了吧你,高三金说,你总不会是专门来捉贼的吧?
捉贼?如果你在村子里偷,我一定第一个敲断你的腿。可你偷的是化工厂呢,化工厂该着被偷。我找你是要入伙,和你一块偷。
找我入伙?哼!王大根也会做贼?眼红我不缺烟抽?或是眼红我有几个闲钱?高三金心里的小算盘拨拉开了,有人入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他左想右想,兴许是坏事呢?他可不想做一锤子买卖,靠偷上一次就发家致富了。偷盗是一辈子的事,你得细水长流。高三金一个人小打小闹地偷,才不会引起化工厂的注意,也才不会让他们真正愤怒。他到如今都还没有被逮着,肯定是这个原因。要是偷的人多了,自然动静就大。动静一大,化工厂还会放过吗?他刚过上一段好日子,还不想早早就栽了。
帮我抬着吧,这东西重着呢,高三金说。
两人抬着蛇皮袋子,往高三金家走去。不光我入伙,还要拉别人入伙。最好是村子里的人全都入伙。偷他们,偷化工厂。全村人都做贼,把他们偷垮,偷得他们离开白龙村才好。王大根说得咬牙切齿,从声音就能听出他的眼里在冒出火花。
高三金听得心惊,手一松,蛇皮袋子的一端沉重地砸在地上。你这不是要害我吗?弄那么多人成群结队地去偷,不等于是自投罗网?怎么着?走亲戚?还是去镇上赶集?你要想被保卫科发现,还不如径直去报案得了。
你怕了吗?你一定是怕了。王大根对眼前这个小个子男人充满了蔑视。你如果不要我们入伙,我们就分开偷,各偷各的,井水不犯河水。
随便你们,只是别祸害到我。
什么叫祸害到你?
那么多人偷,人家化工厂还不来捉吗?地方又小,一捉一个准。如果捉到你们,哪还跑得了我?
呼一下,那根尖锐的硬物又顶到高三金腰眼上。你要是敢耍花招,或是捣乱,王大根说,我会最先在你这儿捅个窟窿。不信你试试。
不耍花招,恼火!高三金再拂开木棍,他的脑子飞快地转动着。他们那些人没一个有经验,没人偷过。真要蛮干,还没动手就会被抓着。哪怕分开偷,目标也大。既如此,还不如就带着他们。行啊,要入伙就入吧。
白龙村偷盗之风愈演愈烈,令化工厂管理层头疼不已。
为此,主任起草了一份严厉的报告,分送给镇政府,和镇派出所。同时以电子文本的形式,传给了远在异地遥控指挥的岳总。
报告指出,本地(白龙村)民风表面淳朴,实则刁蛮。据传历史上就有“匪性”,隔上几代白龙山就出土匪,他们打家劫舍,占山为王。化工厂自建在白龙村起,就非常重视和当地搞好关系,这也是岳总的“企业理念”:决不能让老百姓吃亏。所以,在土地转让,庄稼和牲畜理赔等诸方面,厂方自以为做得积极主动,不曾有过遗漏和差错,村里也从无一人前来扯皮。而且,在村里的公共建设方面,厂方也是不吝投入。比如修路,建花坛。往后,厂方也还会有新规划,将逐步实施。厂方这么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向村民示好,让企业尽快融入本村。最好的结果是,飞龙化工厂和白龙村变成一体。但是,很遗憾,厂方所有的努力并没有收到实效。很显然,村民对化工厂怀有深刻的敌意。敌意是渐渐滋生的,并不断加深。不排除有人在暗中扇风点火,还有人在暗地里组织教唆。报告列举了一些精确的数字,用以说明偷盗现象严重到了何种程度?白龙村全村总人口数是九百七十八人(许多青壮年在外地打工),有过偷盗行为的人保守估计应不下百人(有些人是偶一为之)。化工厂厂区内电子眼密布,通过调阅“录影”,那些惯偷很容易就能被指证出来。突然出现,并呈密集爆发之势的偷盗,大约是从几天前开始的。原因待查。以前厂里也经常会有一些很小的被盗事件,但厂方始终保持克制。因为损失微不足道,厂方大都秘而不宣,几乎不怎么追查。厂方的这一姿态,当然也是对村民的尊重。是否正因为如此,厂方的忍让被当成了软弱,从而诱发了大面积的盗窃?若果真是这样,厂方以后需要改进的地方还很多。报告还具体评估了偷盗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其他危害。损失的数额,以表格的形式附在报告后面。报告称,被村民们盗走的那些物品,如果当作废品卖,其实值不了几个钱。但对厂方的间接损害却很大。有时,厂方甚至不得不被迫停产。经济损失还是有形的,而无形的危害将更严重。假如不能有效地遏制偷盗,发展下去将很可能变成盗抢。这是有可能的,偷盗和盗抢仅为一步之遥。真要那样,谁也负不了责。报告认为,虽然厂里已加强了安全保卫工作(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巡逻),但这显然不够。因为化工厂和白龙村毕竟“条块”分割,厂方的“权限”到不了白龙村,白龙村的治安,化工厂其实无权过问。这才是问题的“瓶颈”。即使偷盗发生在厂区内,并被保卫科现场抓获,他们也不敢有过激的处罚方式。
所以,报告紧急呼吁镇政府和镇派出所,对白龙村的治安状况加强治理。
主任的报告,实际上是在岳总的授意下写成。岳总反复强调,要办好企业,必须依靠当地。当地出问题了,必须就地解决。
镇里的黄书记对此很重视,他把孙得福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你是怎么管事的?咳!你那地方都乱成什么样了?贼窝啊!黄书记把报告在手掌心里啪啪地抽动着,群体性偷盗,很恶劣,很严重,你难道看不见吗?以为是吃大户啊!怎么着?打土豪,分浮财?人人有份?谁都想伸手捞一把。
孙得福手摸着自己的粗脖子,他眼珠往外翻着,眼神黯淡,一看就心不在焉。
别老摸你那脖子,我看着呢,你在听我说话吗?
听着呢,孙得福说,别的地方都有毛病,就耳朵还行,能听见。
尽说怪话,你这态度还能管好事?村里也该出重拳好好治治了,你有办法吗?
要说治,也不是没办法。以前我们村子好着呢,不说路不拾遗吧,好多人家夜不闭户那可是真的。现在这事,根源还是在化工厂。
不用跟我东扯西拉,黄书记断然说道,村里治安恶化,作为村长你脱不了干系。我们的工作不到位,已经严重影响和干扰了化工厂的正常生产。既然你没办法,就由镇里采取措施。你的事呢,以后再说。
黄书记所说的措施,是让派出所李副所长带着两个民警到白龙村来驻村,协助工作。协助工作是一种比较笼统的说法,到底是协助化工厂呢?或是协助村长?镇政府并没有明示。
李所长五十来岁,烟瘾很大。到了白龙村,人们发现他阴沉着脸,总像没睡醒似的无精打采。他带着的两个民警,倒都是年轻后生,精壮着呢。白龙村村子不大。进村第一天,李所长他们三个人全佩戴着枪,在村子里昂首阔步地走了一个来回。他们钉着铁掌的皮鞋,敲打着化工厂铺就的水泥村道,响声清脆刺耳。那阵势,就像是城里的治安巡逻小分队。
主任带着几个人,站在路边对李所长致意。李所长没搭理他们,也没接受他们的邀请去化工厂吃饭。他直接去了孙得福家,说今天就在你家喝酒。可能要在村里呆些日子,以后我们回镇里吃,有车,方便着呢。今天例外,跟你讨酒喝。
说这话时快到中午,他们在孙得福家喝了整整一下午。孙得福喝得眼泪汪汪。要不你少喝点?李所长说,这酒呛人。
不少喝,少喝那还像样子?孙得福说,这酒不上头,就呛眼睛。
好像是有点。
后来他们都喝醉了。傍晚,天都已经刷黑了,他们才驾车离去。临走时,李所长说,我们还会再来。
警察进村,让风声一下子紧了起来。村里猛然间有了邪恶或不祥的气氛。他们还公然带着枪。那意味着他们代表正义,代表着铁的意志。他们可以随时掏出手铐来,铐向谁。只是在村道上走一走,他们的脚步声就已经让人心惊胆颤。大家都呆在家里,不敢轻举妄动,没人愿意冒犯。
高三金气得发抖,他在老婆面前一个劲地咒骂王大根。他不得好死的,你就看着吧。就连他们家的狗都不要他,可见他不是个好东西啊。他害我,拉我下水。警察可不是随便来的,他们来了一准会抓人。一边咒骂,高三金一边抓挠自己的胸脯,那里发出嘣嘣的响声。他们要抓,还不是先要抓我,知道吗?首恶分子!
他老婆是个黑皮肤的大个头女人,一见他着急,就弄蜂蜜水他喝。她弄了三大碗蜂蜜,搁在桌子上。喝吧,喝下蜂蜜你就不怕,就能安下心来睡踏实觉。
喝到第三碗蜂蜜水,王大根又来了。他说,正好,今晚可以去大干一把。
什么?今晚?你疯了吧?高三金把空碗咣地一声摔碎在地上。你疯了,我还没疯呢。我进过监狱,知道警察。他们可不是吃素的。他们刚来过,你却说可以大干一把。是不是想把我再送进去?
你进过监狱没错,可你别忘了,我还当过兵呢。当过兵的人最清楚,越是危险的时候,越安全。
那我也不去,高三金歇斯底里地叫着。蜂蜜水并没有起到镇定情绪的作用,他稀里糊涂地发作了,蹲在墙角呜呜地哭着。
他老婆站在一边手足无措,以前蜂蜜是可以让他镇静的。这时,她也只能陪着他哭。她说,你就放过他吧,王大根。他比不得你们,他软弱着呢。别以为坐过牢的人都强悍,他的胆子早整破了。
王大根呸呸地吐着口水,行,你不去我去。
在化工厂的机构设置里,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保卫科顾名思义,做保卫工作。从隶属关系看,主任管保卫科长。化工厂的内部管理,像机器一样严密。每个人都是齿轮,岳总的指令在齿轮间,被准确地传送。
眼下的保卫科长刘冬明是个矮胖子,第三任。他可能早年从事过举重运动,上肢发达,满脸横肉。几年来,保卫科一直被要求隐忍。对内部职工可以从严,稍有越轨,都会遭受重罚。而对外,对白龙村的村民,则始终都要亲善。不是没有过零星的冲突,也不是没有被现场抓住过偷盗者,但都被很宽容地处理了。保卫科要尽量退让,我们是在人家的土地上。他们通常只是没收被盗物品,然后通知村委会来领人,把盗窃者交给村长孙得福。至于村长事后怎么处置?他们就不得而知了。但基本上可以推测:他不会处罚。这形成了惯例。所以,当他们被抓住时,他们往往会和保卫人员发生肢体上的冲撞和推搡。你推我一把,我推你一把。那多半是村民们,保卫人员大都会高举起双手。有时,少数村民还会暗使阴招,某个保卫人员因此而会受伤。如果里面夹杂有妇女和老人(后来偷盗发展到顶峰时,的确有妇女老人参入),无疑他们会更为撒泼。他们用白龙村的土话咒骂,倒在地上装死。这种场面具有戏剧性,一般不等村长出现,他们就会当场被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