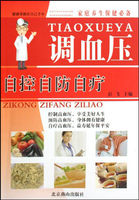孙得贵宣布,开始开会了。他的样子显得有些羞愧,就像他自己正在干着一件极不体面的事。其实他比谁都更头疼。八十块钱是一笔可观的数字,可以买很多东西啊。还有大米和衣被。这是政府的温暖和关怀,他说。政府一定要送给最需要温暖和关怀的人。但是,这会怎么开呢?以前抓过阄,丢过黄豆:每人发一颗黄豆,选谁就丢到谁面前。可弄到最后全都乱成了一锅粥。有人事先写好了字,团在手心里当成他自己抓到的阄。这种人还特别多,所以抓中的“阄”比比皆是。往年就这么搞过,麻烦也因此更多。谁都认为自己才是真的。他们一个个把纸片抹平,指着上面的字,赌咒发誓说,他们抓到了。孙得贵有些厌恶和害怕抓阄,也算是正常吧?至于丢黄豆,也同样毫无把握。你发给他一颗黄豆,谁知道他衣兜或指缝里还有多少颗?你永远也弄不明白这些人,表面看都老实,其实一个比一个鬼点子多。那么,到底怎么开会呢?孙得贵一进入腊月份就开始想这个问题。他想得脑瓜子发芽,也想不出个正经好主意。老在抓阄和丢黄豆上面绕圈子,又老是自己否定。一直拖延到十六日晚上,也还是一筹莫展。那就都发言吧,孙得贵说大家都说说,嗨,这事该咋弄就咋弄吧。
一听这话,就知道孙得贵也没啥主张。仓库里的人彼此之间互相观察,想要从对方的脸上或眼睛里看出某些蛛丝马迹。往年得到过救济的人,这时一般都闷着头不做声。那种滋味并不好受。头一年你被救济了,来年一整年你都得夹着尾巴做人。这是肯定的。你自己也会不自在,似乎你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人们都会用愤怒的眼光看你,无论什么事,你都得让着别人一点。是啊,那是因为你拿了救济嘛。你凭白无故拿了那么多钱或东西,当然就得让着别人。彭先和前年就曾拿过九十块钱的救济。而他家里一头半大的猪仔,却在自个的猪圈里被人给毒死了。毒药裹在一张面饼子里,被人从栅栏里扔进去。彭先和的猪啃了那张饼就哼哼着死去了。但彭先和并没有就这件事大吵大闹,他像是霜打的茄子,悄悄地把这头死猪扔进粪坑。猪的死尸在粪坑里膨胀,老远就能闻到一股恶臭。有人曾就彭先和的这头猪算过一笔账,算来算去,说是死猪让他损失了大约四十八到五十三块钱,这不算多。算账的人也许比投毒的人更为恶毒:他说不算多明显是要从九十块钱里减去这个数,因而还有“余款”。村里人都知道他是这么个意思。这种情况下,如果彭先和再又哭又闹,那就太不像话了。所以彭先和咽下了这口气,但他一直都在暗中追查,他还是想要知道谁毒死了他的猪?他找不到真凶。好几个夜里他从床上爬起来,独自来到粪坑边上。他划燃一根火柴,又划燃一根火柴,看着粪坑里黑糊糊的一堆,他哭得泪水糊满了一脸。现在他也坐在仓库里,心如止水。他只是来开会,开会的内容与他无关。他得过一次了,不可能再得到。此时他不无恶意地揣测着谁将会笑到最后?和他想法差不多的人也就一两个,都是以前得过的。而大多数人事实上还是存有奢望。
仓库里还有几个粮柜,有点像是大户人家家里的家具:装衣服或棉被的扁平立柜。它们的外形巨大而笨拙,板壁厚重。没人时,它们在空旷的仓库里显得孤零零的,透着寒碜。这会儿在拥挤的人群后面,它们一溜排地挤靠在墙边。有人用手敲打柜壁,粮柜的上半部分发出空洞的响声。而它的下半部分则明显有些沉闷,可能里边还储藏了一些稻种。对!据了解内情的人透露,那就是一些稻种,颜色金黄,颗粒饱满。它们被放在粮柜的底部,明年用来下种。而在稻种的上面,还放置着一些麻袋。里面装着黄豆,花生或芝麻。它们也是种子,庄稼的种子。它们现在都在里边。
人们都已经习惯了煤油灯的光线,每一张脸都被暴露着。
大家发言吧,孙得贵说。怎么推选?推选谁拿救济?大家说了算。这么说着,孙得贵心想,自己真像个无赖。就这么撂挑子了?可不这么办又能怎么样呢?那一个一个的人可都不是好惹的。他当村长也一样惹不起。要说他也想拿一份呢,可轮得到他吗?
哼!马跑说话之前先哼了一声,猛一听就像冷笑。抓阄不行,丢黄豆也不行。那还有什么办法?不如在稻场上弄一个台子,把钱和东西都放在台子上。一家出一个男劳力,然后发一声喊,大家一起去抢。谁抢到是谁的,抢多少是多少。
马跑是个粗人,他的一番话引起一片哄笑。
这样倒他妈省心,马跑说,干脆!
马跑总是这样,总能成为人们的笑料。他老往山里跑,总在钻林子。不怎么跟人打交道,所以脑子里一根筋。他的这一提议,被认为不过是在自说自话,更或者就是一个玩笑。它所唯一起到的作用,是让会场变得轻松一些了。有人从仓库里挤出来,在不远处小便。马跑也很穷。他暴烈的性子,并没有使他比别人过得更好一些。事实可能恰恰相反,他几乎算是家徒四壁。而且因为岩石和荆棘,他要比常人消耗更多的衣服和鞋子。但是他脸皮薄,让他开口要救济实在是为难他。他相信这么做很丢脸。而他老婆却不这样想,她在家里唠叨,怂恿他。她说,又不费什么,那不就是“白捡么”?她以为村里人都怕马跑,只要他一出面,什么事都好办。没想到他却只能出这么一个馊主意,让人们笑一笑罢了。其实,没人知道马跑的苦衷。他是在故意这么说。这么说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这刚好也符合他的天性。另一个意思更为要紧,他也想“抢”。只不过他在把一件正经事往“荒诞”里说,毫无疑问他是在以此来掩饰自己。他怕被人嘲笑。
匡有元显然不认为这有什么值得嘲笑。抢就抢吧,他说,万一不行,我不如就点一根雷管把台子炸掉了事。
匡有元只有一条胳膊。在建飞沙河水库时,他是有名的“点炮员”。人们在岩石上凿洞,填炸药,拉导火索。因为要炸掉半爿山,筑坝蓄水。那是一些坚硬的岩石,必须“炸炮”。在峭壁上,用铁钎和大锤凿出又细又深的洞来,把炸药一层一层地塞紧。炸药压得愈紧,威力愈大。工地上有人在捣弄炸药时,会因为用力过猛而导致瞬间“引爆”。操作者往往非死即伤。可是匡有元在工地上呆了三个冬季,直到飞沙河水库顺利建成,他都毫发无损。填好炸药之后,他总是峭壁上最后一个人。有人在高地上吹哨子,摇动红色的三角小旗。这是在通知所有人,马上就要放炮了。人们都躲开了,躲到远处去。只有匡有元,他披着褂子,嘴上叼着烟卷,手里拿着点火用的麻秆。他不慌不忙,就像在悠闲地巡视。他用麻秆点着一根炮捻,又点下一根。所有的炮眼都有顺序,他点得有条不紊。那些最先被点着的炮捻,导火索要长一些,而留在最后被点着的,则只有很短的引信。他点燃了每一个炮捻,还要用目光扫视一遍,看看有没有遗漏?然后才顺着一条山道下来。他也不跑,只不过比平时走得步子快些而已。等到他刚一到达安全地带,炮声就响了。密密麻麻,像是在放一串鞭炮。大家都在看腾起的烟尘,和飞落的石块。而匡有元闭着眼睛。他听声音就知道是不是所有的炮都炸了?有没有“哑炮”?他说好了,去清场吧。人们就放心地涌上去。如果他阴沉着脸说,不行,还有炮没炸呢。那就谁也不敢动。经过排查,他说有几个炮没炸就会有几个炮,一次也没差错。匡有元在工地上有些神,那也是他最风光的时候。水利工程结束后,回到村里来,匡有元重新变成了一个普通人。他一定不怎么甘心。有人猜测,他家里肯定藏匿着大量的雷管和火药,那都是从工地上直接带回来的。人们的这一猜测,在除夕之夜得到了证实。那天夜里,烟灯村的每家每户都在放鞭炮。而在匡有元的家门口,人们从鞭炮声里又听到了一声接一声巨大的轰响。大家很容易就能辨别出来,那是雷管发出的声音。匡有元家里有雷管,这样一个事实让人们不安。至于到底是什么让他们不安?却没人能说得清楚。一根雷管或者两根雷管,是可以炸掉一间屋子的吧?事实也是这样,如果你邻居家里装满雷管和炸药,你能安心吗?总之,匡有元被举报了。他的那些邻居把他告到公社和派出所去。派出所选择在一个温暖的春日,前来搜查了匡有元的家。和煦的阳光洒落在已开始抽芽的树枝上,烟灯村平和而安详。他们在匡有元的家里捣腾了一上午,甚至还挖掘过他的猪圈。可是,他们一无所获。匡有元自始至终一直陪伴着他们,他脸上挂着若有所思的表情。那种表情让你以为他还在做梦。当然,在他做“点炮员”时,人们经常能看到类似的表情浮现在他脸上。派出所的人临走时对匡有元说,你要是有,还是趁早交了吧。而匡有元根本就不搭理他们。几个月之后,匡有元开始在夜间,偷偷地到池塘里去炸鱼。他把炸药和雷管装填在玻璃瓶里,用黄泥巴紧封住瓶口。他携带着它们,就像一些土制手雷。人们在睡梦里,能听到像是炮声一样的声音。那正是匡有元在炸鱼。鱼漂浮在水面上,有些鱼死掉了,另一些鱼则只是被震昏了。匡有元捞取它们。他们家总在吃鱼,吃不了的鱼他会拿到镇子上去卖。但是,他炸掉了自己的一条胳膊。事情败露后,派出所又来搜查过一次,而且搜查得更为彻底,但却依然一无所获。真是奇怪!谁都知道他有雷管,那么他都藏在哪呢?为治疗断臂,匡有元在医院里住了二十多天。刚一出院,又被拘留了一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