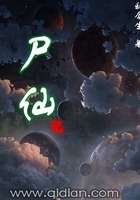一、在上海戏剧学院的求学之路
中学毕业之前,余秋雨需要考虑究竟该报考哪所大学。这时的他踌躇满志,坚信自己可以考上任何一所大学。但到底报考哪所大学呢?他一时也没有主意,于是他想到了两个同学,一个姓丁,一个姓张,他俩的成绩也出类拔萃,他想问问他们报考哪所大学,也好给自己作个参考。当时的大学分为三类,一类为理工科,二类为医科,三类为文科。他们考虑来考虑去,也没有结果。突然,不知是谁出了一个主意,他们决定三人各报一类,这样一来,等大学毕业后,三个人的知识加在一起,谁也不能超过他们。他们还可以揣着这些知识周游世界,全世界的人都会羡慕他们。
决定通过后,大家都很兴奋,并且决定,都要考每一类最难考的学校。那么三类怎么分配呢?干脆抓阄。丁同学抓到了第一类,考上了清华大学;张抓到了第二类,考上了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余秋雨抓到的是第三类,这是他不太愿意选择的一类,但大家既然已经定好了规矩,也就只能这样了。值得一提的是,那时的余秋雨从来没有想过要考中文系,因为他觉得中文在中学里都学过了,而且他私下里也看了不少文学名著,这方面积累的知识已经足够多了。余秋雨想来想去,觉得自己应该报考外文系,他开始打听哪个学校的外文系最好。
这是余秋雨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选择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他的未来。余秋雨回忆道:
班主任孙老师把我找去了,他身边站着一位我不认识的瘦瘦的老师,自我介绍是上海戏剧学院来的。“我们学校要以最高的要求招收戏剧文学系的一个班,现在已有几千人报名,只招三十名,但我们还怕遗漏了最好的,听说你在全市作文比赛中得了大奖……”
余秋雨听这位老师一说,有些来劲了,忙问上海戏剧学院是不是今年全国文科大学中最难考的?这位老师没有正面回答他,他告诉余秋雨,郭沫若先生在这个大学高年级里发现了一个能写剧本的高才生,立即决定中止他的学业,转到他们学院去读书了。这位老师还告诉余秋雨,巴金的女儿也来投考上海戏剧学院。这更增添了他报考这所学校的决心。巴金,这个让他敬仰的大师都将自己的女儿推荐到这所学校,这一定是所好学校,机会不能错过!
戏剧学院在全国是提前考试,考完还未发榜,全国高考统考就开始了,余秋雨很想试试自己的实力,又第一志愿填报了军事外语学院。结果两校都录取了他,这倒让他有些为难了,哪一个学校他都不想放弃。还是戏剧学院抢先一步,将他的档案拿走了。余秋雨隐隐之中感到有些遗憾,他打听到,军事外语学院毕业后可以做情报员、外交武官,这是多么吸引青年人的工作啊。在戏剧学院里,郭沫若推荐来的曲信先就坐在他的后面,他的邻座是巴金的女儿,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的自尊心。
当时上海戏剧学院的课程安排颇具时代特色。专业主课叫“剧本分析”,分析的大多是朝鲜的《红色宣传员》、中国的《夺印》和《英雄工兵》之类没有多少艺术价值,宣传味道很浓的影片。更让余秋雨诧异的是,所谓分析就是讲解思想内容,这本是中学语文课上的必修课,没想到到了大学还要这样操作,而且讲解的思想内容都往政治上靠,猛一听,就像在上政治课。余秋雨疑惑了:难道这些在社会上都能听到的东西就是大学课程?余秋雨盼望着他感兴趣的古典文学课。终于他们等来了一位老师,老师用不标准的普通话教了几个月的平仄和格律后,就要求学生写古诗。让同学们哭笑不得的是,待他们将写好的古诗交给老师时,他大为惊讶,连连问道:“这是你们自己写的?”余秋雨想,这位老师大概忘了,他们是以什么分数考进来的。
还有更叫人大跌眼镜的事情。一位有革命经历的干部说要给他们一次学习的机会——要他们抄写他新创作的剧本。剧本是歌颂一个劳动模范的,学生们对革命干部很敬重,也觉得很新鲜,就很虔诚、认真地抄写。可是他们不停地抄写,却总也抄不完,因为在他们抄写的过程中,这位干部还在没完没了地改稿。
在上海戏剧学院这样稀里糊涂过了一段时间,突然,学校奉上级指示,要他们下乡参加“四清运动”。余秋雨便又稀里糊涂地,不,应该是高高兴兴地和同学们一起来到了农村。农活虽苦虽累,好在那时的人都有一种信念,再苦再累都有共产主义精神支撑着,什么苦也就能撑过去了。要命的是,吃饭和住宿问题,余秋雨被分配在全村最穷的一户农家。他和四只羊住在一间屋里,每天吃的菜,就是一碟盐豆,从没见过一片青菜,更别说其它。而最让他恶心的是这里的水,淘米、洗衣、乃至刷马桶,全靠村里一条杂草丛生的污浊河沟。余秋雨很难适应,又不得不适应。他们这批大学生,本来生活在现代化的都市,平时洗菜的脏水也不知要比这河沟里的水干净多少,他们迷惑了,难道这就是让他们来锻炼的原因。
余秋雨惟一的精神之柱,就是几本从家里带来的外国名著,只有看书时,余秋雨才感到生活的真正意义。多年以后,余秋雨在《访谈录——关于读书》中表述了他对学者们读书于乱世的思索:
抗战时期,许多学者轻装逃难前确实思考过这个问题。有人带了《庄子》,有人带了《剑南诗稿》,有一位教授狠狠心,在简薄的行囊中硬是塞进了一部《红楼梦》。五十年代中期,一位被错误地开除了公职的大学教师落荒成一名边远地区的“车把式”,他的蓝布小包袱中则始终藏着一部《楚辞》。二十年前,一位美学家被迫到农村去劳动时,偷偷带了一本最“经读”的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
历史已经证明,这种匆忙间的选择,不仅温暖了这些学者生命史上荒寒的岁月,而且往往决定了他们后半辈子的学问走向,甚至,还有可能决定人文科学领域某一座大厦的落成。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这种选择中凝聚着他们的见识和截断。
余秋雨是一位智者,他总能掌握自己的人生座标,的确,生活虽然变化莫测,但你只要好好把握,就总能寻出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找到自己生存的空间。
二、“文革”对学生的影响
终于结束了农村生活,回到学校,余秋雨的眼前豁然开朗,他突然觉得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同学,包括学校的一草一木都是这样可爱。他先前在学校里的感受,完全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正当余秋雨准备全力以赴投身到学习之中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谁也没有想到这场运动会来得这样猛,来得这样残酷,又这样的持久。学校里的朗朗书声,变成了“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批判;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甚至鼓吹“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将打击的对象波及到父母有问题的下一代。被郭沫若推荐来的曲信先同学因家庭问题受到打击,巴金的女儿李小林更不用说。
余秋雨的家庭在这场灾难中也没能避免厄运。1997年1月9日,余秋雨在台湾东海大学题为《何处大宁静》的演讲中,描述了他全家在文革中遭受的不幸:
到大学遇到了文革,我父亲以“阶级异己分子”的罪名被关押,他是我们全家8口人生活经费的惟一来源,这一下全家被推入了绝境。我当时虽然还不到20岁,却是全家的长子,想到能救助我们的只有独身在安徽工作而尚未成家的叔叔,但刚刚想到就传来了噩耗,叔叔受不住批斗自杀。70多岁的祖母赶到安徽抱回了自己最小儿子的骨灰,然后偷偷找到父亲的单位,冒着危险从门缝里战战兢兢地看父亲受批斗,因为按照心理素质,父亲更容易自杀。当时全家的生活,靠我的刚刚初中毕业的大弟弟出海捕鱼来维持,未成年的弟弟每次回到上海都不敢回家,先找到我,小心翼翼地问爸爸自杀了没有……
如今,稍有同情心的人读到这段文字都会潸然泪下,可那个时候,人们的心仿佛被一种无形的魔力钙化,变得阴冷而坚硬。在那个年代,这种事情处处皆是。
那时的“血统论”和“唯成分论”也毒害了一批人。“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父亲是高干,儿子自然就是好汉,父亲是黑五类,子女也就是坏东西。“成分论”更是压制了一批无辜的人。“成分论”是解放初期“土地改革”运动时定的:以解放前三年为依据,这三年中,你是干什么的,解放后,你的成分就是什么。
几十年过去了,每每回想起自己将青春岁月一起流入到“斗、批、改”中,余秋雨都感到很痛心。他在《千年庭院》一文中这样写道:“我们这一代,很少有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完全没有被‘大串连’的浪潮裹卷过,但又很少有人能讲得清这是怎么回事。先是全国停课,这么大的国土上几乎没有一间教室能够例外,学生不上课又不准脱离学校,于是就在报纸、电台的指引下斗来斗去,大家比赛着谁最厉害,谁最出格。”
当时整个国家陷入混乱。上课的时候,占上风一派的老师如果突然兴致来了,可以号召下面的同学到另一个班里去,揪出被打倒一派的老师,进行现场批斗。过了一段时间,西风压倒了东风,被斗过的老师可能又会号召自己的学生向斗过自己的老师开火。老师之间尚且如此,年轻气盛的学生更是胡闹。遇上右派老师上课,学生可以在课堂上胡闹,老师也不敢制止,只能硬着头皮,自顾自地讲他的课。遇到调皮的学生,可能还会受到语言和身体的双重侵害。
那时所有的老师和学生都在盲目地“运动”着,学校里充满着各种各样的革命派别,大家各领风骚三五天,人人都处在高度的亢奋状态。这样胡闹了几个月之后,正当所有人都觉得无聊之际,更新奇的事情终于来了,这就是被称之为“革命大串连”的全国性行动。全国交通除了飞机以外,一律向全国青年学生免费开放,吃、住、行都不要钱,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去宣传革命思想也行,去观光看景也行,只要你是学生,或是还有没被打倒的年轻教师。于是从大学生到中学生,甚至还有少数高年级的小学生,都从各自的城市、乡村走了出去。所有的交通工具都被挤得满满的。
从农村回到城市没多久,余秋雨和同学接到上级的通知,又要再下农村。1968年12月,余秋雨打理好行装,来到了江苏省的吴江。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上级号召同学扎根农村!余秋雨的心颤栗了,他压抑,他愤怒,所有的前途、抱负和理想都将随之化为泡影,但他没有反抗的能力,他也无力阻挡汹涌而来的时代大潮。最让他难受的是,他的这种心态还不能表现出来,他和同学在一起时还要表现出乐观幸福的模样。他其实没有一点敌视农村的意思,他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要用这种怪诞的方式来锻炼学生,他更不明白,知识分子有什么错,为什么要将他们都弄到农村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难道把知识分子都赶到农村去就能发展生产力么?
三、余秋雨在“文革”中的写作
关于余秋雨在“文革”期间参加写作组的问题,很长一段时间炒得沸沸扬扬,人们都想知道,他在“文革”期间到底做了什么?这段历史,是与他读书、写作相关联的,也是他生命中不可割裂的重要部分。
对余秋雨的这段历史问题,1994年上海的一位杂文家在一份文学刊物上发表了题为《笔名谈屑》杂文率先发难。他隐晦地指到“一位名声显赫的权威曾是当年‘石一歌’的成员”。一石激起千层浪,揭批余秋雨“文革”历史的活动便拉开了“序幕”。其中,北京大学青年学者余杰发表的文章最有代表性,且言辞最为激烈。他给余秋雨扣上了“文革余孽”的帽子,并进行“拷问”,在《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一文中,他写道:“据若干余秋雨当年的同事透露说,他在写作组中的态度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因为他的出色表现和突出成绩,深受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青睐。如果不是文革结束,余秋雨也许会走上一条类似姚文元的飞黄腾达之路。”
这篇文章被多家报刊转载,并收入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想飞的翅膀》一书中,从此,文坛掀起一股否定余秋雨的旋风,对余秋雨真有意见的,假有意见的,嫉妒的或想借此出名的,纷纷在报刊撰文,形成一股蔚为壮观的风潮,一时间媒体对余秋雨的态度从赞扬变为贬斥。
然而,历史是不容改变的,当年和余秋雨在一个写作班子的胡锡涛先生否定了这一说法:“这些内容恰恰都说错了。余秋雨在写作组呆了大约三年半左右,他的态度不完全是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时候,在‘批邓’时期,他主动避开了一年多。他也不是‘主动’投靠写作组,而是鄙人推荐的。至于说他深受康、张、姚‘青睐’,纯系瞎编。康生在‘文革’后期已病倒,1975年就死了。张、姚对余秋雨也不认识,据我所知,1975年春天,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张、姚因不得志到上海“观察”,朱永嘉乘方便之机把余秋雨引见给张、姚,仅仅见了一面,就叫‘深受青睐’?至于说余秋雨‘也许会走上’姚文元之路,更是无稽之谈。余秋雨在1975年开小差溜走,恰恰是在张、姚接见之后!”
据胡锡涛介绍,他最初发现余秋雨的写作才能是在批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时候。当时写作组共有5个成员,即: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讲师余企平,该院戏剧文学系毕业生余秋雨,上海两家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助导,还有国棉十七厂造反派秀才。“……既然朱永嘉要我‘负责到底’,我不得不按我心中的计划,分三步走:第一步,我和大家都通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然后分工摘录观点,汇编资料,印成小册子;第二步,让余秋雨重写初稿,试试他的笔力;第三步,万一余秋雨初稿不行,只好由我主刀……出乎我意料的是,余秋雨写出的初稿,不是一篇大批判文章,却是一篇学术论文,文笔流畅生动,却毫无批判力度。”自然没有选用。
余秋雨后来还写了一篇散文《苏东坡突围》。胡锡涛称是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的块垒,表明自己不想成为“四人帮”利用的工具。胡锡涛回忆:“余秋雨是否从此摆脱一切干系、冲出重围了呢?没有,反而又陷入困境。1977年,是他‘三十而立’之年,但他无法‘立’起来,原因是他被‘揭、批、改、查’运动拖住了,有些人非要把他整倒不可。他曾三次上书市委,申诉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但均无下文。对上海写作组的小萝卜头、业务骨干分子等人员的‘揭、批、查’,整整花了三年多时间,进驻康平路89号的工作组换了三批。受到牵连的余秋雨也被审查了三年,对他的文章、修改稿及言论、表现等等,翻来覆去不知查了多少遍,始终查不出他有什么问题。余秋雨不甘心这样不明不白地消耗时间,于是,他悄悄地埋头读书,收集资料,为著书立说做准备,为重新站起来而奋斗。”
虽然胡锡涛已为余秋雨在文革时期的行为进行了解释,但还是有人继续对余秋雨进行批评。譬如张育仁先生就在一篇文章中讳莫如深地搬出余秋雨在《千年庭院》中的两段话,来证实余秋雨在文革中的过错,说是非常有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