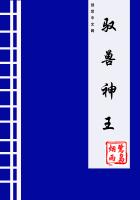李大胆理了理思路道:“说起这事儿已经是好几年前了。那一年我一个老乡在城里摆地摊被地头蛇打了,我与一个兄弟替他出头不料却中了埋伏。我们两个被打了个半死扔到一个十分偏僻的地方。我醒来时四周没有一个人,就在一个方向上隐隐有些亮光,我看了看那个兄弟他伤的比我厉害我只好背起他朝着那个有亮光的地方走。我那个兄弟分量不轻的再加上我身上也有伤可那一回我走了好长好时间也不觉得累。一直到后来路上来了一辆带着车棚的马车,那马车靠近我们时停了下来。棚子里一个老头伸出脑袋问我:‘你们两个怎么独自上路啊!”我当时一听这话也蒙了,因为‘上路’这话通常是有些特殊含义的。虽然我看那老者没有恶意可一时间也不知怎么回答就敷衍了一下说:‘是啊,就两个人。’那老者听了以后便请我们两个上车一起走。虽说当时并没感觉累但有车坐谁也不愿意走路。我就与那个兄弟上了车。上车后我们天南海北的聊了起来,可是没聊多久那人便叫车夫停了马车,还给我算了一卦算,完后便非要赶我下车。临走时还嘱咐我赶紧往回走千万不要到有亮光的地方去。最后我先择了听从他的劝告。背着我那个兄弟往回走,走到我最初起身的那个地方时忽然听到了一声鸡叫。不知怎么的我听到那声鸡叫时全身一抖,这才发现我一直是在地上趴着。一切就像是一场噩梦。”
“我说大胆,你不会是真的就做了场梦吧?”蓝教授问道。“开始时我也是这么想,但这也有地方说不通,就是我第二次醒来时我那个兄弟是趴在我背上的,就像我背着他时摔倒的一样。把人打晕了扔到偏僻的地方这很常见,可是谁会吃饱了撑的扔完人后还要把我们摞在一起啊?所以说这大活人去做纸糊的马车并不是毫无可能。”白鹤舞听了道:“你确定自己坐马车的时候是个大活人吗?”“这……这个……一连几个‘这’字后李大胆闭嘴了他显然不知说些什么好了。唐铁嘴儿听了似笑非笑的道:”会不会是那帮地头蛇中有个变态,扔完人后故意给你们摆了个搞基的姿势啊?”李大胆听了无奈的说:“这一点我也想过。但我没办法确定了。因为那几个地头蛇事后不久卷进了一场抢银行的案子,不巧又赶上了严打,很快就被抓去吃枪子儿了。”蓝教授道:“虽然确定不了但我看你这事儿十有八九是铁嘴儿说的那种情况。”“蓝老哥,这回恐怕是你错,你以为说不通的地方只有这个一个?”李大胆此言一处众人都转过头来,他便接着道:“先说我现在的这个老板吧!就是我以前提到的那个张大拿。我就是按着马车上给我算卦的那人的指点认识他的。还有一个地方我是在最近这两天才发现的,那就是我与那个老头闲聊时无意间在那老头身上发现了一张照片。那张照片里有一个男孩,年龄也就十来岁。我是在给你们送T恤衫的那天晚才注意到白老弟的,只是那次见面我还不太确定,所以那一次我见到你们时‘你’了半天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但照现在的情况来看张照片里的不是别人肯定就是白老弟你啊!”
说到此处白鹤舞心中一惊,李大胆说的那个老者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爷爷白空玄。而爷爷去的是什么地方再明显不过了。白鹤舞一想寻回自己的家人,此刻刚听到家人的消息却早已是阴阳两隔。一时间白鹤舞心潮澎湃、百感交集,也更加担心自己的父母。
回到李大胆家里就简单了。李大胆伤得比较重留在家里养伤,其余人喝些姜糖水去去寒休息一日,明天依然去石坊营子。
第二天清晨大家很早就起来了,看样子几个人精神都不错。只是李大胆还要挂几天吊瓶不能同行了。百般无奈的李大胆取出了几件兵器,一把短匕首,一把长刀就是那种日式的武士刀。还有一张弓箭和一把猎枪。只是可惜箭只有十几只,子弹也不过二十发。这几样东西倒是不值多少钱但保存的很好显然是主人的心爱之物。白鹤舞等人与李大胆相识不过短短数日,他却给人一种相交多年的感觉。见到李大胆带朋友如此真诚几个人也就不再客气,收下这几样东西后蓝教授又道:“建奎还有一件事要麻烦你一下,你得空时候去一趟林业科技报的报社,那报社离这里不远,就在市里。你去那里查阅一下今年2月10号的报纸,那上面有一篇报道食人树的文章,你去打听一下那篇文章是谁采写的。最好问清楚文章中的材料是从哪里来的。”李大胆听了痛快地答应下来。”
白鹤舞一行人告别了李大胆一路打听着朝石坊营子走去。
走了半日的山路终于看见远处升起一缕炊烟。村口处有一个茶点摊,四个人不看见吃的还好,这一看见了就再也走不动了。这个村子虽然偏僻但村里盛产产石头制品,再加上收山货的商贩也时常路过,所以这个摊位生意还算不错。
“掌柜的,前面是不是石坊营子啊?”茶点刚上桌唐铁嘴儿便急着问道。“嗯,没错,只是不知道几位是想请师傅还是要买货啊?”“请师傅,就是不知道村里最有名的是哪个师傅啊?”唐铁嘴儿接着问道。“要说手艺最好的自然是韩老锤韩师傅,不过他早已封锤。要请师傅只能找他的子孙了。”“我们请师傅不要他亲自动手,只是有些技术方面的事请他指点一下。”唐铁嘴儿道。“你们要是非找他不行的话就得赶紧往村里跑,跑慢了可就永远见不到他了。”“永远见不到?”唐铁嘴儿听到这话立刻站了起来。“对”摊主说完就转身离开了。“莫非这个韩老锤快死了。”胖大海道。“应该不会,要是快死了还怎么做技术指导?咱们跑去了也没用啊!”白鹤舞答道。我看咋们不要乱猜了,赶快着进村吧!一会儿就知道了。”蓝教授提议道。“老板算账”唐铁嘴儿这一声大喝没把摊主叫来却“震落”了旁边树上的一片树叶,那树叶不偏不正落在几人的桌子上。再去看那树叶,上面趴着一条毛毛虫,毛毛虫把那树叶咬了一个箭头型的窟窿,而箭头所指的正是村子外面的一片坟地。看样子往村里跑已经晚了。
四人一刻也不敢耽搁抄一条披荆斩棘的小路朝着坟地去了。
离着坟地老远就看见一支送葬的队伍,这队人马穿白戴孝排了足有半里地。“老白是不是这边不时兴哭死人啊?”唐铁嘴儿问道。“这后面的一般都是远亲,前面应该有哭丧的。”白鹤舞虽这样回答心里去也没底,因为即便是远亲这些人的表现也太过反常了一些。几个人加快了脚步一直走到到送葬队伍中间也没见到一个哭丧的。倒是各种杂耍表演一一应俱全,周围人更是笑的前仰后合。
再往前走倒是看见一口棺材。但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个老者骑在棺材盖子上四下里看热闹,嘻嘻哈哈的笑个没完,看上去比周围人还要高兴几分。
这一路走来四个人早已见怪不怪了,一直朝着送葬队伍的前方走去。到了队伍前面时四人才发现那老者一身寿服,虽然满头白发却精神矍铄,送葬队伍中扛着招魂幡的那个儿子少说也有八十岁了,由此推断这老者最少年龄也在百岁以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