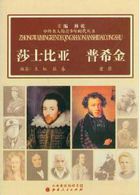凯丰乘坐大卡车来南岗火车站接人。见到久别的妻子和孩子,凯丰格外激动。尤其是看到王茜怀里的何亮,他一把抱过,不停地亲吻着。凯丰离开延安时,何亮还没有出生,想想自己离开延安后王茜所受的苦累,凯丰十分内疚地说:“别怪我没有关照好你。”
王茜鼻子一酸,心里一热,眼泪就流了出来。她能听到凯丰说出这种话,很是难得。在凯丰身边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凯丰不肯随便开口,更不肯轻意向人吐露心声,包括他的亲人在内。有这句话,王茜养育儿女的一切艰辛和烦恼也就被抛到脑后去了。
凯丰与吴德明等一一握手后,抱着何明、何亮,亲切地招呼着女儿说:“明清,走吧,我们回家去。”
凯丰住在哈尔滨南岗区的龙江街上。这条街实际上是一条大一点的胡同。这里驻扎着东北局的大部分机关。林彪夫妇、陈云夫妇、李富春夫妇、张闻天夫妇、罗荣桓夫妇、林枫夫妇、高岗夫妇、后来从苏联回来的李立三夫妇也住在这条街上,并在这里办公。
凯丰和家人所住的这户人家的户主姓傅,是马家沟比较富裕的人家,有很多房屋出租。他的女儿是共产党员,在市政府工作。
吴德明、韩玉霞和警卫员李顺清依旧分配在凯丰身边工作。
吴德明到了东北后,为什么还能留在凯丰身边,不再要求去前线?吴德明说:“一是那时东北局势很严峻,敌特暗杀、破坏经常发生,首长安全保卫必须加强。二是那时我很单纯,跟凯丰同志久了感情太深。刘少奇同志当时虽然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是大领导,但因跟他时间不久,不熟悉领导的生活习惯,只想跟在老领导身边。”
吴德明说:“凯丰同志宽宏大量,从不对同事和下级发火。在延安,刚到凯丰身边工作时,有一次为他倒洗澡水,木盆没把水装住,结果把窑洞的地面都打湿了,让凯丰洗不成澡,办不了公。因为窑洞既是凯丰的卧室,又是他的办公室,我吓得不敢见他的面。凯丰同志知道后,不但没有批评我,反而笑着对我说:‘你年纪小,没做过家务,如果这时你还在家里,还是母亲给你倒洗澡水呢。不要紧,实践出真知,以后你就会知道怎样倒洗澡水的。我告诉你,木盆里的水为什么会漏掉呢?现在是夏天,干燥的气温早把木盆烤裂了,水放进去,还不是烂篓子装泥鳅一样,走的走溜的溜吗?你应该在没倒洗澡水之前,先将木盆放在水里浸泡一会,让木板膨胀起来,将木盆的缝隙挤紧,这样才能让热水规规矩矩待在木盆里。’我听了他的指教,以后就照他教的法子做了。一九四七年春天,苏联给了我们一批苏式吉普车,分给每位首长一台。我对开车很感兴趣,就悄悄学了起来。就像小孩刚刚学会爬就想走一样,有一天,我开车去松花江边兜风,结果把一个工人师傅撞倒了,差点撞进江里。师傅住到卫戍区医院后,凯丰同志没有批评我,专门到医院看望师傅,向师傅赔礼道歉,还给了师傅慰问金。一九四七年冬,凯丰同志的小车由吉普车换成卧车。一次,我开他的车进库,因为方向没把准,撞到墙上,把汽车的油箱撞坏了。汽车一时修不好,害得他只能坐大卡车去开会。我爱人韩玉霞埋怨我,说我耽误了首长的工作。我以为这一次凯丰同志一定不会原谅我。当我写好检讨,送到他手里,请求处分时,他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看了下我的检讨说:‘学车就像学走路一样,跌了一跤,用不着这么严肃对待这事。就怪苏联老大哥的油箱钢板太薄了,不然汽车是不会开不动的。你说是吗?’凯丰的大度和幽默大出我的意料。凯丰同志说:‘学开车是好事,将来在战场上,在建设中,肯定能派上大用场。只是驾驶时要小心谨慎,尤其在大城市,人多车多,开不好就会出大事……’”
吴德明对凯丰体谅和关怀下级的评说,秘书董连璧也给予了认同。
二○○七年董连璧七十九岁,离任时为辽宁省体委主任,退休后住在沈阳干休所。他说:“凯丰同志牙齿不好,用不得硬毛牙刷。有一次,他叫管理员为他买一只软毛牙刷。可交代好几天,也不见管理员把牙刷买回来。那天我正准备去找管理员,管理员却焦急万分跑到我这里,问我沈阳市哪有羊毛牙刷。我这才知道,管理员还在为凯丰同志找牙刷呢。我想,再软的牙刷也不至于用羊毛做,就问管理员是不是把话听错了。管理员满头大汗说没有听错,凯丰同志要的就是羊毛牙刷。我去问凯丰同志。凯丰同志听了‘扑’的一笑说,不是羊毛牙刷,是软毛牙刷,是管理员听错了。其实管理员真没听错,是凯丰同志的普通话说得不好,加上镶有假牙,把‘软’说成‘羊’了。管理员敬畏领导,当时不敢多问,因此耽误了采购时间。凯丰同志知道原因后,没有批评管理员,而是作着自我批评说:‘看来我的萍乡普通话跟张国焘一样,说不好,这不利于今后工作的开展。打仗的时候,如果传错话,那是要付出大代价的。连璧同志,你和管理员是北方人,今后要多多给我纠错,不用怕。’”
凯丰身边的工作人员,无论在延安,还是东北,对中央领导的称呼都在名字后面加上“同志”二字。笔者认为他们有些古板,因为在记述他们的原话时,作者要增写好多文字。看看当今,有几个人对上级不是以“书记”、“部长”、“省长”、“市长”相称?副职通通不带“副”字,一律以正职相称,唯恐不恭冒犯了领导。有的甚至将领导称做“老大”、“老板”、“头”……可凯丰身边的工作人员众口一词地告诉我,名字后面加“同志”的称呼,是那个时代的严格要求。你若称他们的职务,他们会批评你。工作人员说:革命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现在想改也改不了。他们还说: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现在能继续这样称呼首长,相信首长九泉之下也会感到高兴的,因为我们毕竟没有忘记首长当年的教导啊。
三十八、拂晓中的哈尔滨
逃进深山老林的国民党残兵败将、土匪,和潜伏在城市里的日伪特务、国民党特工人员,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东北时,开始在解放区进行疯狂的破坏和暗杀。
哈尔滨的形势最为严峻。中共哈尔滨市委常委、中苏友好协会会长李兆麟,在一次赴约中,误入国民党特务窝点,喝了女特务孙恪龄的茶水后中毒,被三名手持短刀的特务连刺七刀,当场死亡。
林枫的警卫员陪同林枫去南岗铁道俱乐部看戏回来,被特务的子弹击中右臂。
在北满的合江、牡丹江、龙江、嫩江和松花江地区,先后有一百五十四名干部被杀害。
整排的苏联红军战士被打死。
一些干部战士被土匪特务开膛剖腹,暴尸街头,惨不忍睹。
…………
敌人的疯狂进攻一时间搅得人心惶惶。
为了安全起见,一九四六年十月,东北局机关家属一度搬到总部后方的佳木斯市,直到一九四七年才搬回哈尔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回顾当时的情况说:“不分兵打匪,到处不能站脚。不仅城市被土匪占据,乡村也是土匪的世界。”因此,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组织指挥部队,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在林海雪原中深入剿匪,在夜幕下的哈尔滨里加强锄奸、反特和肃清土匪恶霸的工作。
负责哈尔滨市委工作的凯丰,与东北局其他领导一道,在调查摸底清楚后,指挥部队迅速出击,处决了作恶一方的张作霖时代的大汉奸、恶霸姚锡九、李九鹏,捕获了国民党地下军头目姜鹏飞和大特务李明信,平息了八月二十日准备在哈尔滨进行的大暴动。这些行动为稳定东北局势,震慑敌对势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凯丰经常去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一次去北安省调查时,在火车上,他被一双有劲的臂膊抱住。
凯丰一看,抱他的竟是何长工!凯丰为在东北见到生死与共的老战友激动得跳了起来。
凯丰与何长工分别很长时间,知道他现在任职军政大学校长。一阵寒暄过后,凯丰就说:“长工同志,东北要干部,将来全国解放更需要干部,你的任务很重啊。”
何长工说:“是啊,百废待兴,纲举目张,干部是决定因素。凯丰同志,你是宣传部部长、大理论家,有时间给我的学员讲讲课怎么样?”
凯丰说:“就怕难当此任啊。”
何长工说:“宣传部部长都讲不好课,你还坐在这把椅子上做什么?”
“这……哈!”凯丰和何长工都笑了。
凯丰欣然应何长工之请,去军政大学讲了课。
直到今天,那些听了凯丰报告的学员,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依旧流露出对凯丰醍醐灌顶似的报告的敬佩。凯丰以《学习贯彻(七七决议)》为题,结合自己的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以及在东北农村调研的成果,提纲挈领、深入浅出地一讲就是大半天。他的报告,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打断。当他以《七七决议》最后一段话作为报告结束语结束演讲时,会场上的人都站了起来,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凯丰高亢地说:“从全国范围革命力量与反动势力的斗争的发展过程看来,革命力量在上升,反动势力在下降,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空前强大,国民党从未像今天这样丧失人心。在这样有利的条件下,只要我们全东北的干部认清东北的形势,团结一致,紧紧地与群众在一起,兢兢业业,一步一步向着奋斗目标前进,就一定可以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一定可以建立起巩固不拔的阵地,粉碎反动派的进攻,使东北和全国一起走上和平民主的新阶段!”
董连璧回忆说:在当时,能请凯丰作一次报告,真是莫大的荣幸。
王茜是位胆小而又文弱的女性。进哈尔滨之前,她经常听到和见到土匪对革命干部的极端残忍行为。因此凯丰每次外出,她不但要反复叮嘱小心,而且亲自检查警卫员的枪支子弹上膛了没有。每天夜里,凯丰不回到家,她绝不上床睡觉。
韩玉霞回忆说,一九四六年冬天一个冰雪夜晚,凯丰从乡下回来,又去督促有关单位给群众供暖,直到凌晨还没有回家。王茜由韩玉霞陪着,一会儿屋里,一会儿屋外,焦急不安地等凯丰回来。等到后来实在放心不下,她带上全副武装的吴德明,在城里四处寻找。天将破晓,当看到凯丰正在工人中间嘘寒问暖时,走了好几个小时的王茜终于瘫倒在雪地里。
回到家里,凯丰一边脱棉大衣,一边埋怨王茜说:“为什么要这样玩命?”
王茜接过大衣,挂往墙上说:“你才玩命呢!下了一天乡,连晚上都不回家。”
凯丰说:“十年军阀混战、八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得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现在是百废待兴的时候啊。全国解放战争刚刚开始,你看看,林彪、彭真、陈云、高岗、李富春、林枫等同志,哪个不是枕戈待旦、夜以继日地战斗着、工作着?”
王茜接过吴德明端来的一盆热水,蹲下地去,为凯丰脱下满带雪水的靴子,将他的双脚放进热水盆里,说:“你总是有理由,如果以后还要通宵达旦地工作,那我跟你一起去。”
“为什么?”
“外面太乱,我要为你挡一挡敌人从暗地里射来的子弹。”
凯丰一愣,睁大了眼睛望着王茜。
如果说盆里的水烫热了凯丰的双腿,那么王茜的话语更温暖了凯丰的心窝。
凯丰伸出手,为王茜扫着头上的积雪。当他的手抚到她柳叶眉下的伤疤时,停住了。
王茜抬起头,知道凯丰又在内疚自己和廖似光之间发生的那场不愉快的婚变,于是说:“不知道廖大姐现在在什么地方?日子过得怎样?”
凯丰的手在王茜的伤疤上轻轻地摩挲着,没有说话。
王茜说:“我对不起她。在白区,在长征路上,她吃过那么多苦,受过那么多伤。我不知道以后的人会怎么看待我们之间发生的事。”
凯丰叹了口气说:“都成往事了,别提它,我们只要好好地工作。”
王茜说:“我一定照顾好你,不使廖大姐失望。我要让廖大姐在全国解放后,再看到你时,你没有失去一根头发,全身的病全都治好了。”
愿望是美好的,也是温暖人心的。可愿望要得到实现,需要经过太多太多的、不可预测的曲折过程。有的愿望,往往就破灭在实现愿望的中途上。王茜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
一九四七年七月,凯丰带着李士彬、吴德明,由李顺清领着一个警卫班警卫着,前往北安省(现在齐齐哈尔东南)调查土地改革情况。王茜要跟着去。
凯丰吩咐说:“你的任务就是看好孩子。”
王茜要争辩,凯丰没让她开口。
王茜只能忧郁地望着凯丰走出家门,登上火车。
下乡不到半个月,凯丰接到紧急电话。电话说,王茜因为担心凯丰会遭土匪袭击,心情过于紧张,突发精神病,现在谁也控制不了她,她说她一定要亲眼看到凯丰安全回来。
在王茜的家族中,上三辈没人患过精神病,由此可见,当时东北的匪患严重到了何等地步。
由此可见,王茜对凯丰爱有多深,情有多重。
王茜患精神病后,经哈尔滨、沈阳等各大医院治疗都没能治好,恢复不了正常人的精神状态。
何明、何亮去医院看她时,她把兄弟俩锁进柜子里,并持水果刀,指着吴德明等工作人员,不让他们带走,说土匪要杀害老革命的后代。韩玉霞带着两个孩子睡觉,常常深更半夜被王茜吵醒,说特务来了,叫她赶紧带孩子转移。
韩玉霞说:“凯丰忙工作时,王茜经常去楼上办公室,为凯丰当‘警卫’。有时突然叫凯丰赶快走,说敌人马上就到,吵得凯丰无法工作。久而久之,两人发生了争执。有一次,凯丰不小心还把王茜从楼梯上推滚到了楼下。”
东北局领导见凯丰无法静心工作,经请示中央同意,就让王茜长期住在沈阳医院,由辽宁省委派专人护理。
王茜的疾病在东北治了二十多年,一直没有治好,一九七三年病逝于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