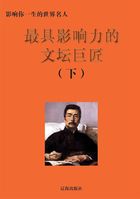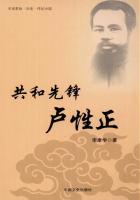你的眼睛疲倦了、累了,闭上你的眼睛……
--弗洛伊德
(一)
弗洛伊德离开维也纳后,首先搭乘“远东号列车”前往巴黎。当列车驶过莱茵河,弗洛伊德才舒了一口气。他和妻子玛丽及家人那宽慰的眼神表明:现在已经平安无事了。
到达巴黎后,儿子们已经从英国赶来迎接,玛丽·波拿巴也乘坐一辆汽车在等候他们,布里特大使也在欢迎的人群当中。随后,玛丽·波拿巴将弗洛伊德一行接到自己的住处,大家轻松愉快地度过了一天。
玛丽·波拿巴告诉弗洛伊德,他的存金已经全部被保护下来了。玛丽·波拿巴把弗洛伊德的存金都转到了希腊驻维也纳的大使馆,然后由大使馆寄给希腊国王,再由国王转运到希腊驻英国大使馆,最后转交给弗洛伊德。
当天晚上,弗洛伊德和家人离开巴黎,搭乘晚上的渡轮前往英国,第二天早晨在多佛平安上岸。
到达伦敦后,琼斯已经安排好了,给予弗洛伊德及家人以外交人员的礼遇,因此他们在多佛和伦敦都没有遭到行李检查和其他的例行检查。
琼斯甚至成功地避开了许多新闻记者的注意,用自己的汽车接走了弗洛伊德夫妇,然后将他们送到事先为他们安排好的住所中。
弗洛伊德对这个新的住所感到很满意。花园、樱草色的大厅和舒适的卧室,都让他感到清新。他来到这个新环境以后,仿佛忘记了自己已经是一位82岁的病人了。
对于一位已经80多岁、重病缠身的老人来说,这趟折腾真是让弗洛伊德感到痛苦不堪。不过,到达英国后的几个月里,至少有一部分肉体上的痛苦被他在英国所受到的欢迎所抵消了。欢迎他的人,不仅是那些有特别理由承认他的正式医学界人士和犹太人团体,还包括一些一般人士。
1938年,玛莎在写信给仍在维也纳的朋友说:
每天,我们都会收到许多欢迎他的来信。我们来这里只有两个星期,但即使信件不注明街道,只写“伦敦,弗洛伊德”也照样能够收到。想想看,伦敦有1000万居民,这不是很奇怪吗?
幸好有安娜的帮忙,弗洛伊德才能应付得了这些如潮水般涌来的信件。在这些信件中,有些是弗洛伊德的朋友写来的,另外一些则是陌生人,他们只是希望问候弗洛伊德,或者索取他的签名。
1938年6月23日,弗洛伊德的住所来了一群特别令他高兴的访客。他们是英国皇家学会的秘书们,带来学会的会员录,请求弗洛伊德签名。
弗洛伊德无法亲自到学会的总部去,会员录只能送到他的面前来,这种荣誉以往只有英国的国王才能享有。弗洛伊德十分高兴,他写信告诉茨威格说:
“他们留下了一册复制本给我。如果你来到里,我可以将牛顿和达尔文的签名指给你看。”
在科学和文艺界,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生物化学家威斯曼、着名作家威尔斯和茨威格陪同西班牙画家萨尔瓦多·达利前后来拜访弗洛伊德。
但是,弗洛伊德并没有忘怀自己的祖国,他很想念维也纳。他在写信给艾丁根说:
获得解放的胜利心情是同忧伤交错在一起的,因为我始终热爱着那所我刚刚从那里被释放的监狱。
每当想起维也纳的时候,虽然他也可以回忆到许多发生在那里的不愉快的往事,但同时也让他又一次留恋地想起自己与父母、子女在那里共度的天伦之乐,想起与同事们一起钻研人类精神领域的奥秘的情景。
可是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啊,都是那可恶的法西斯!它不仅夺去了弗洛伊德及千千万万善良的人们的家庭,也夺去他们的自由生活,夺去了他们的事业。
对法西斯的仇恨,又使弗洛伊德回到了现实。他懂得今后应该怎样生活,他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和无数新人们身上。
(二)
1938年7月,在休息了一个月左右,弗洛伊德又开始工作了。现在,他所研究的问题是“归纳精神分析的教义,而且以最简单的形式和最清晰的字句来叙述它们。它的用意是不强迫别人相信或引起盲从”。
此时,在英国和美国,精神分析就要被广泛应用了,那是弗洛伊德没有预料到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几个月以后即将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期间,多数交战国家都开始聘用精神分析专家为他们自己的心理战运动提出建议,同时也分析敌人的心理战。
在这期间,弗洛伊德的学生恩斯特·克里斯就准备在英国组织一个特别的政府机构,分析德国人的广播;后来,美国也这样做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开始,使用精神分析专家来治疗战争伤患的范围,要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广泛得多。
8月1日,国际精神分析学第十五次大会在巴黎召开了。为了听取弗洛伊德在会上对所争论问题的意见,欧洲委员会的成员们都到弗洛伊德家中座谈,并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平息了双方的争论。这次精神分析学大会,也是弗洛伊德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大会。
随后,弗洛伊德开始安下心来写《精神分析大纲》。他重复了各种基本的理论,以“自我”、“本我”和“超我”的结构来叙述,而且许多地方都暗示他有新的观念需要详细地叙述。但遗憾的是,他永远没能实现这一愿望。
1938年底,弗洛伊德搬到了位于马斯非德花园的一幢宽敞的老宅中。这时,他的家具和私人用品以及从维也纳运过来了。因此,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的书房在这里又重新建立起来,安娜将父亲书房的家具都放在与以前同样的位置,把同样的雕像和画都放在桌子上,这让弗洛伊德倍感亲切。
弗洛伊德的病情还在恶化,来到伦敦后,他又接受了一次较大的手术。医生确认,癌症已经扩散,手术的目的也只是尽力消除癌细胞,减轻病人的痛苦。这是弗洛伊德动的最后一次手术。
到1938年秋,弗洛伊德的精力已经所剩不多了,他需要经常休息,否则就会感到不适加重。这时,他将自己的所有精力都花费在他最后一篇震撼人心的论文的写作上,那就是《摩西与神教》--三篇论文和几年前写的序文。
1939年3月,《摩西与神教》分别在荷兰和德国出版。通常认为,《摩西与神教》是弗洛伊德比较不成功的作品。首先在于,这本书被弗洛伊德写了改、改了又写,结构也多次动摇;其次,年纪大了也是一方面的因素。琼斯在私下曾向一个书评人表示:
“弗洛伊德在晚年时引述别人的话时特别挑剔,他只引用支持他的特殊论点的话。这完全不像他早年时,会看完整篇文章后再斟酌。我觉得,这种习惯与他精力所剩无几有一定的关系。”
在写完《摩西与神教》后,弗洛伊德继续坚持写《精神分析大纲》一书。但由于病情急剧恶化,他不得不中断此书的写作,并且再也没有继续写下去。
在1938年的中旬,医生就在弗洛伊德的口腔深处又发现了另一个肿瘤。他的私人医生舒尔写道:
起先,它看起来像是另一个骨疽,但不久以后,这个组织被破坏的情形显得异常严重。这时,医生对弗洛伊德的病情发展程度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意见,他们不能确切地控制它。1939年2月,巴黎居里机构的拉卡沙内尔博士抵达伦敦,指导我们实施放射线治疗,同时还进行了许多试验。但结果令人叹息,癌症很快又回来了,而且它的位置令我们无法再次进行手术。到了1939年3月,我们都知道,我们最大的希望只能是设法减轻他的痛苦了。
到这时,弗洛伊德的生命还剩大约6个月左右的时间,但他依然坚强地面对命运,拒绝服用可以减轻疼痛的药物。直至去世前的几个星期,他还在为几个病人进行精神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