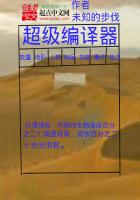在来到长冲村时,张绍鹏曾随乡亲们一起去过逝者杨东来家屋后看过那个夺命的水窖,当时没看到任何鬼物,但在那薄薄的雾气中,他分明感受到了异常浓烈的深深怨气。此后两次看到那漂浮在杨家屋前的鬼影,前后联系起来略一想,已知杨家这少见的惨剧定然另有别情。
虽然这些时日实在不想再参与这些玄幻的奇事,但内心那种天生的怜悯却又不断吞噬着他的决心,特别是看到杨家二儿子杨家贵和几个长冲村民脸上透出的隐隐晦气,心里更感坐立不安。
毕竟经历了这么多,张绍鹏已不是那个冲动的少年了,所以吃完午饭后,他找了个机会把刘萍叫到了屋后,想让她把某些事情告诉主人家。
刘萍双眼已经哭得有些红肿,还未等张绍鹏开口,便抽泣着道:“都是我不好,没有多留我姐在家多住两天,都是我不好呀!”
张绍鹏安慰道:“这事另有原因,怎么能怪你呢?”
“怎么不怪我?本来我姐和姐夫带着周成和斌斌初二就到我家去拜年了,住了几天后姐夫说要回来清洗水窖,我爹妈极力挽留,小周成也不想走,他们都要多住几天了,我却在那多话说过两天开春后就要下雨了,那时清洗水窖要费力得多,叫我爹妈别再留了,结果他们就回来了,谁知道才回来两天就出了这么大的事。你说这怪不怪我,如果我不要多嘴,难说现在我姐他们还在我家玩呢!”刘萍话里满是自责。
张绍鹏看刘萍目光涣散,悲伤中还透出那么一丝不易察觉的绝望,心里有些紧张,过了好晌才轻声道:“节哀顺变吧,这不能怪你,好多事情是避免不了的!”
“怎么不怪我了,这明明就是可以避免的。”刘萍开始有些声嘶力竭。
张绍鹏一震,忽然双手一下捧住刘萍的脸说道:“刘萍,看着我!”,同时心里转念了一遍清神诀,之后大声喝道:“醒!”。
刘萍停住哭声,怔怔地看着张绍鹏,有些茫然地道:“张绍鹏,怎么你也在这里?”,待发现脸蛋埋在张绍鹏双掌之间,急忙挣脱,一丝红霞映上脸颊。
张绍鹏有些尴尬,搓了搓冻得有些冰冷的手掌道:“刘萍,你刚才有些迷糊了,我是叫你过来向你讲一下你姐的事!”
刘萍一听又低泣起来,张绍鹏赶忙正色道:“你信不信得过我张绍鹏,我可是曾经救过你的那个抓鬼人呀!”
“你救我的事我一直没忘记,有什么事你说吧!”刘萍有些不耐烦,当受人恩惠被提在嘴上估计谁都高兴不起来,何况是在这种情形下提起。
张绍鹏也顾不得这么多,直接问道:“你姐家的弟媳,就是那杨家贵的老婆,是不是脸上嘴角有一颗大大的黑痣?”
“你说的是斌斌的妈妈汤倩姐?她虽然有一颗痣,但长得却是非常漂亮的,只可惜生斌斌时……,唉!我姐夫一家从老到小善良本份,却遭受了这么多苦难,上天可真是不公平,老天无眼呀!”刘萍叹道。
“那就是了,我怀疑你姐家这次出事与她有关!”张绍鹏见印证了自己的想法,便也不再拐弯抹角。
刘萍瞪大眼睛道:“这怎么可能,那汤倩姐可是已经去世将近五年了呀!”
张绍鹏见刘萍有些不相信,便小声道:“我可不是想随时提在嘴上,你不记得你刘家那姑祖奶奶刘书雅死了多少年,不一样可以来缠上你吗?”
刘萍听后心头大震,忙问道:“难道你看出什么不对劲的吗?”
张绍鹏见刘萍终于相信自己了,便将今天两次看见汤倩鬼影的情景详细地讲了出来,末了对刘萍道:“我感觉汤倩身上带有很强的怨气,那水窖里残留的怨气应该也是她留下的。然后就是今天她看自己老公和有些乡邻的那种眼神,我估计这件事情还远未结束。”
这下刘萍是真惊到了,因为张绍鹏的神奇自己可是亲身体验过的,所以清醒后对他的话自然是深信不疑,忙问道:“那该怎么办?”
张绍鹏见刘萍那么信任自己,近一个月来的失落与决心瞬间抛诸脑后,对刘萍道:“我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其实那次你在学校被你姑祖奶上身的事最后还是那龚师傅解决的,所以如果要我出手的话,我能做的最多也只能是抓住那怨气冲天的死鬼汤倩,但那有什么后果可不是我能预知的,再说要抓住她还没有十足的把握。”
见刘萍有些失望和恐惧,张绍鹏又说道:“先这样吧,你去跟杨家你那姐夫的二弟把情况悄悄说一下,让他去请道士宋大庸宋法师来做个法事,看看能不能将汤倩的怨气化解,只要把她的怨气消了,可比抓住她还要管用呢!”
刘萍听后道:“好吧!,就照你说的办”,想了一想后又问张绍鹏:“你的意思是不是请人做做法事,一定要请什么宋法师么?”
张绍鹏郑重地点了点头道:“我记得小时候的一些事,在我们方圆土地上好像听说就数宋法师最有道行,请他来是最有把握的。”刘萍嘴角动了一下,轻声说了声“谢谢”后就回屋找杨家贵商量去了。
当天,张绍鹏没有随父亲回家,而是一直待在长冲村杨家,在法师没来之前,他始终有些放心不下这里的情况。当然,他内心也知道,让他留在这里的,也许还有另一个原因。
下午时分,所请来的法师便到达了长冲村,来者一共五人,除宋大庸和两个徒弟外,还有一老一少张绍鹏很不想见到的人,老的是胥家舅公胥仁天胥大先生、少的正是“守龙一族”新任族长胥子平。
请宋大庸是杨家贵叫的乡亲,但是胥氏祖孙,听说却是刘萍跟父母说后让人去的。
不过好在刘萍一直在张绍鹏身边,虽然两人没再有交谈,但这对张绍鹏来说已然满足无比了。只是想起请胥子平是刘萍的意思时,又忍不住涌起一股酸酸的感觉。
见到胥大先生时,张绍鹏过去轻轻地叫了声“舅公”,对身边的胥子平直如视而不见。胥大先生见状后随便应了一声,当时倒也没说什么。
宋大庸已经老迈孱弱到需要徒弟搀扶了,到杨家后先在家堂的开壇作法也是由徒弟进行的,他只是披着个道袍坐在一边看着,偶尔跟着徒弟的镲鼓声吟唱两句。两个徒弟随后又到屋后水窖边祭祀好一会,才进屋接着在家堂前敲打念唱。
在此过程中,胥家祖孙一直坐在杨家院里同前来帮忙未散和看热闹的乡亲们闲聊着。张绍鹏倒也顾不得计较刘萍和她父母也在招呼胥子平他们了,在两个年轻法师到水窖边祭祀时便跟了去看,见他们进屋时,杨家贵手里的引魂幡后分明紧跟着七个逝者的亡魂一直到他家堂屋,而水窖边原来那股怨气在祭祀完毕后竟已经散完散尽,不由对两个法师充满了敬佩之情。
堂屋的法事直做到天黑,而在这个法事上,张绍鹏对宋大庸师徒更是非常崇拜了,因为随着两个年轻法师的唱念,张绍鹏看见这一家七口的亡魂竟然从最初的浑浑噩噩到渐渐清醒,后来竟携手一起到宋大庸身前跪下磕了个头,宋大庸几句唱念后,一群身着铠甲面无表情的阴魂闯进杨家的家堂,拉着兀自跪着的七个亡魂风也似的消失在夜空……
旁人只看到那传统的祭奠法事在进行,根本不可能看到张绍鹏眼中的一切,但除了宋大庸师徒外,还有两人是肯定看见了的,那就是胥大先生和胥子平祖孙。因为那群进来押解杨家亡魂的阴兵进门时,见到已经移步到堂屋的胥家祖孙时,领头那白脸是先漂到他们前面抱了抱拳后才过去押解亡魂的,张绍鹏见胥大先生微微点了下头算是打招呼,而胥子平则把头一抬,一幅爱理不搭的模样。但张绍鹏也有些尴尬,那群阴兵出门时见到角落里的他是,都向自己的这个方向躬了下身后才离去,而那时他显然听到了胥子平鼻子里发出不屑的哼声。
待将七个亡魂送走后,宋大庸让两个徒弟收了法壇,对胥大先生道:“胥先生,宋某只能做到这了,我这是治标不治本,原先那孽障就只有靠您了!”,胥大先生虽然比宋大庸年长不少,但身子骨却要硬朗得多,见宋大庸如此说,赶紧过来扶住他道:“宋法师客气了,我胥仁天近年遇事多次得宋法师相助,可是感谢你的还来不及呢!”。
宋大庸又和胥大先生寒暄半天后,不顾众人盛情挽留,竟执意带两弟子连夜离去。
张绍鹏悄悄地跟宋大庸师徒走出院子,虽然自始至终他都没能和他们讲过一句话,但总觉得这老法师和自己特别有缘,见他们离去便想偷偷送他们一程。
走出不远,夜色中的两只电筒突然倒转过来一下照在了他的身上,张绍鹏有些不好意思地大声道:“宋法师慢走!”。
不想宋大庸趴在一个徒弟的背上折转身来到他面前,开口问道:“你是张家村胥老太的孙子吧!”。张绍鹏一怔道:“法师认识我?”
宋大庸道:“你长大了,有些不认识了,但看刚才地殿兵士看你的神情,我已经猜出几分了。听说请我们来也是你的主意,呵呵!这可承蒙你的抬举了!”
张绍鹏知道他能看见那一切倒也不奇怪,于是道了一声:“谢谢法师出手相助!”
“多年前我曾有缘到过你家一次,那时便已推算出你的与众不同之处,而你奶奶胥老太的葬礼上,我也曾有幸前去略效薄力。想不到真是代有人出呀!”,宋大庸喘了口气后叹道:“其实以你之力完全可以解决的呀,怎么又去请我和胥大先生呢?”
张绍鹏不好意思地道:“我那舅公可不是我请的!不过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才想起您的。”
“怎么会呢?你张家那《三界法语》何等厉害,我这一宗的祖上可也是学到鬼谷子先生道传的《三界法语》皮毛,才渊源流传了这些年的。你身为圣书传人,自是不可同日而论的呀。”宋大庸有些疑惑地道。
张绍鹏似懂非懂,一时也不能理解宋大庸的话语,只得笑了笑道:“宋法师过奖了,我真的什么也会的!”
宋大庸点了点头道:“你还小,以后长大了,不论身居何位,可一定不能把我华夏祖上留下的传承给荒废了!”
张绍鹏应了一声,见宋大庸弟子背着他转过身去,再不打话走了,便也回身返回杨家,从下午作法开始,他就没再见到汤倩的鬼影,说起来心里还是有些放不太下。
来到杨家堂屋,堂屋大门竟然紧紧闭着,主家的几个村邻和刘萍父母等亲戚聚集在院里,一问后听说胥氏祖孙和杨家贵父子在堂屋内继续作法,不准大家进入。但当得知刘萍也在堂屋内时,张绍鹏有些失落,便高声呼叫起她来。
听到他的叫喊,胥大先生苍老的声音高声道:“你进来吧!”。张绍鹏便在众目睽睽之下打开堂屋门走了进去,然后又顺手把门给关上。
进到屋内后,他便知道自己先前的担心有些多余了:汤倩那鬼影此时正战战兢兢地跪在杨氏的家堂前,胥子平手持一方大印正在厉声问着什么,杨家贵紧紧地抱着儿子,一起呆呆地看着汤倩,刘萍坐在他身边也是睁大眼睛看着,只有胥大先生坐在另一旁无事儿事的翻着一本陈旧的万年历样的书。
张绍鹏没好意思和大家的招呼,偷看了一眼刘萍,见她看着汤倩全然没留意到自己,便在胥大先生身旁坐下。
只听胥子平对汤倩道:“还有什么话要说?”
汤倩跪在那好像很是惊恐,身上也全没白天看到时的那种让人压抑的气场,几次想要起身,无奈都被胥子平手上的大印发出一道黄光给逼得动弹不得,嘴里叫道:“为什么不放过我,我已经说了缘由,为什么不放了我?”
胥子平冷笑道:“你先前为什么不放过你的家人,他们可都是你最亲的人,给你敬奉香火为你祈福的人呀?要不是看在你家孩子的份上,此时你恐怕早已魂飞魄散了!”
“我说过了,我是有原因的,他们是罪有应得!”,汤倩恶狠狠地回道。
胥子平低低地念了几句,张绍鹏见竟招来了牛头马面,那怪异的样子突然从堂屋地底冒出,把杨家贵和刘萍吓得轻呼了一声,倒是那小斌斌好奇地盯着直看。
见自己被牛头马面抓在手里,汤倩绝望地哭泣着,但已经不再挣扎。胥子平淡淡地道:“让她七世为猪,挨尽七刀还清孽债后才得再世为人!”。牛头马面也不说话,点了点头后抓着汤倩一闪不见。
杨家贵怀里的小杨斌低声问道:“爹爹,我妈妈被那两个戴面具的人抓到哪里去了?”
杨家贵眼含泪光没有回答,只是低低地道:“爹抱你去睡好不,我一会就来陪你了!”
杨斌点点头,被父亲抱起时突然指着胥子平奶声奶气地道:“大哥哥你让我妈妈做猪,你不是好人……”,还未说完便被杨家贵捂住了小嘴。
张绍鹏见胥子平眼里露出一道凶光,不由感到一丝冷意。待见胥子平温柔地笑看刘萍,而刘萍也是面带微笑迎了上去时,这些天以来那种心灰意冷的感觉又重新浮上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