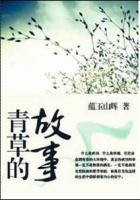女人挨近了男人的身边。
他们已经许久没有像从前那样肆无惮忌的愉悦了。他们的心里一直需要火,需要那团燃烧成灰烬的火。男人不再像从前那样的,对女人是那样的渴求了。另一种欲望,占有了他的心。
女人虽然那样亲昵的抚摸着他,在他的心中,产生出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却不是来自生理的本身。
那是一种渴求揭破大自然秘密的冲动。
从这一刻开始。
他已经褪却了野人的原性,那本能的、原始的、野性的欲望。
他学会了思考,学会了探索,开始渐渐的冲破了一般动物的界限。
他,已经可以称之为人类了。
野人,是一种动物,一种森林之中,和虎、豹、狼、猪等等相差无几的、野生的动物。他们活着,就是为了吃饱肚子,躲避天敌,顺其自然的满足自己生理上的需求,繁衍着后代。自然的生,自然的死。对于大自然,他们只求温饱,没有任何其它的索求。他们只要能和伴侣,和自己的家人,快快乐乐的在一起,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从需要火的那一天起,他们已经脱离了原性,开始了对大自然无穷无尽的索取,直到大自然也学会了报复。
从需要火的那一天起,爱情也不再像从前那样,虽然粗野,却是真正的神仙伴侣,不离不弃。爱情,也学会了,如火产生的那一天,虽然熊熊而来,却很快会被一场飘泼而来的大雨,冲洗的,干干净净,只剩下一堆烟灰。
男人烦躁的推开身边的女人,一个人走出了山洞,仰望着蓝天。那说不出的冲动,已经深深的刻入了他的骨髓:他必须知道,那团火从何而来,为何会转眼间,就可以排山倒海一样,摧毁那样一片偌大的森林,烧焦那么多鲜活的生命。他骨子里开始萌发出一种想要征服的欲望。
男人,也许正是从这时,开始了想要征服世界。
他想要征服的世界中,也包括:女人。
严格的来说,在很多很多的时候,只有男人,才能称之为“人类”,女人,只能称之为“类人类”,她们常常是男人所征服的世界中的一个附属品种。
这种格局,从原始森林中,已经开始了。
女人现在不再在乎,那火从何而来,又回归何处;那烧山鸡的味道,虽然曾经那样的引诱着她,日日夜夜难以入睡。然而,当她发现,自己的男人,已经因为那团火,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不再是从前那个,整个身心里,装满的都是她的时候,她忽然间清醒过来:她意识到厄运就要降临了。
她开始千方百计的在男人面前搔首弄姿,展现出千般柔情,万种风骚,想要男人忘记那团火,那团已经湮灭的火。
太迟了。
男人的心,已经被火整个的咬住了,不能自拔。想要揭开秘密的欲望,充斥了他的身心。
女人后悔莫及,她渐渐的学会的反思:那团火来临的时候,男人没有走进去,他害怕,他曾经是那样的不敢靠近。他退缩着,试图远离。然而,自己是那样义无反顾的走进去,想要弄个明白,看个清楚。
女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那样的好奇心,非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可。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她情愿和从前那样,吃着血淋淋的肉,喝着腥臭的血,在这片森林中,和自己深爱的人,怡然自得的享受着这天地间的那一片清纯。
她第一次尝到了哀怨的滋味,那是一种万箭穿心,求生不能,求死不能的痛。
她第一次用热切的目光,换来一种冷漠的回应,那淡然的神情比那团火,更加灼伤了她的五脏六腑。
她第一次流下了眼泪,那咸咸的滋味,腌透了她的每一寸肌肤。
当她倦缩在洞壁的一侧,任由泪水滑落的时候,男人仿佛刚刚睡醒了似的,记起了从前的快乐时光。他走过去,用自己长长的手臂,擦干了她的眼泪,轻轻的亲吻了一下,不知道是抚慰,还是爱惜。他吻她的时候,是那样的轻柔,像是怕要触动她的痛。
一股寒气冰冷的刺穿了女人的心。
他不再像从前那样全心全意的亲吻着她了。他从前总是那样热切的,用饱满的热情爱恋着她,仿佛她是他整个世界的唯一。他的目光中,只能显现出她的影子。
那样的快乐一去不复返了。
他抱着她,像是不得不给予的施舍,和恩赐。
女人的眼泪决堤而出。
女人,从这一刻开始,有了眼泪,并常常用自己的眼泪,来清洗自己受伤的心。
男人看着怀中的女人,手足无措。他第一次知道,女人原来是会哭的。他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这样的伤心无助。他依然是爱她的,他依然是她的男人。他并没有远离他,他还在她的身边。
她为什么要哭,还哭的那样的伤心呢?男人第一次不明白女人的心。
他的女人,曾经是部落中最勇敢的女人,她敢在最高的枝桠上跳跃,敢攀登最陡峭的山岭。他的女人,也是部落中最美的女人,身上总是透射出蠢蠢欲动的诱惑,让人迷恋,让人沉醉。
现在,这个女人,如一只垂危的野兽,浑身不停的抖动着,可怕的哭泣声,似乎那一场大雨。
男人定定的看了半晌,心间忽然一裂,很痛:他第一次发现,眼前的这个女人,原来是这样的令人不堪入目,她哭泣的样子,几乎使身上所有的肌肉缩成了一堆,横七竖八的乱放在一起。
他叹息了一声,走出洞外。冬日的森林,虽然是那样的枯萎着,在他的眼睛中,竟然也看出了一分颜色来:到底比洞里那个哭泣着的女人,要好看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