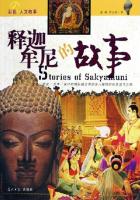王小波在这些作品里,基本是用简单的人物造型和人物关系,粗线条的故事情节和故事片断,带有戏谑幽默色彩的语言文字,向读者描绘了荒唐时代里人物的荒诞生存状况:权力控制无所不在,人活着没有了任何尊严,对理想和崇高的盲目追求走向了它的反面,僵化而缺乏人性的教育造就了一个无智而无趣的世界,对欲望的清教徒式的防范带来人性的畸形发展和集体性的病态的好奇心……在王二寄身的矿院,贺先生只得以跳楼自杀来换取人的尊严,绝顶聪明的刘先生为了苟且偷生却只能装傻,久而久之弄假成真,最后竟为一只鸭子馋死;从香港回归大陆的李先生,最难以理解的是自己堂堂一个博士,回到大陆来,保卫东,保卫西,最后保卫的竟然是大粪:“如果这不是做噩梦,那我一定是屎壳郎转世了!”偏偏这确实又是真的(《似水流年》)。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种种怪现状更发生在“王二”自己身上,六岁被大炼钢铁划伤了手,在身体上留下了永久的灼痛感;14岁因回答“活不活的没什么关系,一定要吃什么东西”而被老师骂作一只猪,在精神上留下了抹不去的创伤;进入豆腐厂后更因为一幅拙劣的不是自己画的女人人体图而沦为被帮教、被改造的对象。该篇以类似于成长小说的形式,将时代的风云变幻寄寓于个人的切身成长经历与人生体验之中,悲剧性的历史意蕴和人生处境均以滑稽、反讽、笑谑、夸张、幽默的笔调出之,对一个荒诞时代的解剖,真可谓尖刻犀利、入木三分。其中对X海鹰与王二关系的描写,最富有荒诞意味。在帮教后进青年的过程中,团支书X海鹰与王二建立起了近似于法官与死刑犯间的关系。面对日复一日的盘问与帮教,王二只好在对X海鹰施以强暴的幻想中获得一丝乐趣,而X海鹰则在帮教的过程中对王二与“有颜色的大学生”间的关系产生了浓厚的、不能自主的兴趣,并最终与王二发生了肉体关系。本篇虽标题为“革命时期的爱情”,但X海鹰与王二间的关系却是与通常所谓的爱情无关的。X海鹰小时候看了太多渲染革命战士经受敌人严刑拷打的电影,梦牵魂绕的就是地下工作和拷打虐杀,但眼前的平庸的世界却不能给她一个经受考验的机会,她于是投身于一种白日梦式的与敌人的战斗中,并在这种虚拟的战斗中扮演了一个受难者的角色,将自己与王二的每一次性关系都叫作强奸,每次和王二做爱,都要说他是坏蛋、鬼子、坏分子,把王二骂个狗血淋头。本应属私人领域的自然、健康、快乐的性爱,在这里却与公共的幻想产生了奇妙的勾连,衍变为革命/反革命间的受虐/施虐游戏,革命的理想与私人的情感因此出现了双重的异化。从自然人性的角度来说,X海鹰所需要的也许只是性爱,但单一僵化的革命传统教育却使她无法理解自身的欲望,这种欲望只有在经过巧妙的置换和伪装后才得以实现,其结果,一方面是扭曲了自然的正当的欲望,一方面也亵渎和嘲弄了革命的神话。这种带有双重异化性质的关系描绘,堪称王小波所说的“我看到一个无性的世界,但是性爱在混沌中存在”的形象注脚。
关注王小波的读者会注意到,王小波喜欢写男女的情爱(包括《似水柔情》涉及被世俗视为超常的同性恋情感),喜欢经常性地提及从人体地形学来说属于下半身的人体器官,但我们也注意到,王小波绝少为性爱写性爱,他更热衷于通过性的描写和身体的描写建立起一种性与文本的政治,即通过对性和身体的描写来呈现政治的无孔不入和权力的至高无上,以及人物通过性和身体发起的对于政治和权力的抵制和反抗。《黄金时代》是一个典型例子。作品一开始就将陈清扬置于一个自己无力自拔的荒谬处境中:陈清扬下山来找“我”讨论她不是破鞋的问题,尽管“我”可以从逻辑上证明她不是破鞋,但“我”偏说她就是破鞋,而且这一点毋庸置疑:
“我对她说,她确实是个破鞋,还举出一些理由来:所谓破鞋者,乃是一个指称,大家都说你是破鞋,你就是破鞋,没什么道理可讲。
大家说你偷了汉,你就是偷了汉,这也没什么道理可讲。”这种一眼可以望穿的混账逻辑与“我”的道德品质无关,作者一是用它来宣示群众(“大家”)舆论特别是有关生活作风问题的群众舆论的非理性本质,二是用它来传达创作主体的一种观念和态度:在一个非理性的社会和时代里,要讲道理和究明真相不仅是一种徒劳之举,而且会使自身也构成一个荒诞的姿势。可取的反抗途径,是勇敢地面对一切不讲道理的指控,甚至坦然承认莫须有的罪孽。对于陈清扬来说,面对一个“把一切不是破鞋的人说成破鞋,而对真的破鞋放任自流”的生存环境,不仅不惧怕被称为破鞋,而且乐于成为真正的破鞋,这就完成了对生存时代和周边社会的最大蔑视和嘲讽。而对处身“革命时期”的王二来说,随时准备承认自己是一条猪以换取自身的安宁,实际上也就预示着可以借此逃离那个时代的荒诞的人生哲学,以貌似屈从、接受无边的非人性的外在力量来完成对权力、政治力量的抵制和嘲讽。这里既包含了个人在一个无理可论的时代里由无可奈何的处境所带来的苦涩和心酸,也显露了一种外表佯狂愤世、内里清醒自信的特立独行的人生姿态。
在以“王二”为主人公的小说里,王小波反复地描绘政治和权力的力量如何折辱着人的尊严,如何以各种无孔不入的方式强行突入私人生活领域,甚至以思想和道德的名义,将最为隐蔽的男女性爱场域转化成为大观式的群众娱乐活动(批斗会),同时也通过描绘形形色色的政治和权力力量如何通过种种置换和改装为性爱所代表的自然、原始力量所瓦解,从而构成了一个政治与性爱犬牙交错的文本领域。在这一领域里,对荒唐时代的控诉不再停留于政治的层面而深入到了文化、人性的层面,同时对性爱的描写也不是局限于相对独立的男女两性空间。同王安忆的《岗上的世纪》比,王二和陈清扬共同逃到山上度过的时光,显然带有政治反叛的痕迹,换用《似水流年》中的话来说,那是一种堪称“在酷刑中勃起,在屠刀下性交,在临终时咒骂和射精”的行为。
当然,随时准备承认自己是一只猪以获取安宁只是王二的反抗形式之一。在王小波的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是规训与抵抗。其中的叙事人王二(在“白银时代”系列和“黑铁时代”系列中则以“我”、“我舅舅”、“我小舅”形象出现),和周围的世界构成的是一种规训与不合作、惩罚与逃离的关系。王二总是以调皮捣蛋、不服管教、特立独行的伪恶者形象出现。在幼儿园和学校,他是学生干部和老师的帮教对象(《三十而立》);在知青点,他是军代表的专政对象(《黄金时代》);进入工厂,他又成为老鲁和X海鹰一类领导的惩诫对象(《革命时期的爱情》);甚至进入到私人生活领域,他也是自己的情爱对象所拯救的对象(《我的阴阳两界》)。面对形形色色的规训力量,王二很少是以愤世嫉俗的零余者形象出现,而是以鬼精鬼灵的逃离者、抵抗者、忍受者的形象出现。他或者是奋起反抗,持枪与军代表对峙;或者是拔腿逃避,与同学们、老鲁们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或者是默然接受,怀着一种沮丧悲观的心情由人生的阴界进入到阳界(《我的阴阳两界》)。但不论王二最终采取了哪种抵抗的形象,他对于来自外界和他人的规训力量的反感是共同的。军代表对王二的指控让他想起中国可能已经恢复了帝制,军代表已经当上了当地的土司;走正路、抢头名的人生设计,在王二的眼里不过是挣死后塞入直肠的那块棉花——一钱不值;而在中国的一个特殊时期,所有的人除了当傻×之外便别无选择,不过一旦人们成长到有足够的理智,就会发现其实有两种选择:当傻×或亡命之徒。
很大程度上,王二的身上寄托了王小波自身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王小波推崇一个自由的、开放的、多元的社会,认同罗素所说的“参差多态是幸福的本源,把什么都规定了就无幸福可言”;他认为有两种知识分子,一种是“一世的修为,是要做个如来佛,让别人永世跳不出他的手掌心”,一种是“想在一生一世之中,只要能跳出别人的手掌心就满意了”;他认为信仰是重要的,但狂信会导致偏执和不理智,故信仰“要从属于理性——如果这是不许可的,起码也该是鼎立之势”;他认为乌托邦作为一种文学的题材,有其独特的生命力,但是作为一种制度,却有其极不妥之处:“首先,它总是一种极端国家主义的制度,压制个人;其次,它僵化,没有生命力;最后,并非最不重要,它规定了一种呆板的生活方式,在其中生活一定乏味得要死。”在小说创作中,王小波实际上是将他对于历史、人生、文化等等的思考借助于一种感性的形式表现出来,作为一个以思考独特、尖锐见长的作家,他小说中的人物和场景某种程度上成了他思想的载体。
《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等作品,实际上写的就是信仰陷入盲从、乌托邦成为一种制度时期的呆板、僵化、压抑、没有个人自由和幸福感的生活,以及王二这种异类反抗这种生活所产生的悲喜剧。王二最初是有不少奢望的,但后来却明白了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黄金时代》);不过,王二并不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由他人和时代所设计好的生活,他要起来抵制所有形式的不是基于个人选择自由的生活:“我早就超越了老鼠,所以我也不向往仓房。如果我要死,我就选择一种血淋淋的光荣。我希望他们把我五花大绑,拴在铁战车上游街示众。”
(《三十而立》)在这里,王小波笔下的人物显示出了一种少有的英雄主义气质。但是,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在于,它对个人的压制和人性的灭绝,更多的是采取了或不动声色、或笑里藏刀的形式,它甚至不愿给它的牺牲者提供一个实现血淋淋的光荣的机会,它的监狱是敞开的(如王小波笔下的工厂、学校、医院、五七干校),它的刽子手是群众(至少是借助了群众的名义,如群众专政),这就使王小波笔下的人物连个拴在铁战车上的机会也捞不着,结果只好采取了一种接近于猫捉老鼠式的游戏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反抗。王二们的反抗,不再以大义凛然的英雄主义方式出现,而是以捣蛋鬼式的嘲讽戏弄的形式出现,其深层的原因大概就在于此。
三
总体上,王小波对现代社会和人类文化的态度是悲观的。在《红拂夜奔》中,叙述人将《红拂夜奔》的寓意概括为“根本没有指望。我们的生活是无法改变的”。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王二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总结出一条对生活的看法:“不管何时何地,我们都在参加一种游戏,按照游戏的规则得到高分者为胜,别的目的是没有的。”在学校里是从老师手里得高分,在竞技场是从裁判那里得高分,在美国则是挣钱越多得分越高。人类给自己制订了规则,也就给自己套上了统一的枷锁,将本应丰富多彩的生活弄得呆板划一、了无生趣。王小波号召大家“跳出手掌心”,并怀念“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但却看不到一个光明的前途。如果说在早期小说《绿毛水怪》《地久天长》等作品中,王小波还保持着对纯真爱情、坚贞友谊的凝眸神往,那么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创作,则无论是对人世还是人情,都抱以低调的、悲观的态度。“青铜时代”系列小说是如此,《黄金时代》中的作品是如此,可归入“白银时代”“黑铁时代”系列的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