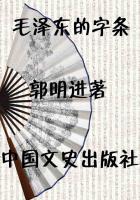知青文学的多元化不仅仅因为作家对历史的叙述和判断由激情走向了理性,知青一代的现实境遇也是导致这种多元化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末,知青一代所想的是如何尽快离开农村这块恶土回到城市,然而愿望达成之后,却发现城市生活仍不是自己的理想生活。由于学业耽搁得太久,他们中有的人不能如愿进入大学;由于先前想的只是尽快回城,他们中不乏有人被迫选择了并不理想的工作和单位;由于在农村耗费了最好的青春年华,他们有的回城后甚至失去了从容选择自己恋爱婚姻方式的空间和余地;再加上社会的冷眼、住房的紧张等等,都可能成为导致回城知青心理失衡的因素。王安忆《69届初中生》中的雯雯,回城后的第一个发现是“这是一个人尽其能的时代”,可自己却一无所能;《本次列车终点》中的陈信,发现在住房极度紧张的家庭生活条件下,自己仿佛成了家中一个多余人。当下生活的种种不如意于是化为对过去生活的怀念,曾经想尽一切办法逃离的乡村土地开始露出其可亲可近之处,在有的作家那里甚至成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成为自己流浪灵魂的最好的安居之所。知青作家的创作中因此兴起了一股迅猛的“回归”潮。在这种“回归”潮中,又可以细分出三种流向:
其一是去知青一代历史中发掘有价值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新的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基础。张承志是这种流向的典型代表。这个作家一直小心翼翼地回避着对红卫兵运动的直接文学描述,对知青生活中的屈辱的一面也是点到为此。他是当代作家中最倾向于正面肯定知青一代成长经历的作家。在《北方的河》题记中,张承志写道:“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来为我们总结的:那时,我们这一代独有的奋斗、思索、烙印和选择才会显露出意义。但那时我们也将为自己曾有的幼稚、错误和局限而后悔,更会感慨自己无法重新生活。这是一种深刻的悲观的基础。但是,对于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国度来说,前途最终是光明的。”后来,他又用更明确的语言说:“我不以为下述内容是一种粉饰的歌颂:无论我们曾有过怎样触目惊心的创伤,怎样被打乱了生活的步伐和秩序,怎样不得不时至今日还感叹青春;我仍然认为,我们是得天独厚的一代,我们是幸福的人。在逆境里,在劳动中,在穷乡僻壤和社会底层,在痛苦、思索、比较和扬弃的过程中,在历史推移的启示里,我们也找到过真知灼见;找到过至今感动着、甚至温暖着自己的东西。”正是凭借着对自己一代人成长经历中有价值因素的坚信,张承志在《绿夜》《老桥》等描绘知青、红卫兵“回归”题材的作品中,总是以对明天的期望和未来的期许弥补现实生活中的失望。当大多数人仔细地甄别过往理想的真伪与价值,或是嘲笑一切理想与信仰时,张承志却在《金牧场》中用断然决然的语气写道:“人心中确实存在过也应该存在一种幼稚简单偏激不深刻的理想。”梁晓声也倾向于用一种辩证的眼光来看待知青运动,他一方面认为它“是一场狂热的运动,不负责的运动,极‘左’政策利用了驾驭着极‘左’思潮发动的一场运动”,但另一方面又认为“荒谬的运动,并不同时也意味着被卷入这场运动前后达11年之久的千百万知识青年也是荒谬的”。他在《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等作品里,既描绘了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给李晓燕、裴晓云们身上打下的鲜明的可悲的时代烙印,也描绘了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勇于牺牲的可贵的理想主义气质和英雄主义精神。孔捷生的《南方的岸》是知青文学“回归”潮中的代表作。它既写了海南知青当年各自不同的选择,也写了一种不死的浪漫主义的理想精神在不同时期不同人物身上的延续。易杰、暮珍的回归海南,构成了作品中最激动人心的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价值取向。有意思的是,张承志《绿夜》中的“我”,在表弟的眼里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而在易杰看来,在世人的眼里,自己也最多是个持矛冲向风车的堂·吉诃德。与“伤痕”文学潮流中的知青文学有所不同的是,作者并不认为这种与风车战斗的堂·吉诃德式的姿态是一种荒诞的姿势。恰恰相反,作者认同于这种看似不识时务的价值取向——因为它有着充分的抗击时俗的精神价值。陆星儿的《达紫香悄悄地开了》,更是以一个重返北大荒的知青的眼,塑造了一个至今仍战斗在无数青年抛洒过热血的土地上的老知青形象。显然,作者要借这一人物脚踏实地、至死不悔的英雄行为说明:“‘知青’这个称呼所拥有的真正内涵,以及这段经历带给我们这代人的命运,绝对不应该只是哀叹和感慨。”
其二是立足于当下生活,试图在知青的青春理想与当下生活中架起桥梁,以更加入世的态度走向明天。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张辛欣的《我们这个年纪的梦》,陶正、田增翔的《星》是这种倾向的代表作。三个作品的共同点,是其主人翁对当下生活都有所不满,这种不满又促使他们以一种眷恋的姿态回首当年的知青生活。当下生活的琐碎平庸反衬出了当年青春理想的单纯可爱。然而,主人公经过一番沉思,觉悟到回归当年的生活只能是梦想,理想只有附着于现实才能找到其实现的基础,不能用对美好过去的追忆来代替对美好未来的追求。这类作家的作品都试图在理想与现实、过去与未来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的每一节都以一个童话故事开头,多彩的童话映衬出了现实的平庸,主人公认定不幻想不做梦的生活是可悲的,但作家并没有愤激到像张承志那样在高蹈理想的同时去蔑视一切卑污龌龊的生命,而是让主人公于“在那些无形的梦和实在的生活之间,是不是有着一座桥”的沉思中形成了一种达观。
作品以“于是,她去淘米、洗菜、点上煤气,做一天三顿饭里最郑重其事的晚饭”结尾,无疑传达出了一个信息:梦想归梦想,日常生活还得继续。《星》中的“星”,既是一首诗的题目,同时也是主人公理想世界的代名词。作品一方面借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抨击了鄙俗的人生取向,另一方面也借他人的反驳阻击了一味怀旧的价值取向:“你想,氏族社会多好呀,那时的人和生活一定很淳朴;山顶洞人更值得怀念,他们穿树叶,吃兽肉,从不制造污染;周口店人可能连火都不会生呢!他们所看到的,准是最最灿烂的夜空!”正是这种充满讽刺意味的话,使《星》不至于成为一种单纯高扬理想、只有一种声音的独白体小说。
这批作品的回归怀旧倾向,都不如第一种流向的作品那么浓烈,作品中具有知青身份的主人公,都没有像易杰们那样真的去旧地重游。显然,他们的作者,也无意于塑造具有理想气质的英雄人物。他们似乎更理解普通人的苦恼和欲望,对普通人在世俗和现实面前的妥协也更倾向于一种同情的态度。《69届初中生》中,任一以烟酒打通了雯雯的回城之路,事成之日,任一在雯雯眼中却成了一个令人厌恶的陌生人。
王安忆在这里的处理是相当艺术化的。在任一“我是没有办法,没法子!没法子”“我们都是很普通的人,我们都是小人物”的哭诉声中,雯雯与任一抱头痛哭。作为普通人,他们朝思暮想地期望回到自己的出生地上海;作为普通人,他们又找不到其他任何改善自己生存环境的途径。他们是为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和做人的原则而痛哭。王安忆是带着一种怜悯的同情的态度来写知青的选择的。她不愿将任一一类的知青处理成普通人之外的另一类人,他们不过是普通人中的一员。这也印证了王安忆自己所说的一席话:
现在,我不愿说:我们这一代,是如何如何的一代。置身在我们民族四千年的历史上,我们这一代似乎并没什么值得特别强调的。
现在,我不愿意说:知识青年的生活,是如何如何的生活。
置身在我们八亿多人的人生之中,这生活也似乎并没什么值得特别在意的。
何况,还有世界,还有宇宙。
当众多作家在强调夸耀知青一代的特殊性时,王安忆却主张将知青生活放到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下去看,她所从事的几乎是一种去神圣化的工作,在她那里,知青生活不过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一个变种。正是这种将知青当作普通人来写的倾向,导致了她后来在《岗上的世纪》中对特殊时期里日常生活之流的关注,对普通人欲望的关注。《岗上的世纪》中的女知青李小琴,既是社会人,也是自然人。作为社会人,她试图利用自己的色相达到回城的目的,杨绪国这时在她的眼中是丑陋的;作为自然人,她在同杨绪国的暧昧交往中得到了欲望的极大满足,杨绪国这时在她的眼中是强健的。可以说,如果张承志、梁晓声们是将知青当作虽败犹荣的英雄来写,其作品中贯穿了“青春无悔”的声音,王安忆们则是将知青当作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来写——他们有普通人的向往和追求,也有普通人的苦恼和欲望。
其三是有意地回避对知青生活的正面评价,并从知青生活中引出对更大的人生境遇的思考。韩少功的《归去来》是这一倾向的代表作。作品以如梦如幻的形式,写了“我”(黄治先)被误认为当年知青马眼镜的经历。作者通过这种有意无意的身份混淆,艺术地表现了知青主体身份的迷乱和困惑感。知青作家喜欢用“梦”来表现自己这一代人的理想,或是对知青生活的怀念,韩少功却用一次如梦似幻的“归去来”表现知青一代的恍若隔世感。韩少功曾在《月兰》《遥望茅草地》等作品中描绘了“左”倾的危害,又在《飞过蓝天》中表现过知青的沉沦与追求,还在《远方的树》中传达过知青对已逝生活的情感上的留恋,但我们注意到,《远方的树》中,田家驹将要离开自己插队的土地时,内心里升起的是一种“熟悉又陌生,亲近又遥远”之感,甚至产生了自己曾在这里生活过么的奇怪想法。《归去来》表现的不过是数年后“回归”潮中知青的那种“熟悉又陌生,亲近又遥远”之感。黄治先赤身裸体洗澡时对自我身份的思考,正代表了作家对知青主体身份的思索:“由于很久以前一个精子和一个卵子的巧合,才有了一位祖先;这位祖先与另一位祖先的再巧合,才有了另一个受精卵子,才有了一个世世代代以后可能存在的我。我也是连接无数偶然的一个蓝色受精卵子。来到世界干什么?可以干些什么?”“我”是偶然之物,正如“我”被“命名”为马眼镜是偶然的一样。推而广之,所有的知青包括整个的知青运动都是偶然的,都只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环。“我”的这种思考实际上瓦解了梁晓声式的“我们是时代的活化石,我们是独特的一代。无论评价我们好或不好,独特本身就是历史的荣耀”式的文学叙述。而一旦瓦解了知青一代的独特性,知青主体的身份就成了一个问题,《归去来》的结尾(“我累了,永远走不出那个巨大的我了。妈妈!”)传达的或许正是这种主体身份的迷乱感与困惑感。
而这种迷乱感与困惑感,只不过是人的迷乱感与困惑感的寓言式表达。
知青作家的创作,尽管最初呈现出向主流文学靠拢的趋势,但大多还是从自己个人的经验起步的。随着创作的深入,不少作家开始从自身的经验里超脱出来,从而获得了更大的文学视野,注意到了更具普遍性的人生。这种变化无疑是知青作家创作中的一个突破。确实,知青和知青生活都是独特的,但将其置于更广大的人生背景下去审视,知青与知青作家的问题其实也是整个人类和所有作家的问题。如知青作家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对乡土的“逃离与回归”情结,我们在所谓青年农裔作家如贾平凹、莫言等身上同样可以看到。青年农裔作家对故土的那种既爱又恨的情感,与知青作家对乡土的那种“逃离与回归”的矛盾情感何其相似。距离产生美,只有失去的才是最好的,其间的奥妙,也只有放在普遍人性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释。王安忆、韩少功、阿城、史铁生等作家后来都脱离了单一的知青立场去反映更广更大的人生。如果说,“伤痕”文学时期的知青作家创作同“归来”一代作家一样立足于“我们国家”、“我们党”的立场,“回归”潮中的创作是立足于“我们这一代”的立场,后来的知青作家的创作则开始逐渐向民族文化立场和民间立场转移。阿城曾说:“我有幸与我极佩服的作家贾平凹谋面,并请他对《棋王》讲些真实而不客气的话。他说:知青的日子好过。他们没有什么负担,家里父母记挂,社会上人们同情,还有回城的希望与退路。生活是苦一些,但农民不是祖祖辈辈这么苦么?
贾平凹的这些话使我反省自己,深感自己不只是俗,而且是庸俗,由此也更坚定了我写人生而不是写知青的想法……”确实,知青上过当,受过苦,但比起中国广大的受苦受难的农民来,所经受的苦难可以说微不足道。立场的变化带来了创作风貌的相应变化。
如阿城的《棋王》,主人公王一生虽为知青,也追求精神化的生活,但他的生活态度却相当平民化。“此去的地方按月有几十元工资,我便很向往,争了要去,居然就批了。”叙述的是乱世,作者的叙述语调却是从容的,镇定的;王一生是一个异人,但在叙述人眼里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倒是精神上同历史上的那些无名小辈有些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