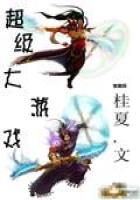一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作家基本上停留于对伤痕的描写、历史的反思、改革的鼓吹,对政治、经济、道德与法的热情使他们的创作满足于题材的突破、主题的更新、伦理的讨论,对意义内容的过分投入使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学对文学的形式探索表现出了一种明显的轻视与漫不经心的态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的兴起,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是一个新的契机。它们不仅使中国文学进入到了文化、历史、自然与人的范畴,而且也形成了一种对文学的形式探索的自觉。中国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呈现出了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的良好发展态势。在这一发展过程中,马原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带有过渡性质的文学人物。他的具有浓厚实验探索色彩的创作不仅启发了相当多的先锋作家对小说的叙事艺术的自觉,而且也带来了批评界和读者的兴奋与困惑。人们用“马原的叙事圈套”和“马原式的叙事迷宫”一类的言辞来表达对马原小说的观感,既透露出了马原小说在那一时期给人们的新奇之感,也反映出了其小说创作所带来的阐释的困难与困惑。
马原小说最令人兴奋和困惑的,首先是他在叙事技巧上所玩的众多的花招和小把戏,特别是他对真实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人物身份的有意混淆。作者最大的爱好和本领是将“马原”引入小说文本,让其讲述故事、让其冒险、让其写作、让其谈论故事的讲法和小说的写法,这既使他的小说具有了相当浓厚的元小说色彩,而且突破和混淆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达到了真真假假、以假乱真的效果。“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我喜欢天马行空,我的故事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点耸人听闻。”《虚构》一开始便自报家门,端出一个多少有点夸夸其谈、自以为是的“马原”自我形象。
但这一自我形象的复杂性,是他同时兼备了真实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人物等多重身份。随着故事的展开,这种多重身份一一得到了印证。在作品的不同地方,这个“我”分别指向了不同的身份。
“我就叫马原,真名。我用过笔名,这篇东西不用”,“我实在只是个写小说的拉萨居民,时而有一点超出常规的浪漫想法”,这两处的“我”显然指向了真实作者“马原”。而“实话说,我现在住在一家叫安定医院的医院里……我住在这里写作”所创造出的是一个写作者的形象,这个“我”所唤起的是有关隐含作者的想像。所谓隐含作者,按赵毅衡的说法,即“实际参与写作过程的作者的代理人”,“是作者通过作品的写作创造出来的一个人格”;按布斯的说法,则是“作者的‘第二自我’和‘正式替身’”。在一般情况下,这个隐含作者不会直接出现在作品中,他应当是读者依靠文本的阅读建构起来的作者形象,它可以同真实的作者完全相同,也可以大不相同或大同小异。但马原却虚构出了一个直接出现于文本中的写作者“我”的形象:“我开始完全抱了浪漫的想法,我相信我的非凡的想像力,我认定我就此可以创造出一部真正可以传诸后世的杰作”,这个有点盲目自信和自大的“我”的形象,进一步强化了读者对有些自恋的隐含作者的想像。而《虚构》的复杂性还在于,除第二节以外(第二节中的“我”是作品中的人物“哑巴”),作品中的“我”既是叙述者,又是作品的主人公。随着现代叙事学的兴起,人们已经能够较清楚地区分叙事作品的作者与叙述者及主人公,不再将作者与叙述者“我”、主人公“我”混为一谈,也就是说,读者已经能够较理智地将叙事作品中的“我”视为作者创造出来的一个叙述者/人物形象,但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真实作者与叙述者/人物间又不是毫无联系,特别是在带有实录色彩和自传色彩的小说中,叙述者和人物“我”身上常带有较多的真实作者的影子,并且可以成为后者的较可靠的代言人,这就增加了区分真实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人物“我”的难度。《虚构》对于“我”的玛曲村之行有接近历史书记员式的实录,对“我”与麻疯病人接触时的周边环境、气候特征等都有纤毫毕现、煞有介事式的描绘,这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故事的“真实”面貌;但是小说中出现的带有元小说性质写法的段落,又拆穿了故事的“真实性”的帷幕,使有时间、地点、人物的玛曲村之行落实为一个叫“马原”的作家的纯粹虚构和一个在疯人院写作的“我”的超出常规的浪漫想像。《虚构》因此呈现出了真实与虚构交糅重叠、混沌难分的审美形态。
虽然马原在《冈底斯的诱惑》《西海的无帆船》等作品中总是频繁地变换视角和人称,通过改变叙述视角和叙述声音以造成焦点的移动和变化,并达成不同的叙事效果和审美信息,但马原的大部分小说还是采用的第一人称叙事,只不过这个第一人称叙述者在马原的小说中主要承担叙述功能、管理功能、见证功能和交际功能,而很少发挥评论功能。一般来讲,第一人称叙事由于叙述者身在故事之中,其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往往就是他自己的叙述对象,因此其中常常带有自己较多的主观色彩和生命体验,但马原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很少叙述自己的故事(《虚构》等少数作品例外),他更多时候是故事的旁观者而不是主人公,在叙述故事时主要采用的是客观叙述而不是主观叙述,也就是说,在叙述的过程中,这个叙述者“我”主要承担叙述和见证故事的功能,他关注的更多的是人物的行为和事件的本身,主要叙述的是人物在做什么而避免叙述人物在想什么,基本对人物和事件不表明自己的主观态度和价值判断(哪怕是《旧死》中面对海云做出的那种令人发指的乱伦事件时也是如此)。但与此同时,马原的叙述者又不是隐身于文本之中而是公开出现在文本之中,总是采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如与拟想读者公开对话或是自我嘀咕的方式)讲述小说的构思过程和叙述方式,彰显写作的痕迹,暴露小说的虚构特征,时时让读者意识到叙述者的存在。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我之所以从结尾开始讲述这个故事,部分是因为这个故事早已经发生过,它与那些边讲述边发生的故事有大不同,它自身能够提供的可能性都已经完成了或接近完成,或者可以说这个故事的弹性已经被它的过去时态消蚀得一干二净了。”(《死亡的诗意》)“那些看惯了我东拉西扯的老读者,请不要在这里抛弃我,这一次我至少不是东拉西扯,我是认真地做一次现实主义实践,请一行一行循着我的叙述读下去;我保证你不会失望,正儿八经的。就这么说定了行吗?非常感谢。”(《旧死》)这样的公开叙述与努力地制造“真实”的幻觉的隐蔽的叙述不同,它揭示出了小说虚构的秘密,叙述者在这里既承担了划分篇章、衔接故事等等管理功能,而且承担了与叙述的接受者(读者)进行交流的交际功能。
如果马原的小说仅仅停留于此,还不足以构成其小说的独特风貌。作者在频繁地使用公开的叙述揭示虚构的秘密的同时,还让一个叫“马原”的家伙以各种各样改头换面的方式出现于文本中,夸耀小说的虚构的权利,时时表明写作者的存在,特别是表明他有怎样的虚构才能并曾有怎样的创作伟绩。《虚构》是个典型的例子。长篇小说《上下都很平坦》亦不乏其例:“我不能不咬文嚼字。要骂人我比他便利,我让他骂人他才骂人,我可以要他死。我在虚构小说的时间里神气十足,就像上帝本人。”“我”在姚亮面前的上帝般的优越感使“我”的身份变得可疑,他似乎突然从一个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角色退回到了小说作者的角色——这个角色在其他虚构人物面前拥有生杀予夺、杀人无算的权力。《上下都很平坦》在写到肖丽的自杀时,又提到一部记载肖丽死前那段生活的小说:“那部小说的作者也叫马原,不知道那个马原是否还活着。”这种装聋作哑、装疯卖傻式的互文手法,使马原的另一作品《肖丽》同《上下都很平坦》之间形成了一种互相指涉的关系;而在写到陆高的爱犬时,作品又出现了这样的段落:“后来的事,看过我的《海边也是个世界》的读者都知道了。结果被勒死的是陆高的爱犬。
这就是真象。”这一段既在作者不同的两个小说文本间建立起了一种互文关系,同时透露出了小说的虚构秘密:相同的故事原素经过不同的艺术处理可以演绎出全然不同的情节线索和故事结局,只要读者回想起叙述人在开篇定下的“我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年龄,我不再试图还原所谓真实”的基调,便不免心生疑惑——谁来保证《上下都很平坦》所写的陆高爱犬的故事就是“真象”?所谓“真象”之说,只是进一步暴露了小说的虚构本质而已。
在马原的小说中,最具有意味同时也最让人困惑的是其作品中“我”、马原、姚亮和陆高的关系。“我”是马原作品中的叙述者和人物,但作者常常使他混同于真实作者“马原”:“这一节描写使我筋疲力尽。我觉得我像个刽子手,我怕我,怕这个马原。我怕我再也受不了,我想草草结束了。”
《西海的无帆船》中,“我”突然不经任何过渡就从叙述者和人物的位置退到写作者的位置,从而形成了作品中“我”的身份的多重含混和混淆。姚亮和陆高本是作者马原创造出来的两个虚构人物,但在《西海的无帆船》第23节中,姚亮却以第一人称叙事者的身份出面,指责“马原先生的这篇小说尽他妈的扯蛋”,“他在小说形式上大耍花样,故意搞得扑朔迷离以造成效果,使读者不辨真伪”,姚亮并且透露了“陆高就是马原本人”的内幕,并吁请读者推敲其叙述人称和结构方式。
这一节带有浓厚元小说色彩的文字,既揭露了小说的虚构特征,同时也造成真实与虚构的混淆。在这一方面走极端的一个作品是《涂满古怪图案的墙壁》。该篇一开始便写道:“我下决心在这个故事里不出现我。”
但在第二节对姚亮作出介绍时,又写道:“我的一部小说曾对他提出通奸指控……那部小说叫《西海的无帆船》。我叫马原。”不难看出,在开头部分,作者将“我”的意义控制在人物角色的范围之内,在第二节,则将“我”的意义控制在真实作者的意义之上。但这一作品并没有严格地维持这两者间的界限,作品后来写道:“姚亮有过著作,是与孙效唐先生合作完成的一个短篇小说,叫《中间地带》,发表在1984年5月号的《西藏文学》杂志上”,然而熟悉马原作品的人知道,《中间地带》恰好是马原与孙效唐合作的一个作品。
这显然又是马原在叙事上玩的一个小花招,即采用一种混淆视听的手法,抹去人物角色与真实作者间的界限以造成叙事上的迷宫和阅读上的障碍。《涂满古怪图案的墙壁》的令人惊奇之处,是姚亮抄录或保存的一部手稿《佛陀法乘外经》记载了尚未发生之事——姚亮的蹊跷的死及姚亮死后陆高阅读手稿的过程,而《涂满古怪图案的墙壁》的题记也出自《佛陀法乘外经》:“有些人出于自尊意识,喜欢用似乎充满象征的神兮兮的语言,写可以从后面从中间从任何地方起读的小说,再为小说命名一个诸如——涂满古怪图案的墙壁——这样莫测高深的标题。他们说为了寻求理解;这话同样令人难于理解。”这一题记既暗示了《涂满古怪图案的墙壁》
的结构方式,同时也充满了对《涂满古怪图案的墙壁》的反讽,这事实上建立起了文本本身与文本中的文本的自我相关、相互指涉、互为反讽的复杂关系。不仅如此,在陆高的梦中,姚亮过去的情人尼泊尔小情人与陆高谈起了姚亮之梦,并说姚亮曾对马原大加抨击嘲讽。这种抨击嘲讽堪称是作者塑造出的人物对作者的造反,它描述出的是作者与人物间的复杂关系:作家因他的人物而成为作家(“马原只是记录他的生活就成了作家”——这里的“他”指姚亮),但人物一经塑造出来便获得了自已的独立性(“白纸黑字,不朽的是姚亮而不是他姓马的”,“傻瓜蛋马原自觉自愿地当了他的书记官”),不过归根结底,人物还是跳不出作者的手掌心,因为作家拥有他至高无上的权利和对人物命运的终审权(“他明知道马原谋杀他可他对此无计可施,他想过要指控马原也知道结果一样”)。
从《涂满古怪图案的墙壁》看来,马原带有元小说色彩的创作远不止于只是采用公开的叙述将写作的具体技法暴露出来,他还通过更为深层的具体的人物形象塑造、故事情节的设置,实践着一种有关小说的小说创作。
二
姚亮和陆高是经常出现在马原小说中的两个人物和叙述者,在《西海的无帆船》《冈底斯的诱惑》《海边也是一个世界》《涂满古怪图案的墙壁》等作品中,他们同“马原”之间构成了一种特殊的互相指代的关系,那么,是否可以说姚亮和陆高是作者马原的双重第二自我或作者人格的双重替代呢?应当说,在马原那里,还不能建立如此直捷的关系。首先,姚亮和陆高出现在马原作品中叫姚亮和陆高纯属偶然,他们并不是不可替代:“他叫姚亮,叫陆高也行。
看来这又是陆高和姚亮两个人的故事了。也不一定。为什么不能再有别人的人?甚或别的——什么东西——比如一条狗(陆二?
陆三?陆九十九?)?比如一面画满古怪图案的墙壁?”(《涂满古怪图案的墙壁》)这事实上意味着姚亮和陆高频繁出现于作者笔下只是习惯使然,所谓更为便当罢了。其次,姚亮和陆高在马原的小说中经常是一种互为反讽、相互拆台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更多局限于小说的虚构范围之内,并不指向一个统一的或者分裂的作者人格,他们更多的是要有意混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西海的无帆船》在写上一段姚亮指责陆高就是马原本人、他在小说形式上大耍花样之后,又由“我”直接出面说上一段“姚亮是个可爱的人,只不过在经历了这次劫难后,他的精神受到一些刺激”,这显然是为了一方面要造成姚亮实有其人的印象,一方面又要瓦解姚亮看上去有理有据的指责,使作品所写的两次历险经历维持在真实与虚构之间的混沌状态。
此外,这种相互拆台也使马原带有元小说性质的小说创作散发出一种自我嘲讽气息。读者从马原小说中得来的隐含作者的印象,一方面是自高自大、夸夸其谈、自以为是、华而不实的,颇有些王婆卖瓜、卖啥吆喝啥的味道,但另一方面,又是敢于自我嘲讽、自我贬低、自我拆台的,颇有点自轻自贱、自掌嘴巴的勇气。可以说,自恋与自贱,在这样的隐含作者身上,得到了同等的体现。它在高度炫耀作者的虚构权威和才能的同时,又在消解和嘲弄作者的虚构权力和能力。
马原最喜欢运用的叙事花招之一是使自己的作品同自己或其他人的作品互相关联镶嵌,形成一种互文性。南帆就曾略带调侃地提到马原“喜欢敞开小说的边界,让他的众多的小说相互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