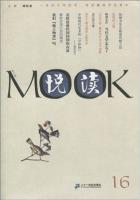苏童描绘出的南方还是一个孤独无助的南方。人在其中显得既寂寞又孤独,既无望又无助。这种孤独感和无助感既不是来自于人在博大的自然和悠久的历史面前所感受到的人的渺小和人生的短暂,也不是来自于个人与强大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尖锐对抗,而是来自于人的最基本最原始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或得到满足以后仍然无法解决人类与生俱来、无法根除的痛苦。苏童特别擅长写一种孤独寂寞的心态。少年剑在妹妹小珠惨死于铁道之上以后,懂得了顺从母亲的意愿而不再到铁轨上去玩,但他人虽留在家中,心却仍在铁轨上活蹦乱跳:“但是在那个炎热潮湿的夏季里,剑总是神思恍惚,在凭窗眺望不远处的铁道时,他的心也像天气一样炎热潮湿,是一种烦闷不安的心情,剑知道那是因为他克制了欲望的缘故。”(《沿铁路行走一公里》)这是一种少年的欲望无法得到满足的寂寞与孤独。一个能不说话就绝不说话、总是用冷漠散淡的目光拒绝着同事们任何交谈愿望的邮递员,与一个年轻美丽、发出幽怨的叹息之声的女孩产生了奇遇,但结果却是幽明殊途、阴阳两隔,一个接近人鬼恋的故事,表达的也是一种普遍的孤独之情(《樱桃》)。尤为难得的是,苏童似乎深谙艺术表达的辩证法,他还经常借吵吵嚷嚷和轰轰烈烈去表现人的孤独与无助。少年小拐为了摆脱与生俱来的受欺负的屈辱地位,拖着一条病腿到处拜师学艺,复兴野猪帮,试图过一种威风凛凛、颐指气使的生活,但命运偏偏残忍地捉弄了他,另一班青少年无法容忍一个小拐子在香椿树街称王称霸,他们不是在小拐的手臂上刺上他想像中的野猪标志,而是在其额头上歪歪扭扭地刺上“孬种”两字,从此小拐羞于走到外边去,渐渐变成了孤僻而古怪的幽居者(《刺青时代》)。一个自卑的少年在吵吵嚷嚷的少年时代想通过自己强硬的人生态度换来自尊,结果却陷入了命运的捉弄和更大的耻辱之中。少年小拐的童年时期仿佛是无拘无束的,自在自由的,但表面的大呼小叫、快活单纯却难以掩其内心的孤独与悲伤。苏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米》,已被人们做了各种各样的归纳与阐释,但它最根本的还是要借一个逃亡与回归的故事母题,去写一个人的孤独无助的、具有轮回意义的一生。我们甚至于可以简切地说它要表现一种南方的孤独。嚼着家乡枫杨树出产的最后一把糙米进入城市的五龙,一开始就屈服于最原始的饥饿感,为了一块卤猪肉而叫了城市地痞阿保一声“爹”。这种屈辱的地位和遭遇使五龙后来所有难以置信的、出乎意料的行为和举止得到了解释:他的残酷,他的无耻,他的敲掉满口好牙而装上满口金牙,他的临死之前还想押送着一车大米回到枫杨树故乡,其实都可以在他刚入城市的那一声“爹”里找到解释——在命运面前,这是一个无依无助的孩子,他所有的挣扎和苦斗都可以看成是对自己屈辱命运的反抗。五龙最后的心理活动是颇有意味的。他在辽阔而静谧的心境中想像自己出世时的情景,但是什么也想不出来:“他只记得他从小就是孤儿。他只记得他是在一场洪水中逃离枫杨树家乡的。五龙最后看见了那片浩瀚的苍茫大水,他看见他飘浮在水波之上,渐渐远去,就像一株稻穗,或者就像一朵棉花。”真可谓世事苍苍,人海茫茫,在残酷的命运面前,个人就像是一个没有爹妈、失去了家园的孩子,飘浮在滔滔的洪水之上。五龙似乎把握了自己的命运并获得了成功,但他的灵魂至死也是孤独着、飘浮着,找不到它的居所。关于《米》,还是作者自己说得好:“这是一个关于欲望、痛苦、生存和毁灭的故事……《米》的主人公五龙是一个理念的化身。我尝试写一种强硬的人生态度,它对抗贫穷、自卑、奴役、暴力、孤独,在对抗中他的生命沉浮着,发出了我喜欢的呻吟、喘息、狂喜或痛苦的叫声。”五龙的一生,可以说是轰轰烈烈的,但本质上仍然是悲剧性的。作者通过五龙的一生,写出了一种孤独无依的生存状态:不仅人与人之间是相互隔绝的、无依无靠的,而且人的肉体与灵魂之间也是分离的,南辕北辙的。夸张一点说,孤独无助是一种永恒的生存状态。五龙的孤独,堪称一种南方的孤独,一种普遍的人的孤独。
苏童笔下的南方还是一个忧郁伤感的南方。无论故乡的过去是多么有声有色,童年的生活又包含着多少快乐欢欣,苏童勾画出的南方的面孔本质上总是忧郁伤感的。故乡的传奇掩不住心底的失落,童年的快乐也遮不住那突如其来的内心忧伤。且不说少年时期那么多无法理解的死亡事件所唤起的内心的隐隐的兴奋与不安,单说一个简单的愿望得不到实现和满足便足以使少年的内心充满忧郁和悲伤。少年舒农的愿望是从分床的第一夜起便不再尿床,但无论怎样努力也还是归于失败(《舒家兄弟》);陶经历了回力牌球鞋失踪事件以后,养成了无论走到哪都眼光下斜、观察别人脚上鞋子的奇怪习惯(《回力牌球鞋》);少年达生杀人的起因不过是为了赶在游泳池关门前的最后一天好好地游一回泳(《游泳池》)。
最简单的愿望导致了最扭曲的行为,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忧郁和悲伤的呢!但少年的忧郁和悲伤还不止于此。童年时代的意中人再次劈面相逢时成了一个腆着大肚子的女人(《桑园留念》),自己喜欢的金鱼突然暴死(《金鱼之乱》),舞跳得美丽动人的女孩赵文燕在舞台上却没能憋住尿尿(《伤心的舞蹈》),所有这些细琐的看似无意义的材料却成为苏童展现少年的忧郁和悲伤的绝好素材,这一方面归功于苏童对少年心理、情绪的深入体察,同时也归功于这一作家的简单优雅的叙述语言,水一般的柔弱风格。当然,苏童笔下的南方的忧郁,不仅来自于作品中人物的那种忧郁情绪,还来自于作者将讲述话语的时代的一些情绪融入了话语讲述的时代之中。在“香椿树街”和“枫杨树故乡”系列作品里,苏童在叙述方法上同当时的大部分先锋小说一样,做了一些创新和尝试。在作品中,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话语讲述的时代与讲述话语的时代之间的分离与糅合构成了一种特殊的艺术张力和审美效果。在话语讲述的时代里,“我”曾经以拍手大笑来对待赵文燕的尴尬处境,但在讲述话语的时代里,“我”由于经历了更多的人世沧桑,体悟到了少年的天真幼稚里其实也蕴含了一种残酷的意味,“我”的回顾往事因此带有了更多的忧郁之气。特别是在“枫杨树故乡”系列作品中,由于叙述人“我”总是从当下的生活处境去眺望遥远过去的故乡生活,话语讲述时代的生活与讲述话语时代的生活于是构成一种内在的对比,“我”作为城市“外乡人”的身份总是强化着故乡一去不复返的失落感与忧郁感,故乡的颓败和没落更增加了叙述者内心的失落与忧郁,于是,一个颓败无望的、孤独无助的、忧郁伤感的“枫杨树故乡”形象便出现于苏童笔下,并强化了其笔下的南方总体形象。
迄今为止,还很少有作家像苏童一样如此集中为我们描绘一个充满颓败无望的历史气息和忧郁伤感的审美意味的南方形象。
在沈从文、废名、汪曾祺等作家笔下的南方,是一个充满人情美和人性美的南方,是带有田园风味的南方,是有点遗世独立意味的南方,为了达成一个理想化、纯粹化的南方形象,他们基本上取一种有所规避的创作态度,特别是不去触及人内心的最原始欲望,即使写,也只写健康的最原始的欲望;而鲁迅、许杰、王鲁彦、高晓声等作家,则多从思想启蒙与国民性批判的角度,将南方塑造为一个荒蛮、愚昧、落后的,在物质和精神上呈现出双重贫困的所在,过分强烈的启蒙意图和民风民俗的渲染甚至影响了他们将南方作为审美的对象来看取。苏童的创作则有所不同,他关注的是一个想像的、作为审美客体的南方,但他又是从人最基本最原始的欲望入手去描绘南方形象的,因此,他所塑造的南方,既是一个有着生活实感的南方,又是一个想像的文学的南方。
三
尽管苏童的“香椿树街”和“枫杨树故乡”的故事为读者提供了有关南方的文学想像,但真正给他赢得大批读者的是他的“妇女生活”系列。《妻妾成群》《红粉》被搬上银幕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这批小说更强的故事性、可读性和熟悉的陌生感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苏童曾在《红粉·代跋》中说:“我喜欢以女性形象结构小说,比如《妻妾成群》中的颂莲,《红粉》中的小萼,也许是因为女性更令人关注,也许我觉得女性身上凝聚着更多的小说因素。”在“香椿树街”和“枫杨树故乡”的故事中,苏童已经塑造了一系列的女性形象,如刘素子、祖母蒋氏、女人环子、疯女人穗子、丹玉、毛头的女人、蕾、姚玉珍、红菱,但她们在作品中并没有上升为主角,通常只是男性世界的一点点缀,或是男性欲望的追逐对象。她们身上的更多的小说因素,主要表现为围绕着她们而展开的一些戏剧性因素(如通奸、乱伦、引诱、争风吃醋等)使南方堕落、颓败的文学形象得以丰满。如《门》一篇,一开始便写毛头的女人吊死在门框上,是小偷朱明所为,还是单身汉老史所为,抑或是毛头的女人因为自取其辱而死?作品没有提供一个确切的答案。但由于作品多次写到关于门的谜语、毛头的女人为老史留着门、老史又自称阳萎,这一作品便散发出一种暧昧、神秘、堕落的气息,从而与其他作品一起,完成了对于南方小城颓败生活方式的描绘。
《园艺》《红粉》《妻妾成群》《妇女生活》《另一种妇女生活》有所不同,女性在作品中上升为主角,成为作品最有力的结构因素。这些作品处理的都是男女的情爱与婚姻生活素材,侧重于写活生生的男女如何在婚姻和情爱的深渊中无望地挣扎苦斗。可注意的是,女性在这些作品中是主角,但却不是婚姻情爱领域里的主人,她们似乎总是将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糟,没有男人的日子她们不能过,有男人的日子仿佛也过不好。孔太太先是赌气不让孔先生回家来,一旦先生没回家便仿佛失了主心骨,变得魂不守舍,六神无主,儿子令丰、女儿令瑶也跟着受气(《园艺》)。没有男人的日子女人和女人可以成为好姐妹,男人一出现,胜过姐妹的两个女人却反目成仇。《红粉》中的小萼和秋仪便是典型的例证。三个女人一台戏,但三个女人却很难将一出戏演好。《妇女生活》将一家三代娴、芝、箫放在一个历史发展的流程中去写,虽然宏观的时代和历史在发生着急剧变化,妇女的生活却很少变化,下一代的生活差不多就是前一代的重复,母亲甚至成为搅乱女儿幸福的关键因素。
《另一种妇女生活》写了简家酱园三个女店员与简氏两姐妹的生活。三个女店员栗美仙、顾雅仙、杭素玉之间关系的微妙多变,真胜过一场类似男人间的多国战争,分分合合,瞬息万变,基本上没有什么游戏规则和道理可讲;没有走上社会、以刺绣为生的简少贞与简少芬姐妹,虽然以一种自闭的生活方式构成了对男权中心文化的拒斥与背离,但久而久之也无法维持一种自足的姐妹情谊。
看来无论是新式职员的与时俱进,还是老式姐妹的固步自封,都没有给妇女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带来什么令人振奋的因素。泯灭人性的婚姻礼俗与道德伦理、灰暗平庸和琐碎无聊的日常生活、人内心最原始的本能和欲望,构成了苏童笔下那令人不寒而栗的情爱和婚姻生活风景。
《妻妾成群》是苏童流传最广的作品。中国文学史上“一夫多妻”的故事和“红颜薄命”的母题在这里得到了新的文学演绎和诠释。作品从年轻、水灵、有文化的颂莲踏进陈府大门写起,到颂莲发疯、五太太文竹进陈府大门戛然而止,触及的是“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屡见不鲜的封建大家族制度和男权中心文化“吃人”的主题。但作者没有将主要的笔墨用于控诉声称“女人永远爬不到男人头上来”的封建家长陈佐千的荒淫和无耻,而是通过对颂莲悲剧命运的描绘,重点表现了五个女人(一妻三妾一丫环)如何为了将自己拴在一个男人的脖子上而互相绞杀。一夫多妻的家庭结构留给她们的是十分狭窄、令人窒息的生存空间,争宠斗法便成为她们拓宽自己生存空间的惟一选择。现代女权主义者所张扬的“姐妹情谊”面对着最现实的考验,每个女人的争宠都是对其他女人的生存和呼吸的一种威胁——性的压抑和无法满足便足以使她们相互为敌。从颂莲最初选择走向做妾的人生之路一点看,她是自以为能把握自己命运、在陈府获得自己一席之地的。她的“女学生”身份确实也使她在故事的开始阶段表现出了一定的优势,但时移境迁,颂莲带有学生气和现代味的言行举止却使她越来越不容于充满了僵尸气味的大家庭。她既不像毓如那样拥有制度本身赋予她的高人一等的地位,也不像卓云那样熟知男性中心家庭的游戏规则,同时也不像梅珊那样为了自己生存的权利而敢于胆大妄为。